余华认为,莫言不受各种意志约束,能够 “吾手写吾口”,这是对创作自由的极致践行。“吾手写吾口” 意味着莫言在创作中坚守自我,以真实的笔触表达内心的思考与感悟,不被外界的条条框框所束缚。这种创作状态让他能够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社会的肌理,其作品中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与强烈的个人印记。 同时,莫言敢于质疑和反思,这恰恰体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文学不仅是美的呈现,更是对现实的观照、对历史的叩问,莫言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作品中对诸多社会现象和人性问题进行深刻剖析,引发读者对生活与世界的思考,这无疑是对 “作家” 这一称号的最好诠释。 余华强烈反对有些人对作家进行道德上的无端指责,认为这是对作家个人人格的侮辱,是恶毒且残忍的,尤其是当这种指责仅仅基于似是而非的借口时。作家的创作应基于内心的真实与艺术的追求,而非被强加的道德枷锁所捆绑。莫言的创作始终遵循文学的内在规律,其作品的价值在于文学本身的魅力与思想的深度,而非迎合某种外在的道德评判标准。而莫言的获奖,余华强调无关于政治,也无关于他 “体制内” 的身份,我们不应为此苛责他。这一观点直指文学评价的核心 —— 应回归作品本身,以文学的标尺衡量作家的成就,而非被身份等外在因素所干扰。 学者张旭东则从另一个维度解读了莫言获奖的特殊意义。他指出莫言并没有兴趣去做一个 “持不同政见者”,也没有表现出脱离中国社会创作的形象。这意味着莫言的创作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他的作品反映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情感世界与精神追求。他拥有一个普通中国人能够享受的权利,也分担着所有人都受到的限制,这种 “融入” 而非 “脱离” 的姿态,让他的创作更具真实性与普遍性。他的作品没有哪一部是在别人的授意之下、按照他人的意志来写的,这坚守了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高密东北乡,这个莫言以故乡山东高密为原型构建的文学地域,并非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与奇幻色彩的文学王国。它是莫言创作灵感的源泉,承载着他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与复杂情感。在莫言的笔下,高密东北乡是一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这里有红高粱如海的壮丽景观,有充满野性与激情的人民,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着悲欢离合、生死歌哭。 高密东北乡不仅是莫言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舞台,更是他表达对历史、文化、人性思考的载体。通过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描绘,莫言深入挖掘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层结构,展现了民间文化的丰富内涵,探讨了人性的善恶、美丑与复杂多变。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英雄豪杰还是普通百姓,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真实的情感,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奋斗、成长,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与生活的真实。 莫言提出的 “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 这一创作理念,犹如一把独特的钥匙,开启了文学创作中人物塑造与生活反映的新大门。在他的作品里,这一理念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余占鳌,这位活跃于高密东北乡的人物,身上汇聚了人性的复杂多面。他是土匪,有着土匪的蛮横与不羁,行事作风带着草莽的野性。在传统的认知里,土匪无疑是 “坏人” 的代名词,他们烧杀抢掠,为祸一方。然而,余占鳌绝非简单的 “坏人” 形象。当外族入侵,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毅然挺身而出,带领着兄弟们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 从 “把好人当坏人写” 的角度来看,余占鳌即便在抗日的正义行动中,也并非完美无缺的英雄。他的性格中依然有着冲动、鲁莽的一面,在处理一些事情时,常常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和情绪,而缺乏深思熟虑。他的土匪习性也并未完全消失,有时行事手段依然带着江湖的匪气。这使得他区别于传统意义上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更加贴近真实的人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都是有缺点和瑕疵的,即便是英雄也不例外。 而 “把坏人当好人写” 在余占鳌身上同样得到了体现。尽管他曾经以土匪的身份在社会边缘生存,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有着自己的道德准则和正义感。他对朋友重情重义,对乡亲们也有着朴素的情感,他的 “坏” 并非是纯粹的恶,而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生存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对人物的多面塑造,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物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复杂的人性。 至于 “把自己当罪人写”,莫言在创作中,通过余占鳌的视角和经历,深刻地反思了历史、人性和社会现实。余占鳌在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和生活的磨难后,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他对自己曾经的行为、对战争带来的破坏和伤亡,有着深深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更是对整个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的反思。莫言通过余占鳌这一人物,将自己代入到历史的情境中,以一种忏悔和反思的态度,审视着人性的善恶、美丑,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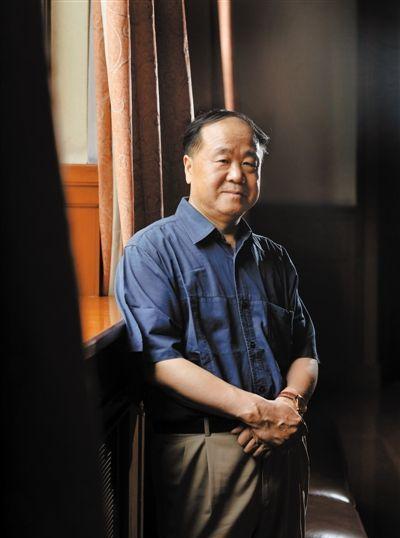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