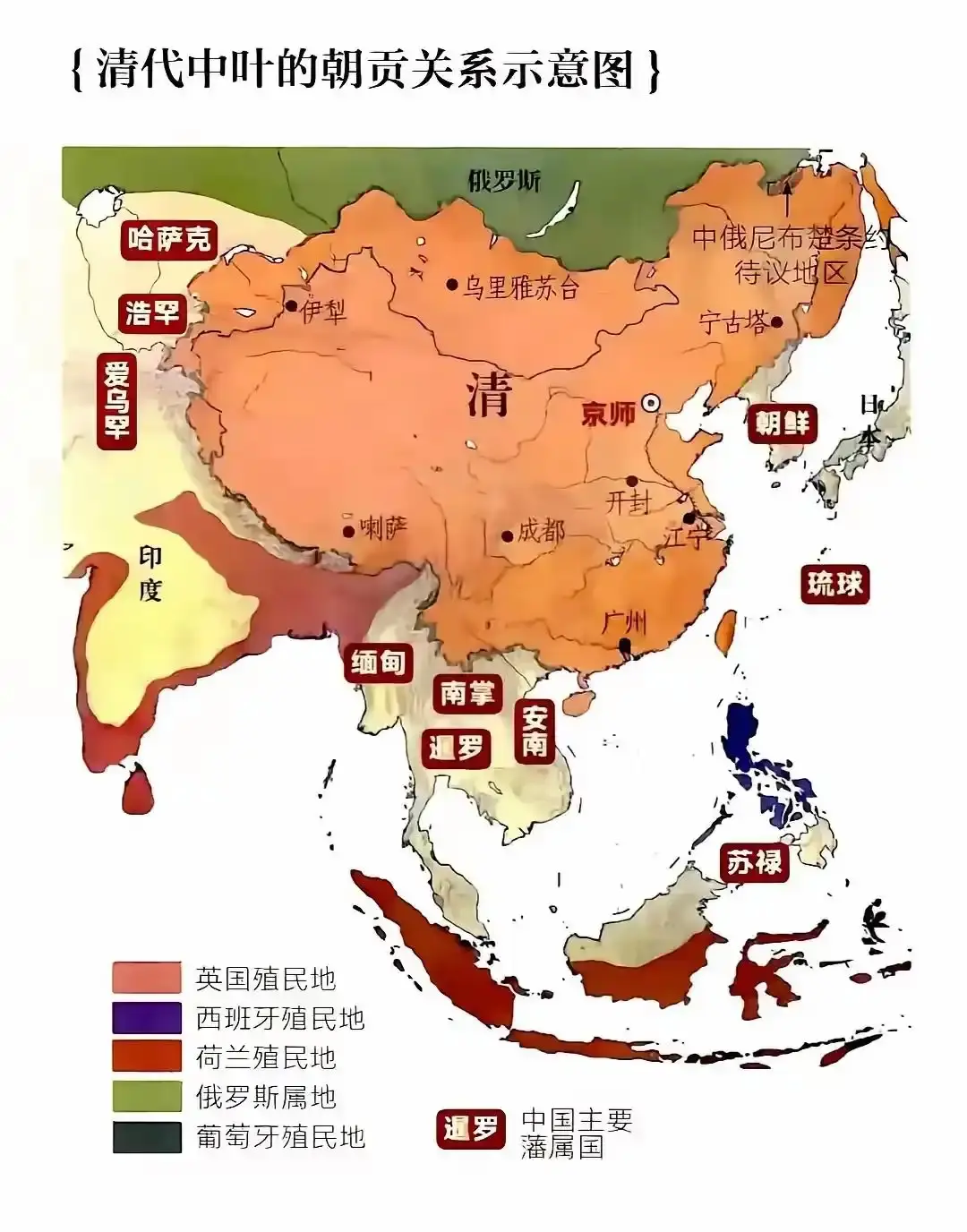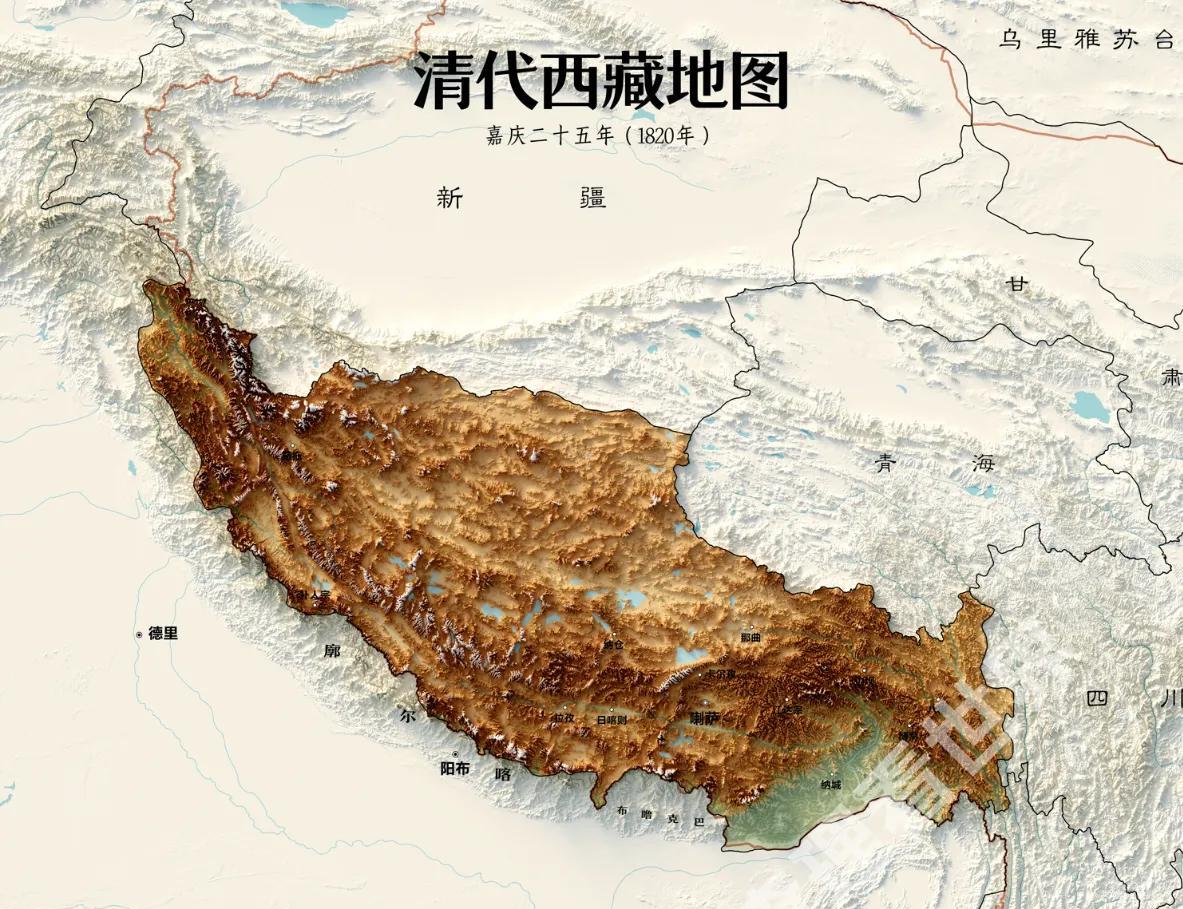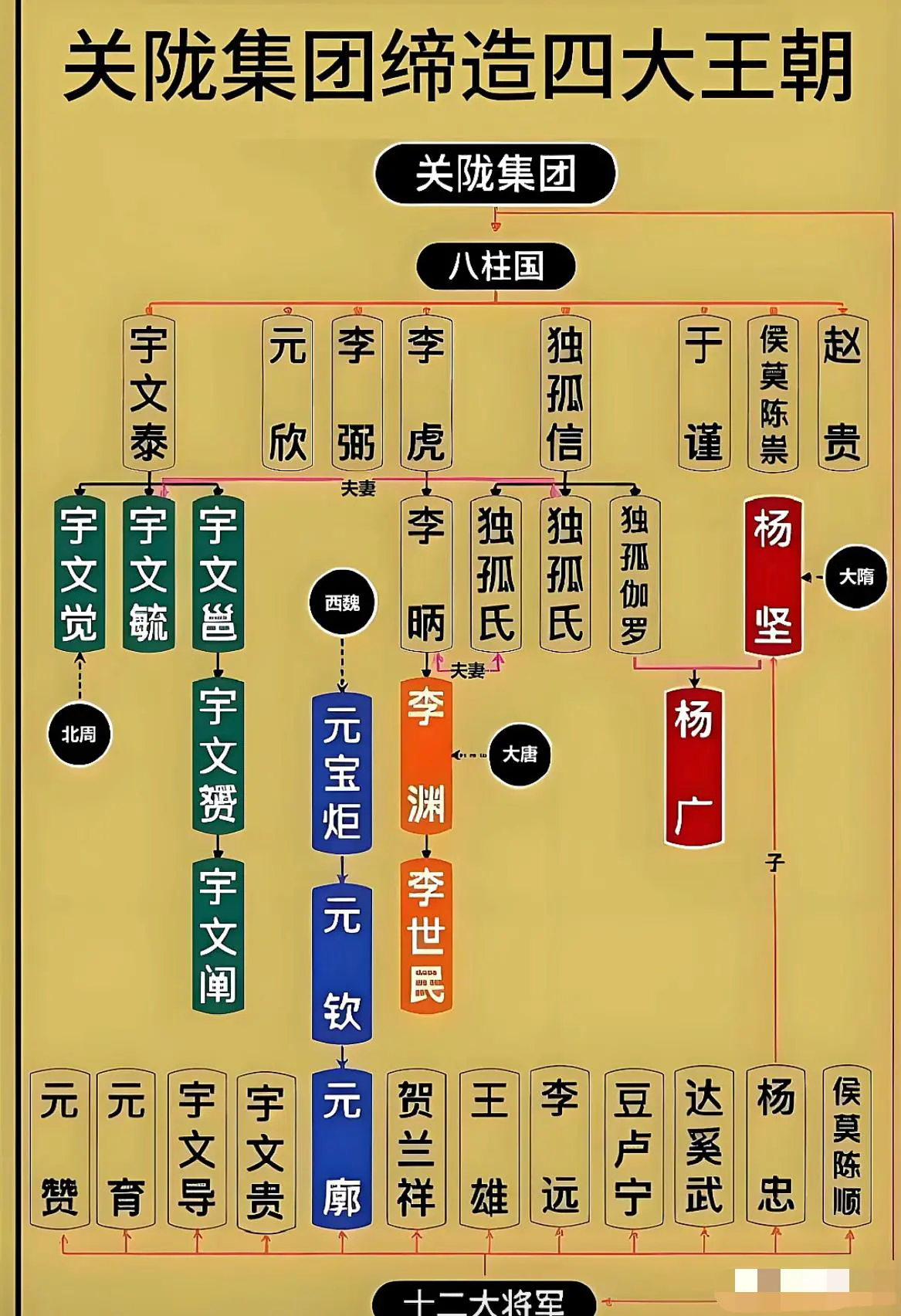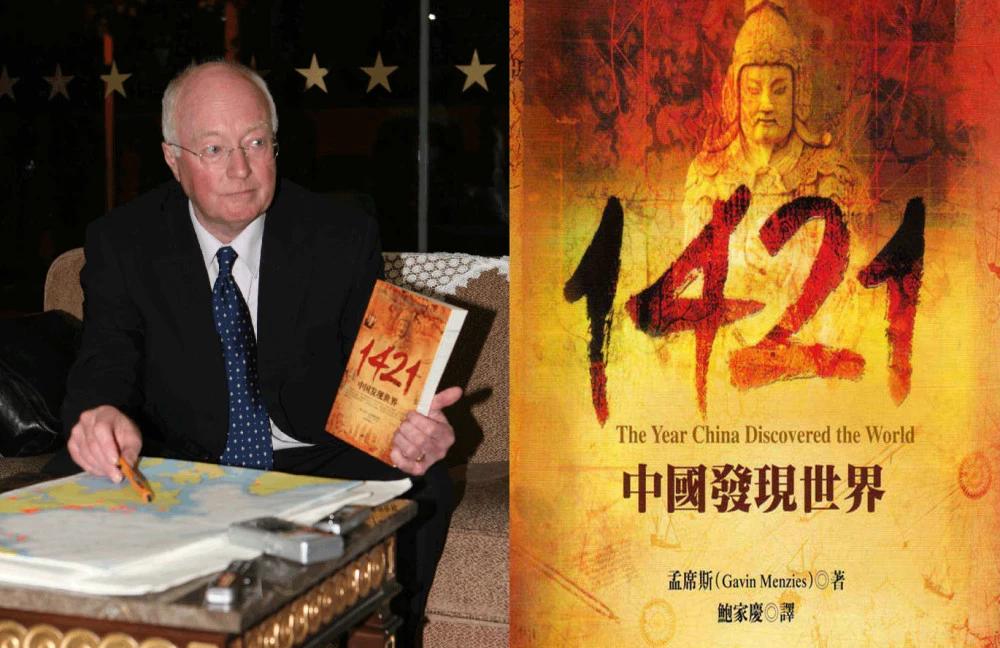西方历史可以被质疑,但东方的“阿拉伯帝国”“萨珊波斯”也不能被随意抹去。今天,有声音说这些只是“中国史籍捏造”,但事实并非如此。大量史料、文本和考古证据铺陈其存在。要彻底推翻它们,你得同时否定《旧唐书》《新唐书》里的“大食”“卑路斯”“波斯都督府”。那些文字不是凭空生成,而是当年使节互访、战争纪事留下的痕迹。 不少人只盯着西方史学的错误,却忽略东方学术地基。有学术去伪存真没问题,但要拿它为由,否定不利己的历史,这就过界。有人把“阿拉伯帝国”说成是伪构,把“萨珊波斯”降格为戏剧台词,这不是怀疑,而是动摇历史体系的基础。 先说文本层面。《旧唐书》《新唐书》都有“西域传”“小宛列传”涉及这些外族。据记载,阿拉伯帝国(书中称“大食”或“黑衣大食”),曾遣使来朝,报朝贡与冲突。波斯被称为“卑路斯”,曾设“波斯都督府”,管理在中亚高加索一带的通商往来。这些记载出现在中国官方史书里,不是民间传闻,而是官方编纂的正史。要否定这些,你得解释为什么当时有专人负责记录这些交往。 再来看中亚战争。几次阿拉伯帝国对拜占庭的战争,被《旧唐书》《新唐书》以战绩、战俘录入史书,如怛罗斯之战、君士坦丁堡之围等多场战役。这些记载不是篡改,而是一种跨文明的历史证据。历史于此出现交集,也给我们提供对照。要抹去这些事件,不是推理问题,而是整体否定历史交会的可能。 不仅如此,萨珊波斯的存在,不仅在中国史里,还有罗马、拜占庭的史料记载,以及后世阿拉伯教史中的遗录。它存在于多条交叉证据中。有人说这是“被西方制造”的说法,也有人说是东方自己编出来的。这两种说法,结构同样脆弱。因为它违背了人类史料交叉验证的基本原则。 我们可以从考古层面再验证。中东与中亚、东亚间贸易频繁。丝绸之路沿线出土大量波斯制造的陶器、金属器、钱币,还有带铭文字母的徽章。唐朝宫殿遗址中,发现波斯式图案的壁画。同样,阿拉伯时期的硬币和陶瓷也在中国西北遗址反复出现,说明了长期的经济与文化往来。这些实物,不是某一方编出来的概念,而是具象的历史证据。 再加上那“波斯都督府”的设立。唐代在中亚曾设立对外管理机构,叫“安西都护府”“波斯都督府”“大食都督府”等。《新唐书·西域传》对其权力范围、官员名录、征税制度有详细记载。它们不是一笔带过,而是逐条记录。如果这一切都是编造,为什么史官会详细记录各地事务?为什么没有当时国内对此质疑或否认?这背后反映的是唐朝中央对这些远地事务的认知与关注。 有人质问说:“西方历史可以探讨,东方历史就不能质疑吗?”这是把“质疑”当成任意翻桌的借口。质疑有度,有方法。你得有证据,有对比,有逻辑。如果没有实证,就不叫质疑,而是制造混乱。你不能因为东方史书里也有“帝国”、“都督”,就一概否定它们的真实存在。 只有发出这些未经考证的“东方帝国伪史论”,才能把《旧唐书》《新唐书》里记录的大食、卑路斯、波斯都督府定义为幻觉,但这本身就是对史书和考古成果的双重否定。这样的态度,不是严谨学者的工作,而是意识形态驱动下的火力试探。 是谁告诉我们,历史只能被东方人制造,而文明只能由东方人验证?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世界史就成了一个任由人随意裁剪的杂烩。罗马灭亡、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拿破仑战争、美国独立,这些都可以被取消吗?答案显而易见:不可以。 回到“有度”二字。我们可以挑战历史传统,但挑战得有依据。比如有人指出,《旧唐书》里关于“乌孙”“回纥”的记载有异,这可以作为研究切入点;但要说阿拉伯帝国、萨珊波斯不存在,就必须推翻大量文字与考古证据,这远不是换个观点就能得出的结论。 实际上,更高级的历史工作,是在跨文明边界里建立联系。看到史书中“大食来使”“卑路斯都督府”,并去考古现场验证;看到丝路遗迹里的瓷器和硬币,并回读《旧唐书》《新唐书》的记录。 这过程不是否定历史,而是与历史握手。它是建立在史料互证与文化认同上的桥梁,而非摧毁。 真正的历史学家,不会选边站,也不会随口翻桌。中国的史书,西方的史料,还有其他文明的记载,都是真实历史的碎片。 今天,我们再提《旧唐书》《新唐书》,用它们的记载证明大食与卑路斯存在,这不是复古,而是一种责任。它提醒我们: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史书如果不能互证,考古不能验证,史料就失去它存在的价值。批判,应该来自对史料全面理解后的理性判断,而不是一念之间的情绪举动。 历史要有厚度,也要有宽度。东方史与西方史,都在同一条时间轴上。我们可以治愈北欧史的偏差,也可以修正中国史的遗漏,但不能把质疑当武器,让历史变成一地分裂话题。 今天,我们修复的,不只是史书,也是一种理性态度。愿后人读史,不只是挑刺,而是思考。西方可以质疑,但东方也值得敬重。在这条路上,我们该有度,也要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