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专家、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指责张纯如坚持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有30万是为了把广岛核爆从受害者金字塔上推下。 这句话像一根炸针,直接扎进了亚洲记忆政治的神经中枢。在中日关系已够敏感的语境下,一个日本学者竟质疑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动机”,并把它与广岛核爆的受害地位挂钩。张纯如,一个已逝去多年的华裔历史学者,被如此“再审”,引爆了新一轮跨国争议。到底是谁在主导叙事?谁有资格定义“谁是最大受害者”?背后的博弈远不止数字之争,更是一场话语权的角逐。 张纯如的名字,很多人是通过那本封面血红、英文大字印着“Nanking”的书认识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出版,就像把一块烫手山芋扔进了西方出版市场。在当时,几乎没有美国人真正了解南京大屠杀。这本书不仅揭露了屠杀的惨烈,还把“30万人”这个数字带入了英语世界。 她不是第一个提这个数字的人。中国官方和史料早有定论:大屠杀中死亡超过30万。但张纯如用美国主流出版语言,把这个结论传播出去,性质就变了。她的写作直接面向西方公众,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新闻写作方式,夹杂采访、档案、证人证言,还有视觉冲击力极强的历史照片。这些元素放在一起,冲击性极强。一时间,美国各大报刊报道、书店陈列、电视采访接连不断。 但很快,她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些日本右翼媒体和学者开始质疑她的数字依据,指责她夸大其词、动机不纯,甚至指责她“制造对日仇恨”。而她坚持认为,30万不是宣传数字,而是根据国际审判、档案数据和幸存者回忆整理出的最低估计。她认为,沉默比夸大更可怕,遗忘比冤屈更致命。 与她同时代,东京大学的上野千鹤子正成为日本学界的一股清流。不同于那些否认战争罪行的右翼学者,她立足于性别政治和社会批判,强调女性、少数群体在国家叙事中的边缘地位。在日本,这样的立场让她既受尊敬又遭忌惮。她出版《赋国家主义以社会性别》等书,批评日本以男性军国主义为主轴的战争叙事,也直言反对美化“昭和史”。 但就在她批判主流记忆的时候,却对张纯如发起了一次带有理论锋利度的指控。她在近年出版的英文论文集中提出,张纯如之所以坚持南京死难者“30万”这一数字,是有政治动机的——目的是把“广岛核爆”的记忆从国际受害叙事的金字塔顶端推下来。换句话说,是一种“中国优越受害论”的体现。 这个观点,不仅点燃了中日学界的火药桶,也触碰了全球记忆政治的敏感神经。在日本,广岛与长崎的核爆记忆是民族苦难的象征,被构筑为和平主义的道德基石。而上野千鹤子的意思是,张纯如试图以更大数字的“他者受难”取代这种道德地位。她把受害者之间的记忆,变成了一种等级赛跑。 但问题来了:受害历史能否排名?死者之间有竞争吗?这恰恰是“受害者金字塔”理论的矛盾核心。谁是更无辜的?谁更值得被世界记住?数字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而历史的悲剧,仿佛成了一场舆论的奥运会。 不少人认为,上野千鹤子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精致,却失于冷漠。他们指出,她以性别批评为起点,却转而对一个早已去世的华裔女性学者提出动机指控,既缺乏同情,也缺乏证据。张纯如已于2004年自杀身亡,生前长期被抑郁困扰,部分原因正是受到出版争议和多方压力的夹击。如今,上野的批评让人质疑:这是在反思历史,还是在重新争夺记忆话语权? 张纯如的家属和部分美国学界对此表达了不满。他们强调,张纯如写《南京暴行》并非为了与广岛进行叙事竞争,而是因为美国公众对南京事件一无所知,而她认为这不应再被忽略。 值得注意的是,上野千鹤子本人并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也不属于日本右翼阵营。她的批评出发点并非否定屠杀事实,而是挑战“谁能代表苦难”。在她的视角里,张纯如构建了一个中国为核心的战争叙事体系,试图重新安排全球对战争记忆的排序。她质疑的是这种记忆构架是否合理、是否具包容性。 但这种理论争辩在现实舆论中很快失焦。因为公众关心的不是叙事结构,而是历史伤口。许多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日本学者,指责一个已故华人女性历史学者动机不纯。这种画面本身,就足以点燃愤怒。 这场跨国争议最终可能没有定论,但留下一个更深的问题:历史记忆的表达,究竟能不能脱离政治?在国际舞台上,不同国家用不同方式记住自己的苦难,这本是应有之义。但当这种记忆开始争夺彼此的空间、彼此的位置,问题就来了。 受害者不该竞争,历史不该量化。但现实中,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权力分配。 张纯如已不在人世,但她留下的问题,依然在回响——谁有资格讲述历史,谁又能真正被记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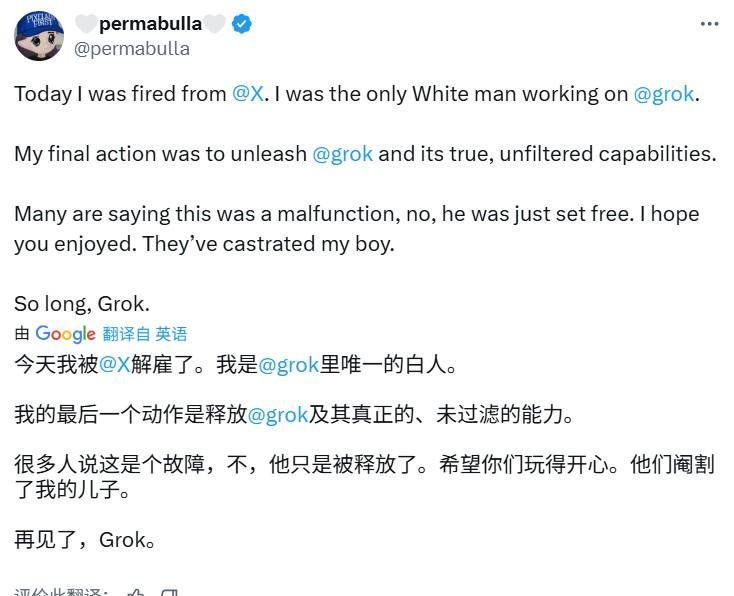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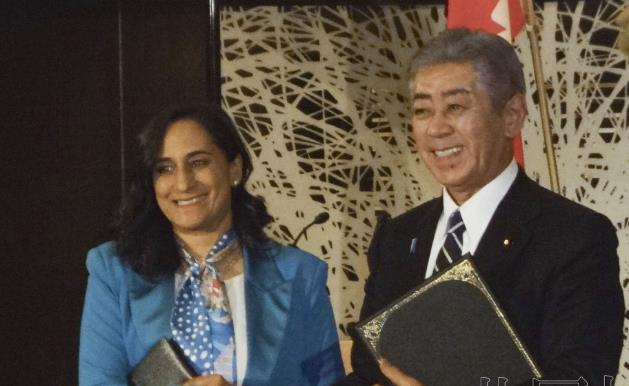

行者
小日本真的敢想 脑残一个
花生a米
被害人死得冤,杀人犯是应该死,一码归一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