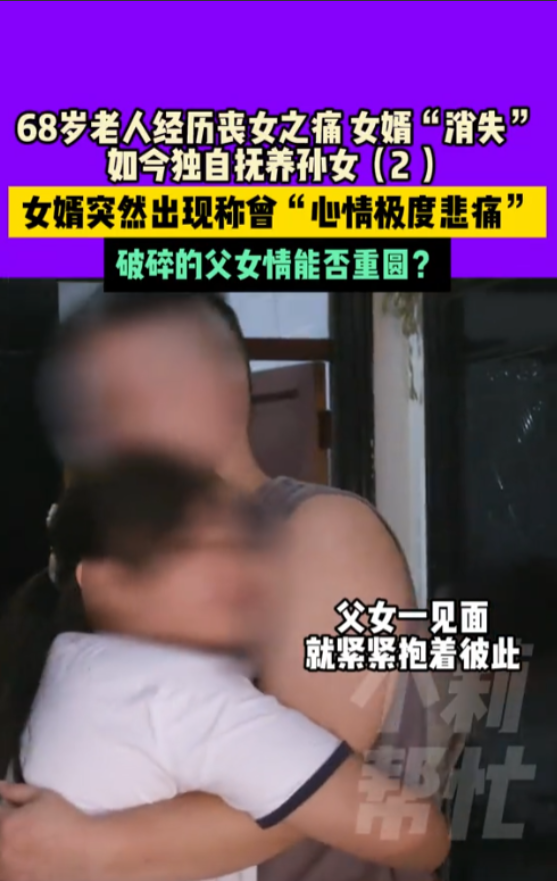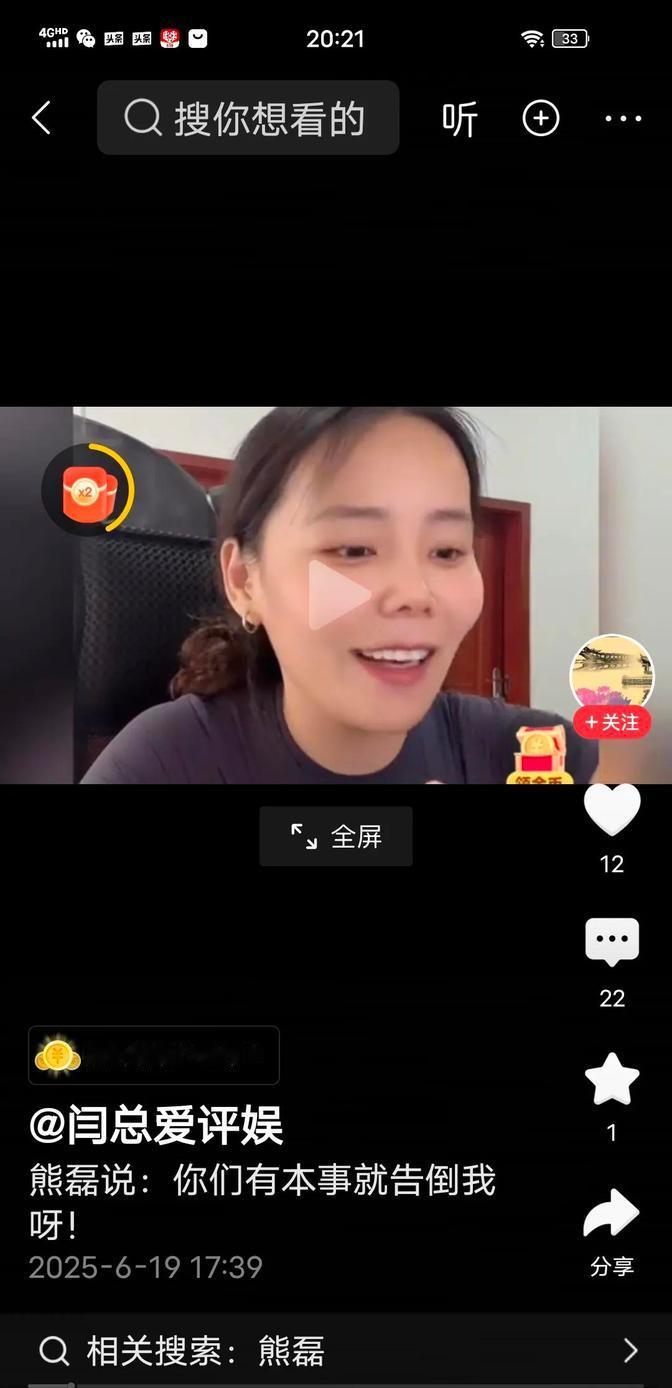公元445年,范晔因谋反被押入死牢,等候问斩。 死牢的墙根渗着水,潮气裹着霉味钻进鼻腔,范晔却浑然不觉。他盘腿坐在稻草上,指尖在地上划着什么,砖块上的凹痕被磨得发亮——那是他这几日用指甲刻下的《后汉书》篇目,从《光武帝纪》到《列女传》,一笔一划,倒比在书房写得更用力。 狱卒送饭来的时候,木碗在石地上磕出闷响。“范大人,还在写呢?”这狱卒曾在太学当过长史,听过范晔讲《汉书》,那时的范大人穿着锦袍,手持玉柄麈尾,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哪像现在这般形容枯槁,囚服上还沾着审讯时的血渍。 范晔抬头,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他没接那碗糙米饭,只是指着地上的“皇后纪”三个字:“你看这里,阴丽华当年辞后位时说的‘不足以当大位’,其实是懂刘秀的心思。帝王家的情分,从来都掺着算计。”狱卒没敢接话,他知道这位大人写《后汉书》时,为了考证一个典故,能在秘阁泡三个月,如今却要带着满肚子的史事赴死。 想起二十年前在彭城,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跟着父亲范泰在刺史府读书。那时他总嫌史书太枯燥,偷偷在《三国志》的空白处画小人,被父亲发现了,用戒尺打手心,却又连夜给他抄录秘阁里的孤本。后来他入了仕,官至太子詹事,最风光的时候,拓跋焘握着他的手说:“卿的史笔,能让百代之后的人看清本朝的模样。” 牢门外传来脚步声,是中书令袁淑。这人捧着一坛酒,袍角沾着露水,显然是刚从宫里赶来。“蔚宗,陛下允了,让你留份遗书。”袁淑把酒坛推给他,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查了,那些所谓的‘谋反书信’,笔迹是伪造的。” 范晔拔开酒塞,醇香混着霉味涌出来。他仰头灌了一大口,酒液顺着下巴流进囚服,打湿了胸口的“罪”字。“伪造又如何?”他笑起来,笑声里带着酒气,“我写《后汉书》时,把邓太后临朝称制的旧事写得太细,把那些外戚专权的龌龊抖得太干净,早就有人看我不顺眼了。” 袁淑望着他鬓角的白发,突然红了眼。他想起范晔为了写《宦者列传》,跑遍洛阳城的老巷,跟退休的老太监喝酒聊天,回来时醉醺醺地说:“这些人,史书里只写他们坏,可谁知道他们刚入宫时,也是爹娘疼爱的孩子。”那时的月光洒在他脸上,眼里的光比酒还亮。 “帮我把这个交给史馆。”范晔从怀里掏出块皱巴巴的绢布,上面是《后汉书》的最后一篇“自序”,字迹因为手抖有些歪,却依旧有力,“告诉他们,‘志’这部分我没写完,让他们找个靠谱的人续上。”他顿了顿,指尖划过绢布上的“班彪续《史记》,吾续《汉书》,皆是为了不让往事如烟”,突然咳嗽起来,咳出的血滴在绢布上,像朵开败的红梅。 行刑那天,洛阳城飘着细雨。范晔穿着干净的素衣,是袁淑悄悄送来的。他站在刑场中央,望着远处的邙山——那里埋着无数帝王将相,他写过的那些人,如今都成了黄土下的枯骨。监斩官读完圣旨,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 范晔清了清嗓子,声音在雨里传开:“昔司马迁受腐刑而著《史记》,范晔今日赴死,能留《后汉书》于世间,足矣!”他没提冤屈,没骂奸臣,只是挺直了脊梁,像当年在太学讲史时那样,目光望向远方。 刀光落下时,有人看见他怀里的绢布飘了起来,上面的字迹在雨中慢慢晕开,最后只剩“史笔如刀”四个字,被雨水冲刷着,渗进洛阳城的泥土里。 参考书籍:《宋书·范晔传》《南史·范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