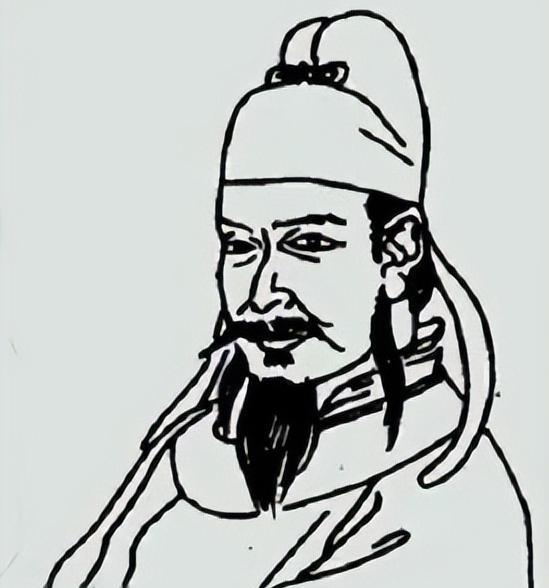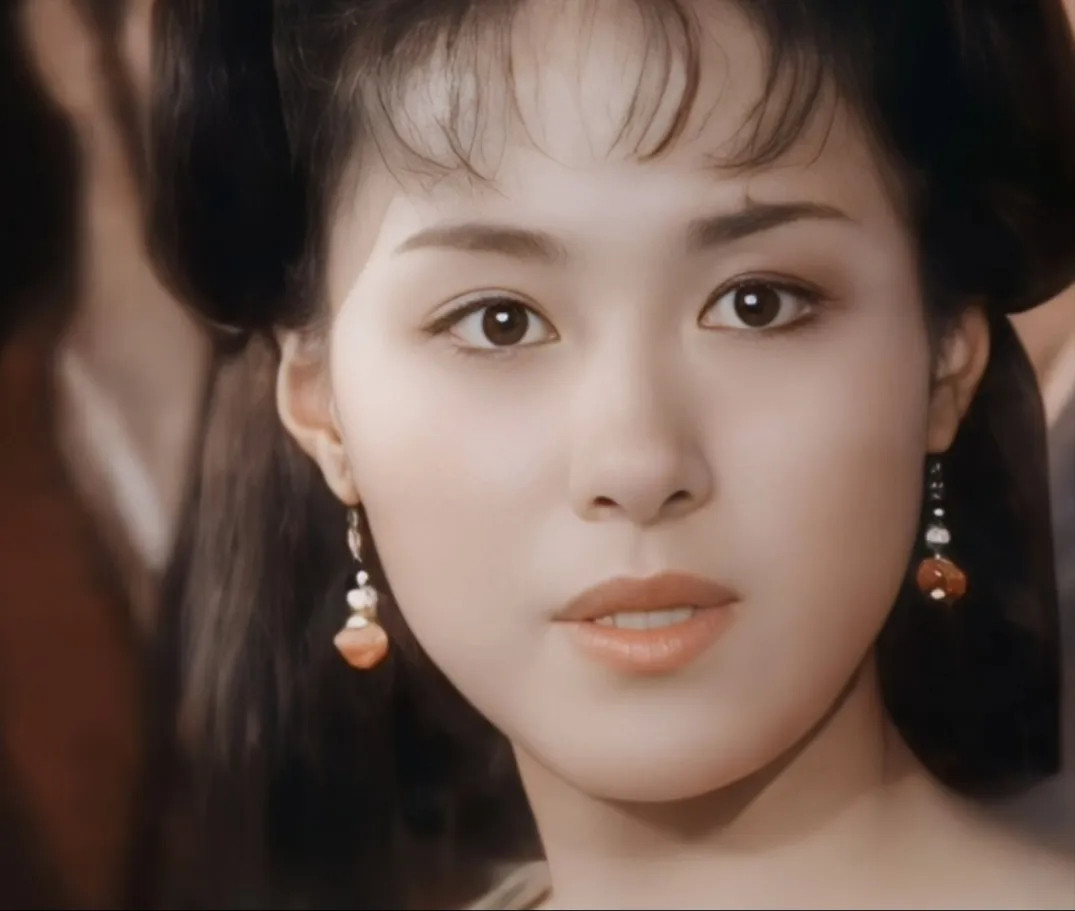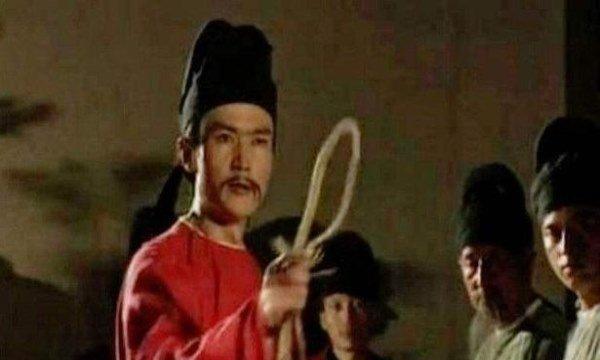公元652年,武则天正准备就寝。突然窗外飞入一个纸团,上面写道:“三更后,我来你寝宫。”三更后,写信人如约而至,来人正是徐士杰。 武则天斜倚在紫檀木榻上,鬓边金步摇随着呼吸轻轻晃动。烛火在她眼角的细纹里游移,映得那双总是含着锐气的眼睛,此刻竟有了几分松弛。“徐大人深夜到访,就不怕禁军把你当成刺客?”她的声音里带着笑意,指尖却无意识地绞着丝帕。 徐士杰刚褪去沾着夜露的外袍,闻言躬身行了个不似朝会那般拘谨的礼。“娘娘寝宫的烛火,比太极殿的宫灯暖得多。”他抬眼时,烛光恰好落在他鬓角新添的白发上,“臣今日在吏部看到新科进士的名册,有个叫郭正一的年轻人,策论里写‘治天下如烹小鲜’,倒让臣想起当年娘娘在感业寺时,给臣煮的那碗野菜粥。” 徐士杰那时还不是什么“大人”。 只是个不得志的起居舍人,常被长孙无忌一派排挤。武则天在感业寺为尼时,他借着上香的由头,偷偷给她送过几次佛经,有时是半块干饼。有回落了大雨,他被困在寺外的山亭,是武则天揣着一碗热野菜粥找过来的,粥里飘着几粒糙米,她说是偷偷从厨房攒的。 “那粥可真难吃。”武则天忽然笑了,眼角的细纹堆起来,倒添了几分柔和,“菜根没切细,硌得慌。” “可暖。”徐士杰也笑,“那天臣淋了雨,差点发起烧来,喝了那碗粥,竟好了。” 烛火噼啪响了一声,屋里静了静。 谁都没提这几年的变故。没提武则天如何从感业寺重回后宫,没提她斗倒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没提徐士杰如何在朝堂上不动声色地为她说话,成了她暗中的助力。 “郭正一……”武则天转了话头,指尖松开丝帕,“此人策论我看过,字里行间有锐气,但不鲁莽,是个可用之才。” “娘娘看得准。”徐士杰点头,“只是他出身寒门,朝中无人举荐,怕是要被埋没。” 武则天端起桌上的茶,抿了一口,茶早凉了。“你想保他?” “臣想保的不是他。”徐士杰直视着她,目光坦诚,“是想让娘娘身边,多些能说真话的人。长孙大人那些老臣,眼里只有祖宗规矩,哪管百姓死活?” 这话戳到了痛处。武则天放下茶盏,指尖在微凉的盏壁上划过。她太清楚了,那些世家大族盘根错节,李治虽为天子,有时也得看他们脸色。她要往上走,要的就是郭正一这样没根基、只认才干的人。 “你倒是会给我找事。”她语气里带着嗔怪,眼里却亮了,“明日让他来太极殿外候着,我自会让陛下见他。” 徐士杰松了口气,起身要谢,却被武则天拦住了。 “谢就不必了。”她看着他鬓角的白发,想起当年那个冒雨送佛经的青年,“只是徐大人,深夜入后宫,传出去对你我都不好。” 徐士杰明白她的意思。这宫里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旧情是软肋,也是把柄。 “臣明白。”他重新穿上外袍,袍角还带着湿气,“只是有些话,在朝堂上说不得,只能夜里来叨扰娘娘。” 他走到门口,又停住了。 “娘娘当年在感业寺说,‘若有朝一日能出去,定要让天下人看看,女子未必不如男’。”徐士杰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臣信娘娘能做到。” 武则天没说话,只是望着跳动的烛火。那火苗忽明忽暗,像极了她这些年走的路,一步踏错,就是万丈深渊。 徐士杰轻轻带上门,脚步声很快消失在长廊尽头。 武则天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月光冷冷地洒在宫墙上,墙头上的禁军握着长矛,影子像钉在地上的桩子。她知道,徐士杰这趟来,不止是为了郭正一,更是在试探她的决心,也是在表他的忠心。 深宫之中,所谓的情谊,从来都和算计缠在一起。 她想起那碗野菜粥,想起徐士杰当年冻得发红的鼻尖,又想起明日要见的郭正一,想起朝堂上那些虎视眈眈的眼睛。 指尖又开始发凉,她拢了拢衣襟。 “来人。”她对着门外唤了一声,“把那盏凉了的茶换了,沏壶新的龙井来。” 有些路,一旦踏上,就不能回头。她需要郭正一这样的新锐,也需要徐士杰这样的旧友,但更需要的,是自己手里那把越来越硬的刀。 窗外的月光,终究是冷的。暖人的,从来都是心里那点不肯熄灭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