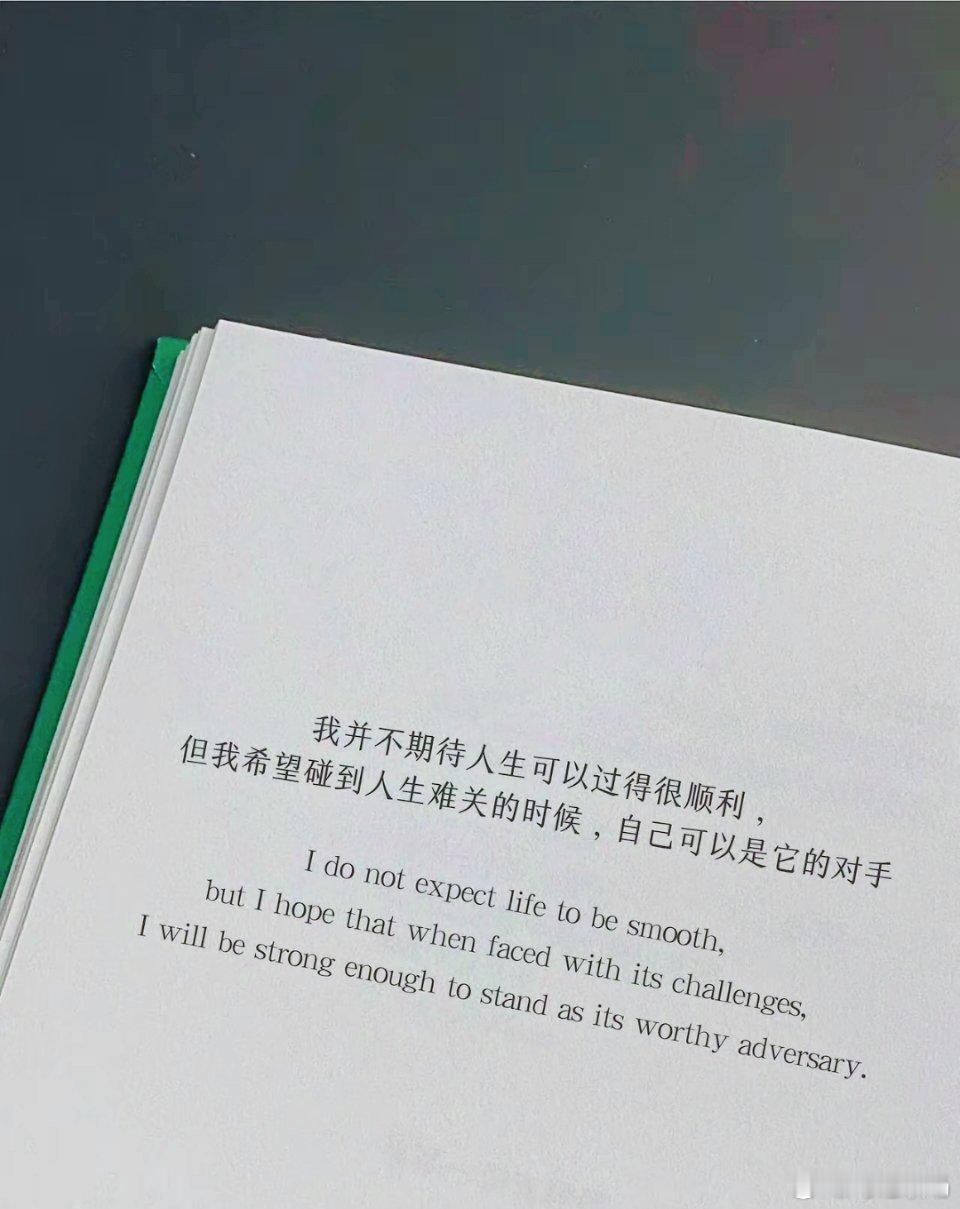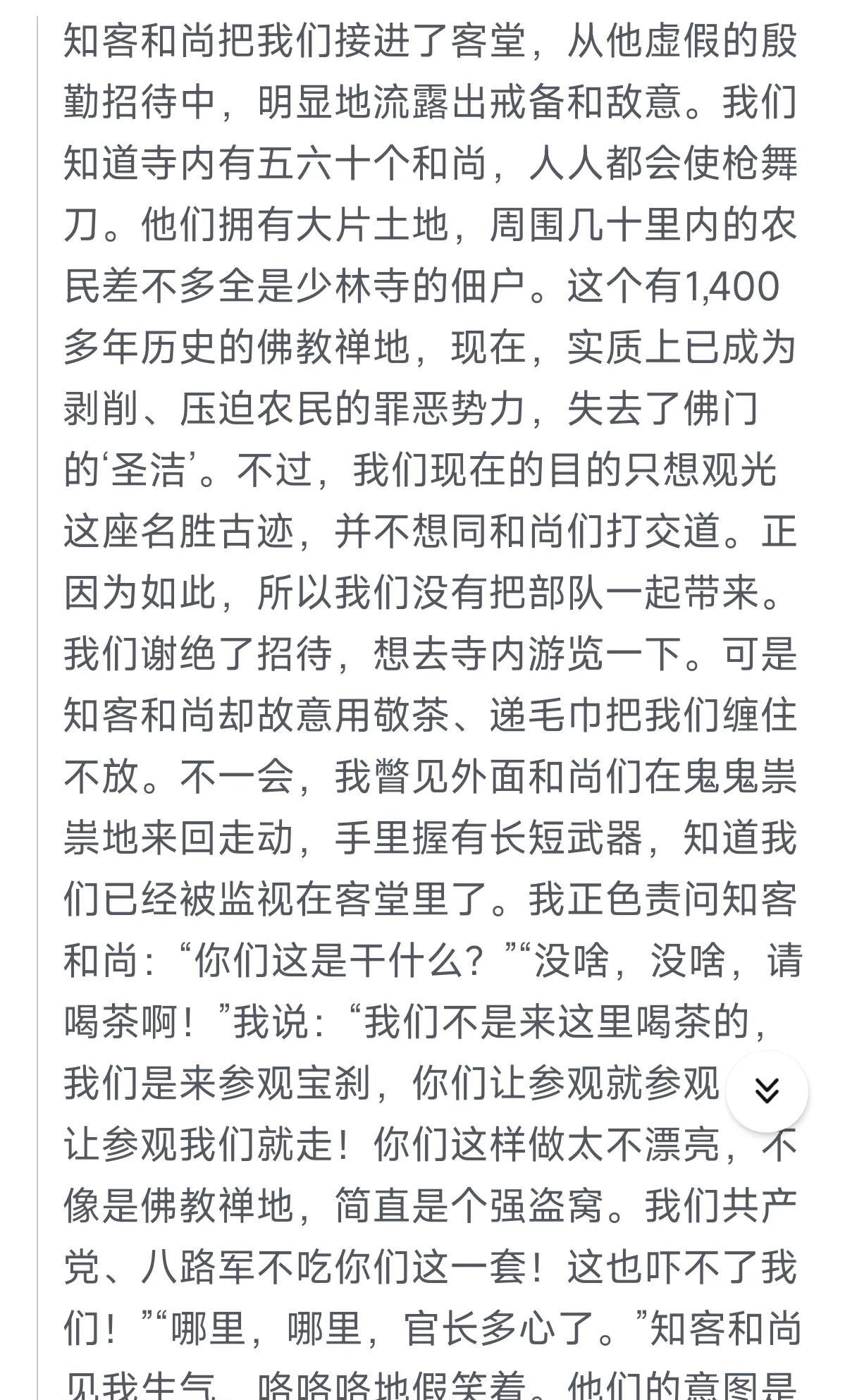风沙漫天,街角的少年蜷在破庙门前,衣衫破旧,手脚冻裂。他才16岁,已经流浪了好几年。家没了,亲人死了,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他想过抢,也想过死。但那天,一个女人走来,拉开衣扣,从胸口摸出一块腰牌,扔进他手里,说:你以后可以进我后院。那块不起眼的腰牌,像是一纸通天符。它不光给了张作霖一个藏身的地方,还成了他翻身的第一块跳板。 张作霖生于1875年,辽宁海城人,家里世代务农,虽穷却能糊口。父亲张有财,能喝、好赌、脾气暴,母亲本分操持,但镇不住这个家。张家有几个兄弟,最亲的哥哥张作泰在一次争执中被父亲误伤致死。张有财受仇家举报,被乱棍打成重伤,不久死去。 从那以后,家就散了。 张作霖跟着母亲四处逃亡,睡窑洞,蹭饭桌,干重活。他年纪小,干不过大人,嘴又不甜,换饭的活儿也难。他学会了偷,学会了瞒,也学会了看人眼色。十几岁时,他几乎就在奉天城头干尽了低贱活计。 那年冬天特别冷。他拖着冻伤的腿,在奉天老北门口打盹儿。周围都是狗和流民。他觉得撑不过去了。可就是这时候,一个寡妇注意到了他。 她穿着粗布棉袄,年纪不大,眉眼精明。她停下脚步看了他一会儿,没说什么,掏出一块腰牌,塞进他手里。张作霖一脸懵。她甩下一句:这腰牌拿着,进我家后院,不许乱跑。 那一年,1891年。他16岁,孙寡妇的腰牌,就是他命里的转向标。 张作霖没让她失望。 他先是在后院帮工,扫地、劈柴、背水,样样干。后来,他被安排去集市上押运货物,跟人吵架、打架、讨账,样样也行。他不是那种守规矩的孩子,但执行力强,有野劲。孙寡妇渐渐放手让他跑腿办事,甚至接触些灰色渠道。 几个月后,张作霖已经成了她家的头号小工。有人欺负他,他当场掀摊子;有人拖账,他夜里砸门。孙寡妇发现他有手腕,有狠劲,也有一股天生的社交直觉——谁能惹,谁不能碰,他分得明明白白。 在她家,张作霖第一次吃饱饭,第一次有了褥子和被子,也第一次知道,原来人可以靠自己活下去,不必永远在街上打滚。他开始蓄头发,学骑马,看风水、识地理,还跟孙寡妇家的兽医学了点看病喂药的本事。 这几年,是他人生最关键的“打基础期”。孙寡妇虽是女人,却是他半个师傅。 1893年,他十八岁,身高体壮,走在街上已有点地头蛇的气势。这时候,张作霖主动从孙家出来。他不想一直当个打杂的,他要自己搞事。 他加入了保险队。那是个介于民团与黑帮之间的组织,管护商道,也干护镖、打仗、抓盗。他进得去,是因为有人推荐。他干得下来,是因为出手快、下手狠,讲义气,也懂规矩。 保险队给了他刀,给了他马,也给了他舞台。他第一次参加“抓山匪”的战斗,冲在最前,抓了人还顺手敲诈了笔银子。他不是天生的军人,但却是天生的“团练材料”。 在保险队里,他学会打枪、识枪,学会带人,学会分账。他和几个同龄人自组“马队”,去辽西跑镖,偶尔也兼接“清帮”或“赌场维持”的活儿。很快,他有了自己的一帮小兄弟,自己说话能顶事。 到1898年前后,张作霖已是奉天一带小有名气的“骑马汉子”。他开始靠自己吃饭,不再依附任何人。他没忘孙寡妇,偶尔还回家给她送米送钱。但他的人生,已经不再只属于她家的后院。 1900年义和团起事,东北局势混乱。张作霖开始真正接触官场。他的保险队受清军招抚,变成地方自卫团。他在一次清剿中立了小功,被提拔为团练统带。 1902年,奉天新民府扩编巡警马队,张作霖带着几十号兄弟报名。他成功转正,穿上官军制服,成了正式编制军人。他没文化,不识军制,但他懂人心。他知道怎么稳住兵,怎么上缴银子,也知道怎么和地方官打交道。 三年后,他成为一地统带。再后来,他吞并周边团练,控制大半新民府。1907年,他已是奉天西部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 而这时,他才不过三十出头。 而一切,始于那年冬天,那块腰牌,那张藏在孙寡妇胸口的通行证。 张作霖后来说过,他欠孙寡妇一条命。但其实,孙寡妇当年也赌对了。她的眼光和她的胆识,换来了一位未来的“东北王”的一生感恩。 张作霖后院起步,江湖起势,官场立足,最终坐上东北之主的位置。这条路,走得不容易。但他从没忘过,第一步是谁让他迈出的。 一个女人,一块腰牌,一段传奇。那一年,他16岁,她寡居。谁也没想到,这场收留,改变了两个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