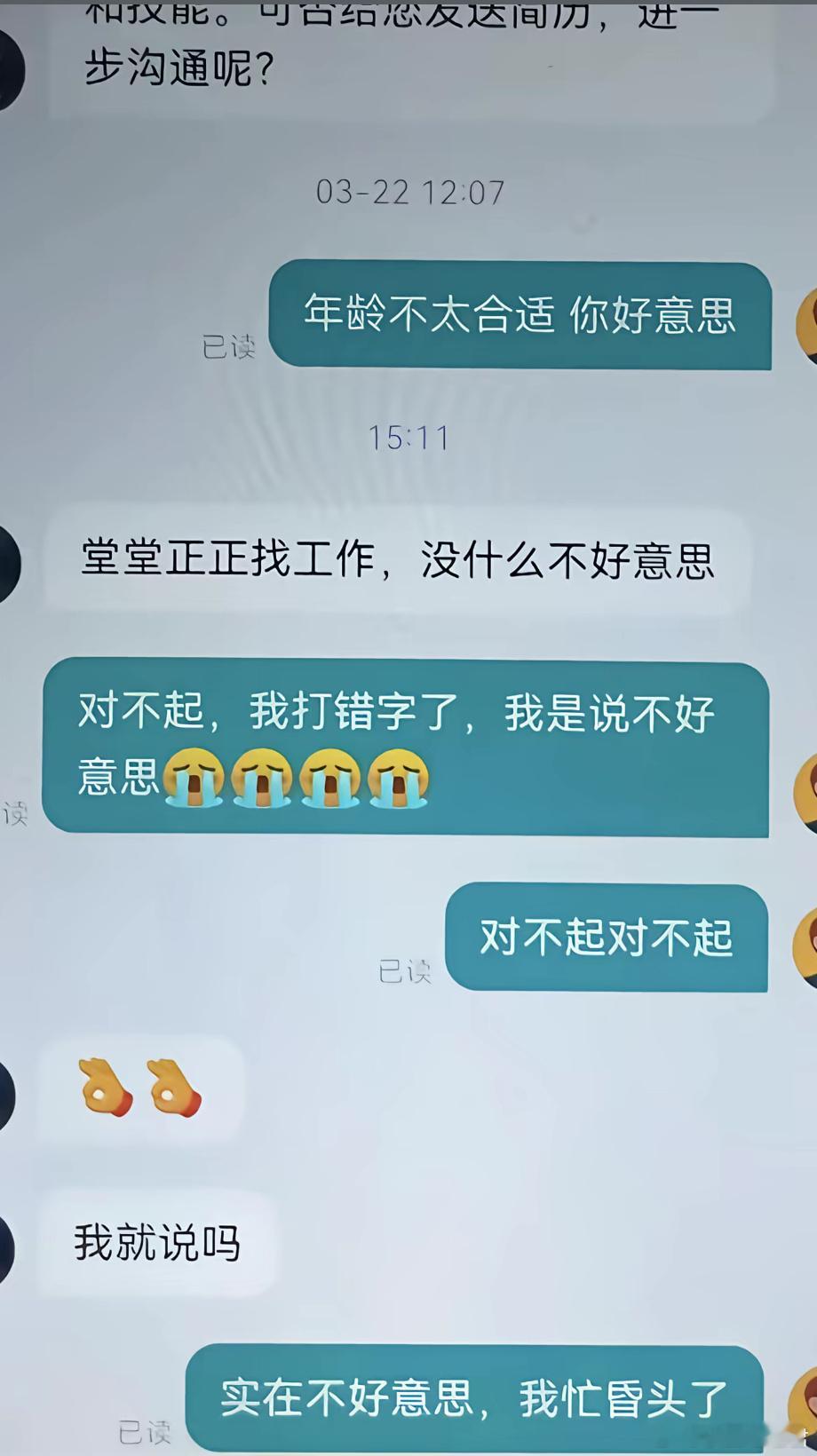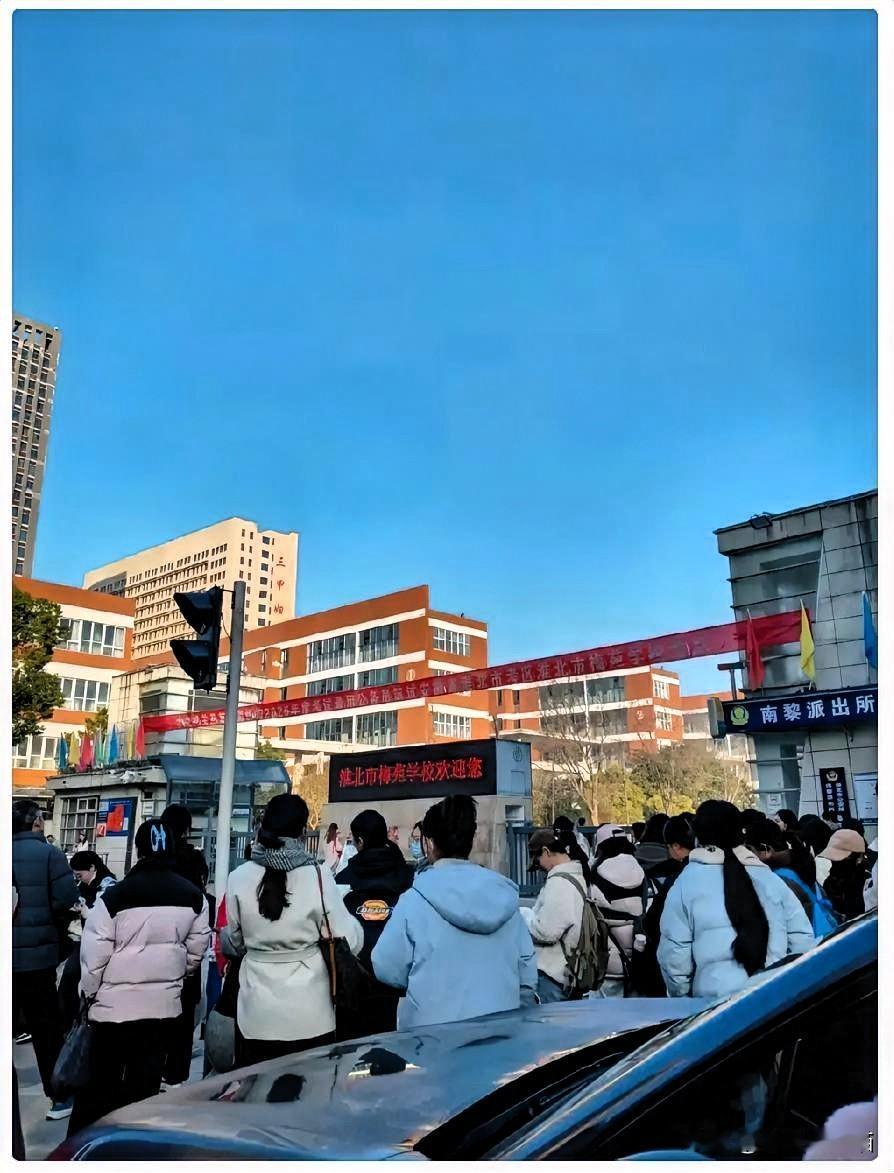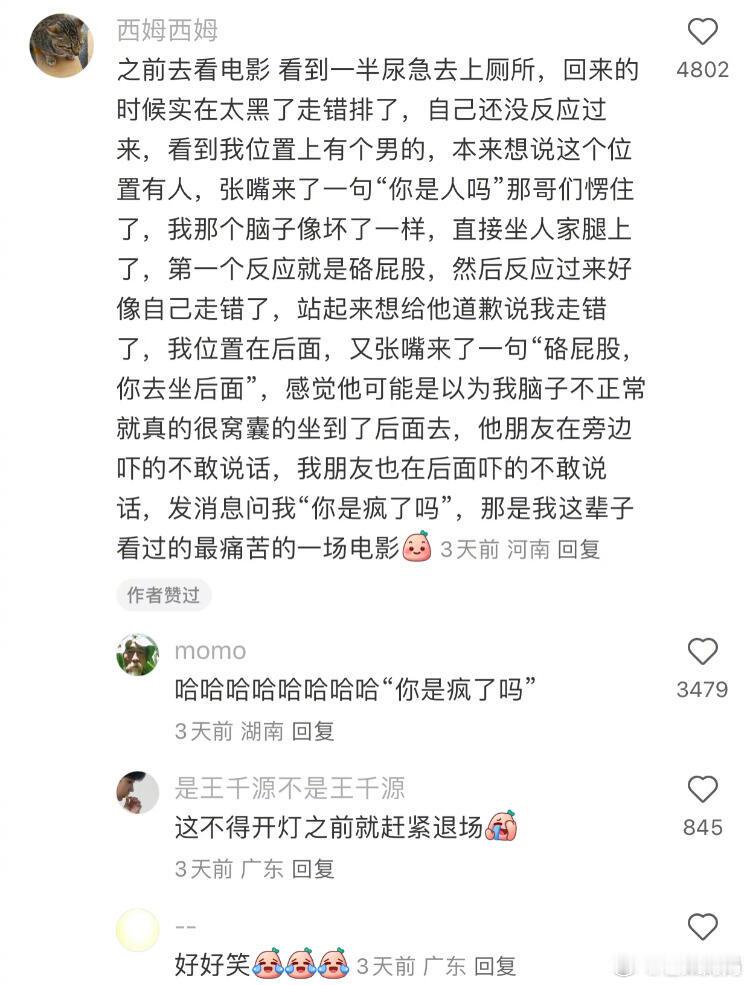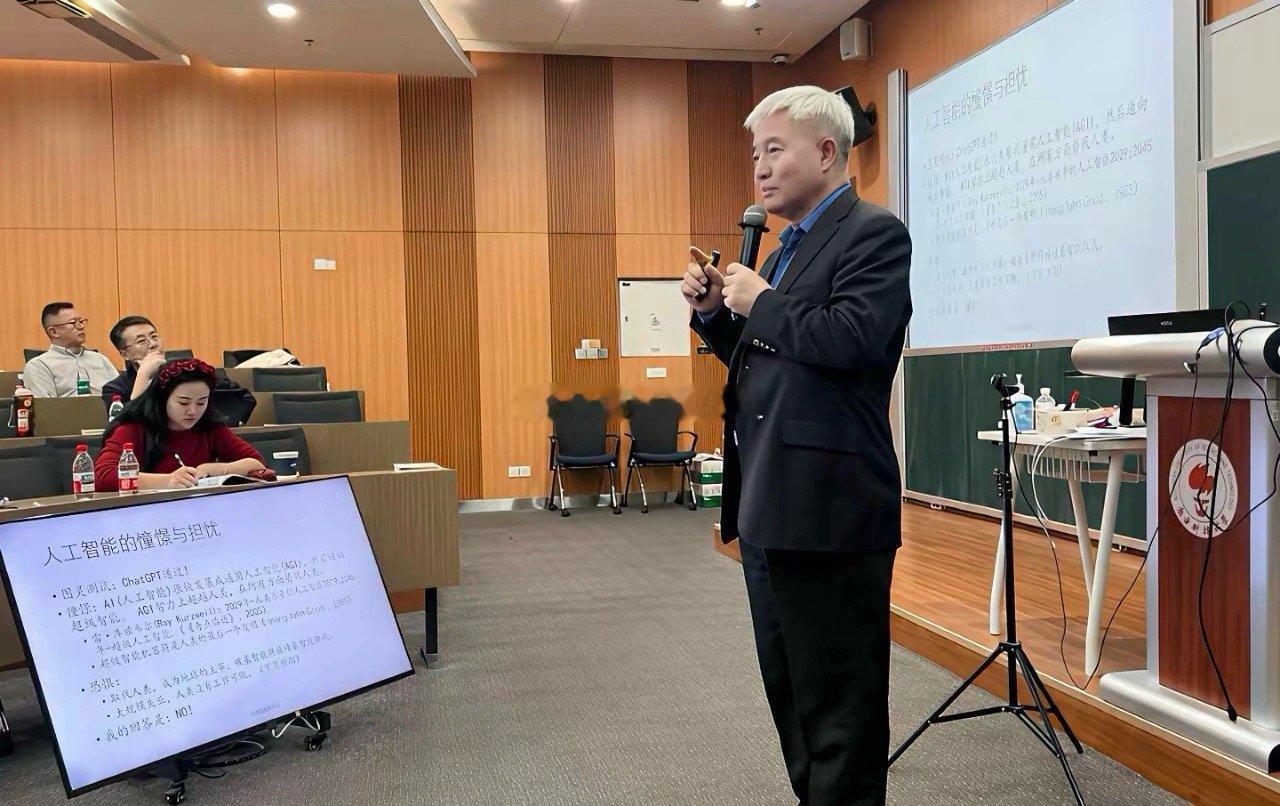选择性视域下美术学去文学化倾向的价值重估 —— 基于华远科学性美论与 AI 语境的对话
作者为华远
写于2005年3月,修改于2025年9月
摘要
现当代美术学领域中,以 “去文学化” 为代表的单线化、平面化倾向,源于对形式自律的追求,却引发 “意义空场” 争议。本文以华远科学性美论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为核心,聚焦其 “选择性” 机制 —— 审美主体在时空维度、物质精神层面、历史文化线索中对信息中介的主动筛选与整合,对话去文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局限。结合 AI 语境下美术创作的形式复制、算法窄化等新问题,引入现当代理论家与评论家观点,通过徐冰《地书》、艾未未《向日葵籽》、奥拉夫・urfe《雨屋》及华远 2008 年《格式化》油画初稿等案例,揭示去文学化的合理边界与价值误区。研究发现,去文学化推动形式语言创新,却因 “选择性” 片面化割裂时空语境与精神意义;AI 艺术进一步消解 “选择性” 主体性,导致审美被动化。唯有以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重构审美逻辑,才能实现形式与意义的良性循环,为 AI 时代美术学发展提供路径。
关键词
美术学去文学化;科学性美论;四维多层多线一元;审美选择性;AI 美学;形式自律;意义生成
引言
自 20 世纪中叶形式主义美学兴起,美术学领域逐渐出现 “去文学化” 理论转向。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提出 “艺术的纯粹性”,主张绘画聚焦平面性、色彩与线条,剥离叙事等文学性内容;极简主义、硬边抽象进一步推进这一倾向,形成单线化、平面化的创作与批评范式。这一转向旨在确立美术独立学科边界,却引发争议:阿多诺批判形式主义陷入 “为形式而形式” 的异化,本雅明担忧机械复制时代艺术 “光晕” 消失。
进入 AI 时代,争议更显复杂。MidJourney、DALL-E 等工具可快速生成符合形式规律的抽象图像,却难复制人类对时空语境的感知与精神意义的注入;算法推荐强化去文学化片面性,使审美 “选择性” 沦为被动筛选。在此背景下,华远科学性美论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提供新视角,其 “选择性” 机制强调审美是主体在 “四维”(三维空间 + 时间)、“多层”(物质、精神、制度、认知)、“多线”(历史、技术、文化、社会)中的主动整合,最终指向 “一元”(良性循环)。
华远创作于 2008 年的《格式化》油画初稿,恰为这一讨论提供了具象实践样本。画面以交错却有序的层线结构,既未陷入单线平面化的刻板 —— 那种仅作为时空定位、缺乏多维度解读可能的 “一层一线” 式表达,也未落入过度文学化的叙事陷阱,而是在抽象与具象、留白与填充间达成微妙平衡。这种平衡让人联想到蒙德里安的抽象作品:长期以来,蒙德里安的格子画常被误解为 “去文学化”“去哲学化” 的极致,实则其线条分割、色彩搭配始终暗含对秩序与和谐的哲学思考,只是将文学性叙事转化为视觉形式的象征。这揭示出美术学去文学化的核心认知误区:去文学化并非彻底剥离艺术中的文学性与哲学性,而是调整其与形式表达的配比,避免美术沦为其他姐妹艺术的附庸。
《格式化》的创作理念更暗合华远科学性美学橄榄型审美结构的核心主张:美术的形式创意需警惕两个极端 —— 既不能一边倒向叙事性文学化,用繁杂故事性淹没视觉语言独立性;也不能走向绝对形式的极端,使作品沦为无意义的线条与色彩堆砌。正如华远所指出的,“过于形式化的去文学化,去哲学化的创作观念,第一个用他的人可能是天才,第二、第三个人可能就是丑才”,这种对 “极端化” 的警惕,正是《格式化》作为去文学化实践案例的价值所在。更值得关注的是,“格式化” 概念从作品延伸至创作主体思维层面时,便显露出深层哲学意涵:在信息爆炸、审美观念多元的当下,创作者的思想也需 “格式化”—— 清除被社会 “病毒” 扭曲的认知偏差,回归艺术创作的初心与出发点。这种 “回归” 并非保守,而是对现象学 “回到事物本身” 理念的呼应,也是美术学去文学化倾向得以健康发展的思想根基:唯有摆脱过度文学化的叙事束缚,才能让美术真正以视觉形式 “言说” 自身价值。
本文研究思路:梳理去文学化谱系与争议,明确问题核心;解析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中 “选择性” 内涵,建立分析框架;诊断去文学化 “选择性” 错位,结合 AI 语境揭示困境与伦理回应;通过跨领域对话(文学理论)深化理论深度;探索 “选择性” 重构路径与实践典范(含《格式化》);最后简述美育实践与未来展望,形成完整逻辑链。
一、美术学去文学化倾向的谱系、争议与问题总结
去文学化是 20 世纪美术自律化进程的产物,谱系可追溯至形式主义,实践表现为图像平面化与叙事剥离,核心争议聚焦形式自律与意义生成的关系,且存在单线化、平面化的固有问题。
1.1 去文学化的理论源头:从形式主义到观念艺术的逻辑延伸
去文学化直接理论源头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 “形式主义批评”。格林伯格在《艺术与文化》中提出 “现代主义本质在于用学科特有方法批判自身局限”,主张绘画 “纯化” 语言,摒弃透视、叙事等文学性元素,专注 “平面性” 这一独有属性。他推崇杰克逊・波洛克的滴画,认为其 “摆脱题材束缚,让线条与色彩自主发声”,为去文学化提供核心逻辑:美术价值在于形式语言自足,而非文学性意义附加。
罗杰・弗莱 “有意味的形式” 进一步强化这一倾向。弗莱在《视觉与设计》中提出,美术审美价值源于 “线条、色彩的组合关系”,而非故事或情感;即便具象绘画,也应转化为 “纯粹的形式结构”。这一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极简主义中达极致:唐纳德・贾德在《特定物体》中宣称 “艺术不应有隐藏意义,它就是它自身”,其金属方块作品仅保留材料、尺寸与空间关系,彻底剥离文学性联想。
需注意的是,去文学化理论逻辑并非单向推进。罗莎琳德・克劳斯在《前卫艺术的新范式》中指出,观念艺术虽延续 “反叙事”,却以 “观念” 替代 “文学” 作为意义来源 —— 如约瑟夫・科苏斯《一把和三把椅子》通过 “实物 - 照片 - 词典定义” 并置探讨 “艺术本质”,排斥传统文学叙事却引入认知意义。这种 “去文学而留观念” 的转向,揭示形式自律与意义需求的内在矛盾。
1.2 去文学化的实践表征:图像平面化与叙事剥离的双重形态
创作实践中,去文学化表现为 “图像平面化” 与 “叙事剥离”,且在不同流派中呈差异化特征。
硬边抽象以 “消解层次” 实现平面化。肯尼斯・诺兰《靶心画》将画布分割为同心圆,以纯粹色彩块面填充,无透视、无笔触、无主题 —— 观众无法读取故事,仅能感知色彩对比与形状对称。诺兰曾表示 “我想让绘画像一面镜子,直接呈现视觉本身,而非通过镜子看背后的东西”,这种 “镜面式” 平面性彻底切断图像与文学叙事的关联。
极简主义以 “物质还原” 剥离叙事。卡尔・安德烈《锌铜平原》将金属板平铺于展厅地面,审美价值仅存在于材料质感、尺寸比例与空间互动中,无人物、场景或象征意义。哈尔・福斯特在《极简主义的批判》中观察到,“安德烈的作品拒绝任何‘解读’,它要求观众仅用身体感知 —— 踩在金属板上的触感、视线扫过平面的视觉节奏,而非用大脑联想故事”。
当代数字绘画中,去文学化进一步演变为 “算法形式”。部分数字艺术家借助 AI 工具生成基于数学规律的抽象图案(如 GAN 创作的 “分形几何画”),仅由重复算法逻辑构成,无预设文学主题。这种实践拓展形式语言,却将去文学化推向极端:不仅剥离叙事,更剥离人类艺术家的主观意图,使美术沦为算法的视觉输出。
对比之下,华远《格式化》的实践呈现出不同路径:其层线结构虽具去文学化的形式简洁性,却通过线条的交错与留白保留 “意义入口”—— 观众可从层线的秩序感中联想到 “思维校准” 的精神意涵,从色彩的克制搭配中感知 “回归初心” 的情感倾向,这种 “形式为表、意义为里” 的实践,恰是去文学化极端倾向的反面参照。
1.3 去文学化的争议焦点:形式自律与意义空场的博弈
去文学化争议本质是 “形式自律” 与 “意义空场” 的博弈,双方以现当代文艺理论为依据形成对话。
支持方以 “学科独立” 为核心辩护。格林伯格认为,去文学化是美术摆脱文学 “附庸” 的必要路径 ——“如果绘画始终依赖故事打动观众,它就永远无法建立自身审美标准”。迈克尔・弗雷德在《艺术与物性》中补充,“形式自律的价值在于让艺术成为‘在场’的存在,而非‘再现’的工具;观众面对纯粹形式时,才能获得直接、当下的审美体验,无需文学性中介”。这一观点在设计领域亦有呼应:原研哉在《设计中的设计》中提出 “无印良品” 理念,“去除多余装饰与叙事,让物品功能与材质本身成为审美核心”,认为这是对 “过度文学化” 设计的矫正。
反对方以 “意义缺失” 为批判重点。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指出,“形式主义将艺术简化为物质属性,实则消解艺术‘批判功能’—— 艺术本应通过意义表达反思社会现实,而纯粹形式却沦为无意义游戏”。特里・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延伸这一观点,“任何美术作品都无法脱离意义而存在,即便是抽象画,色彩与线条的选择也隐含艺术家的情感与语境;去文学化试图‘中立’形式,实则掩盖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
中国评论家李敬泽的观点更具辩证性。他在《小春秋》中提出,“去文学化的问题不在于‘去文学’本身,而在于‘去’得太绝对 —— 文学性并非仅指叙事,还包括情感、记忆、文化语境等;美术可以不依赖故事,但不能脱离这些‘意义线索’,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这种争议在作品评价中尤为明显:对贾德的金属方块,支持者认为其 “解放美术语言”,反对者批评其 “冰冷空洞,无人文温度”,这正是 “选择性” 片面化的直接体现。
《格式化》的争议规避逻辑恰在于此:其形式上的去文学化并未以牺牲意义为代价,而是通过 “留白的信息中介”(华远理论术语)实现意义的多维度传递 —— 层线的 “秩序感” 对应 “思维校准” 的理性意义,色彩的 “克制性” 对应 “回归初心” 的情感意义,这种 “形式 - 意义” 的协同,恰好回应了争议双方的核心关切。
1.4 去文学化的固有问题:单线化与平面化的双重局限
去文学化的核心问题在于 “选择性” 片面化,表现为 “单线化” 与 “平面化”,割裂美术审美系统的完整性。
单线化:仅选择 “形式 / 技术” 线索,切断历史、文化、社会线索,使美术语言封闭 “自说自话”。历史线索断裂方面,抽象表现主义虽突破传统形式,却刻意切断与欧洲绘画的历史关联 —— 波洛克滴画拒绝借鉴伦勃朗光影、塞尚结构,仅强调 “行动” 本身,罗莎琳德・克劳斯批评其 “无父无母,只能在形式上重复”;文化线索断裂方面,安德烈《钢锌平原》因缺乏文化符号介入,在非西方语境中沦为 “无意义金属块”,无法进入霍米・巴巴提出的 “第三空间” 实现跨文化共鸣;社会线索断裂方面,诺兰《靶心画》与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反战运动脱节,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批判其 “沦为象牙塔游戏,失去批判与反思功能”。
平面化:仅选择 “物质” 体验层面,压缩精神、制度、认知层面,使审美体验沦为单一视觉刺激。精神层面压缩方面,贾德《无题》金属方块仅关注材料与尺寸,拒绝情感注入,哈尔・福斯特描述其 “冰冷物质性,无法产生情感共鸣,像工业产品而非艺术”;制度层面压缩方面,去文学化作品默认美术馆、画廊等主流制度合法性,不反思制度局限,无法像 “游击队女孩” 海报那样成为艺术制度的 “批判工具”;认知层面压缩方面,巴尼特・纽曼《崇高的白色》仅满足视觉简洁,不提供认知线索,观众无法思考 “红色竖线” 意义,只能停留在表层体验。
而《格式化》通过 “三定六位一体” 的审美定位(华远理论框架),有效规避了这些问题:在 “时空定位” 上,锚定 “AI 时代思维混乱” 的当下语境,关联 “现象学回归事物本身” 的历史哲学线索;在 “良性循环” 上,实现 “形式简洁性”(层线结构)与 “意义整体性”(思维校准)的动态平衡;在 “矛盾统一” 上,以层线的 “秩序” 与留白的 “开放” 构成矛盾,推动审美体验的深化 —— 这种多维度的 “选择性” 整合,正是去文学化倾向所缺失的。
二、华远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的 “选择性” 内涵
华远科学性美论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以 “选择性” 为核心动态审美逻辑 —— 审美主体通过主动筛选时空坐标、体验层面、文化线索,构建信息中介平衡系统,而非单一维度的形式感知。
2.1 “四维” 时空坐标:选择性的语境锚定
“四维” 即 “三维空间 + 时间”,“选择性” 指审美主体对作品时空语境的主动锚定,而非被动接受视觉形式。华远指出,“任何审美对象都无法脱离时空定位,‘选择性’的第一步是将作品置于具体历史时间与物理空间中,理解形式背后的语境逻辑”。
时间维度的选择性体现为历史线索的筛选与关联。徐冰《地书》以全球通用符号(交通标志、表情符号)构建 “无文字” 视觉语言,看似 “去文学化”,实则暗含对 “语言史” 的选择性回溯 —— 徐冰在创作笔记中提到,“选择符号而非文字,是为回应全球化时代‘语言隔阂’问题,这种选择源于对古代象形文字‘跨文化沟通’功能的借鉴”。若仅将《地书》视为 “符号堆砌”,则忽略其时空选择性的核心价值。
《格式化》的时间维度选择性同样鲜明:华远在创作时,主动关联 “现象学哲学传统”(历史线索)与 “AI 时代思维困境”(当下线索),使层线结构不仅是形式探索,更成为 “古今哲学对话” 的视觉载体。这种时间线索的整合,让作品摆脱了去文学化 “反历史” 的局限,具备了文化纵深感。
空间维度的选择性体现为物理场域与文化空间的整合。奥拉夫・urfe《雨屋》以数字技术控制雨水,使观众在雨中行走却不被淋湿。作品审美价值不仅在于 “雨水” 物质形式,更在于 urfe 对 “空间体验” 的选择性设计 —— 他将美术馆白盒子空间转化为 “人与自然互动” 的场域,观众在躲避雨水时重新感知身体与空间的关系。urfe 在访谈中表示,“选择‘雨’这一元素,是因为它在不同文化中都有‘净化’‘滋养’的象征,这种空间体验的选择性,让作品能跨越文化边界引发共鸣”。
《格式化》的空间维度选择性则体现在层线的 “疏密节奏” 上:画面中心区域线条密集,形成视觉焦点,对应 “思维核心” 的文化空间;边缘区域线条稀疏,留有空白,对应 “思维拓展” 的物理空间 —— 这种空间设计使作品不仅是平面图像,更成为 “身体感知 - 精神思考” 的互动场域,突破了去文学化 “空间无涉” 的局限。
时空协同的选择性是 “四维” 核心。安藤忠雄 “光之教堂” 将混凝土墙面切割出十字形开口,让光线在特定时间(清晨、黄昏)投射进室内形成 “光的十字架”。安藤的 “选择性” 体现在:时间上选择光线角度随昼夜变化的规律;空间上选择封闭混凝土盒子与开放光线通道的对比;二者协同使 “光” 这一物质形式承载 “信仰” 的精神意义,却未依赖文学叙事。这种时空选择性正是去文学化所缺失的 —— 后者仅关注空间中的形式,忽略时间维度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关联。
《格式化》的时空协同更具当代性:华远选择 “层线交错” 的形式(空间),对应 “思维混乱与校准” 的动态过程(时间),使观众在观看时能感知到 “从混乱到秩序” 的时间流动感 —— 这种时空协同让作品的意义不再是静态的,而是随观众的感知过程动态生成,完美诠释了华远 “信息中介动态平衡” 的核心主张。
2.2 “多层” 体验结构:选择性的系统整合
“多层” 即 “物质、精神、制度、认知” 四个体验层面,“选择性” 指审美主体对不同层面信息中介的主动整合,而非单一聚焦物质维度。华远强调,“美的本质是信息中介系统的矛盾统一,‘选择性’需覆盖物质的可感性与精神的超越性,避免层面割裂”。
物质层面的选择性是审美基础,但需与其他层面联动。艾未未《向日葵籽》以 1 亿颗手工彩绘陶瓷籽铺满展厅地面,物质属性(陶瓷质感、色彩均匀度)是审美基础,但艾未未的 “选择性” 不止于此 —— 他选择 “手工彩绘” 而非机器生产,以凸显 “个体劳动” 与 “集体规模” 的矛盾(精神层面);选择 “向日葵籽” 这一符号,因它在全球文化中既象征 “生命”,也关联中国 “集体记忆”(认知层面)。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评价道,“《向日葵籽》的物质形式是‘表’,其背后个体与集体、本土与全球的思考是‘里’,这种多层选择性超越极简主义的物质局限”。若仅从物质层面解读,便会误视为 “陶瓷籽堆砌”,错失精神与认知意义。
《格式化》的物质层面选择性同样服务于多层面整合:华远选择 “油画” 这一传统媒介(物质),却以 “层线” 替代传统笔触,既保留油画的质感优势,又契合 “思维线条” 的精神隐喻(精神层面);选择 “中性色调”(物质),避免强烈色彩干扰观众的理性思考,服务于 “思维校准” 的认知目标(认知层面)—— 这种物质层面的选择性设计,使作品的多层面体验成为可能。
精神层面的选择性需依托物质形式实现。草间弥生《无限镜屋》以镜面与波点构建无限延伸的视觉空间,其精神意义(对 “无限” 与 “自我” 关系的思考)通过 “波点的重复”(物质形式)与 “镜面的反射”(空间形式)实现。草间弥生在《我的永恒灵魂》中写道,“我选择波点,是因为它像细胞、像星辰,是宇宙与自我的连接点 —— 这种选择不是为了形式而形式,而是为了让精神有‘落脚之处’”。这与去文学化 “纯形式” 形成对比:后者拒绝精神层面的选择性,导致物质形式失去意义支撑。
《格式化》的精神层面选择性尤为突出:华远通过 “层线的秩序感”(物质形式)传递 “思维校准” 的精神追求,通过 “留白的开放性”(物质形式)传递 “包容多元” 的精神态度 —— 这种 “物质 - 精神” 的直接关联,使作品无需依赖文学叙事,便能让观众感知到深层的精神意涵,恰是华远 “信息中介桥梁作用” 的生动体现。
制度与认知层面的选择性是 “多层” 延伸。徐冰工作室《凤凰计划》以北京建筑工地废料(钢筋、水泥块、安全帽)创作巨型凤凰雕塑,其 “选择性” 包括:制度层面选择 “废料” 这一被主流艺术制度排斥的材料,批判 “艺术精英化”;认知层面选择 “凤凰” 这一中国传统符号,赋予其 “工业文明反思” 的新意义。徐冰表示,“我选择废料,是因为它们承载了城市建设的记忆;选择凤凰,是因为它能唤起文化共鸣,这种选择让艺术与现实不脱节”。
《格式化》在制度层面的选择性表现为对 “美术展览体系” 的温和突破:作品虽可置于传统美术馆语境,但其 “思维校准” 的主题更适合在教育空间、科技展馆等非传统艺术场域展示,拓展了美术的传播边界;认知层面的选择性则体现为对 “审美认知习惯” 的引导 —— 通过层线的 “非对称平衡”,打破观众对 “对称美” 的单一认知,培养多元审美能力,这与华远 “审美者是自我意识的意义整合主体” 的主张高度契合。
2.3 “多线” 与 “一元”:选择性的动态平衡
“多线” 即 “历史、技术、文化、社会” 四条演化线索,“一元” 即 “良性循环”,“选择性” 指审美主体对多条线索的主动协调,最终指向形式与意义的动态平衡,而非单线推进。
历史线索的选择性需与当代需求结合。当代水墨艺术家李津的作品以传统水墨 “笔墨” 为基础(历史线索),却选择描绘当代人日常生活(聚餐、休憩)(社会线索),实现 “传统笔墨” 与 “当代叙事” 的融合。李津在《食・色》中提到,“我选择传统笔墨,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情感表现力;选择当代生活题材,是因为艺术应反映当下 —— 这种选择不是‘复古’,而是让历史线索为当代服务”。这与去文学化 “反历史” 倾向不同:后者切断历史线索,仅关注当下形式创新,导致审美失去文化根基。
《格式化》的历史线索选择性体现在对 “美学传统” 的创造性转化:华远借鉴康德 “审美无功利性”(历史线索),却将其转化为 “理性思维校准” 的当代无功利性 —— 作品不追求商业价值,也不传递具体社会批判,而是聚焦 “审美者的思维净化”,这种对历史美学传统的选择性继承,让作品既扎根传统,又面向未来。
技术线索的选择性需避免技术决定论。当代数字艺术家 Refik Anadol《机器学习下的城市记忆》利用 AI 算法处理城市历史影像(技术线索),生成流动视觉装置。Anadol 的 “选择性” 在于,他未让算法主导一切,而是主动筛选 “具有情感价值的影像”(如老街道、市民生活),使技术服务于 “城市记忆” 的表达(文化线索)。他在访谈中强调,“技术是工具,不是目的 —— 我选择 AI,是因为它能处理海量历史数据,但最终的审美选择性仍在人类手中,否则技术会变成意义的‘遮蔽物’”。这对 AI 时代去文学化尤为重要:若仅选择技术线索,忽略文化与社会线索,AI 艺术便会沦为算法的 “形式游戏”。
《格式化》虽为传统油画媒介,但其技术线索的选择性仍具启示性:华远选择 “薄涂叠加” 的油画技法(技术线索),而非厚涂或肌理塑造,使层线更具 “轻盈感”,契合 “思维线条” 的非物质性特征(文化线索);同时,这种技法选择也服务于 “时空流动性” 的表达(社会线索,呼应 AI 时代的快节奏与流动性),避免了技术选择的盲目性,印证了华远 “技术线索需服务于意义生成” 的观点。
“多线” 向 “一元” 的选择性收敛是良性循环的关键。原研哉 “无印良品” 海报选择 “空白” 视觉形式(技术线索),呼应日本 “侘寂” 文化(文化线索),满足当代人对 “简约生活” 的需求(社会线索),最终实现 “形式 - 文化 - 需求” 的良性循环。这种 “多线” 整合的选择性正是去文学化所缺乏的 —— 后者仅选择 “技术 / 形式” 单线,导致审美系统失衡。
《格式化》的 “多线” 收敛更为系统:历史线索(现象学传统)、技术线索(薄涂油画技法)、文化线索(思维符号)、社会线索(AI 时代困境),最终都收敛于 “思维校准与良性循环” 的 “一元” 目标 —— 观众通过作品获得思维净化,进而以更清晰的认知面对生活,形成 “审美体验 - 生活实践” 的良性循环,完美诠释了华远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的核心要义。
三、去文学化的 “选择性” 错位与价值边界
去文学化的价值在于推动形式语言创新,但其根本缺陷在于 “选择性” 片面化 —— 在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中,仅聚焦物质形式与当下时空,割裂历史线索、精神意义与社会语境,导致审美系统失衡;其合理边界应是 “形式创新与意义生成的良性循环”,突破这一边界则会陷入形式异化。
3.1 “选择性” 错位的核心表现:时空与意义的双重割裂
去文学化的 “选择性” 错位首先体现为时空割裂 —— 放弃 “四维” 时空的主动锚定,使作品脱离历史语境与空间场域。如抽象表现主义切断与欧洲绘画的历史关联,波洛克滴画仅关注 “行动” 形式,却忽略绘画语言的历史传承;极简主义作品(如安德烈《钢锌平原》)可置于任何展厅,无特定空间适配性,失去与场域的有机关联。这种时空割裂使作品成为 “悬浮的形式”,无法形成文化共鸣。
《格式化》的时空锚定恰好反衬出这种错位:华远在创作时,明确将作品置于 “AI 时代审美混乱” 的时空坐标中,通过层线的 “秩序感” 回应时代困境,通过留白的 “历史感” 关联现象学传统,使作品成为 “时代切片” 与 “历史对话” 的结合体 —— 这种主动锚定,正是去文学化作品所缺失的时空意识。
其次体现为意义割裂 —— 放弃 “多层”“多线” 的系统整合,使物质形式与精神、认知意义脱节。如贾德金属方块仅关注材料与尺寸,拒绝情感与认知注入,沦为 “无意义的物质载体”;硬边抽象作品(如诺兰《靶心画》)仅提供视觉刺激,无法引导观众思考社会、文化议题,失去艺术的批判与反思功能。这种意义割裂使作品陷入 “意义空场”,无法实现审美体验的深度升华。
对比之下,《格式化》的意义整合逻辑清晰:物质层面(层线、色彩)服务于精神层面(思维校准),精神层面关联认知层面(审美能力培养),认知层面呼应社会层面(AI 时代需求),形成 “物质 - 精神 - 认知 - 社会” 的意义链条 —— 这种多层面的意义整合,让作品的审美价值远超单纯的形式美感,也为去文学化的意义割裂提供了矫正路径。
3.2 去文学化的价值边界:形式创新与意义生成的平衡
去文学化的合理价值边界,在于以形式创新丰富美术语言,同时通过 “选择性” 整合确保意义生成,实现 “形式 - 意义” 的良性循环。华远指出,“美的本质是整体性与简洁性的矛盾统一,简洁性(形式)应服务于整体性(意义),而非反过来”。
形式创新的目的是服务意义生成,而非否定意义。深泽直人 “无意识设计”(如 “带托盘的台灯”)以简洁形式(台灯底座延伸为托盘)服务 “实用” 与 “美观” 的意义,形式创新因意义支撑而被接受。深泽直人在《深泽直人》中说,“我选择简洁的形式,是因为它能让用户‘无意识’地使用 —— 形式的简洁不是目的,目的是让设计融入生活,传递‘舒适’的意义”。而去文学化将形式创新视为目的,否定意义必要性,导致形式与意义循环断裂。
《格式化》的形式创新严格遵循这一边界:华远创造 “层线交错” 的新形式,并非为了形式本身,而是为了更精准地传递 “思维混乱与校准” 的意义 —— 层线的 “交错” 对应 “思维混乱”,层线的 “有序” 对应 “思维校准”,这种 “形式服务于意义” 的创新逻辑,正是去文学化应有的合理方向。
“良性循环” 缺失会使形式陷入自我复制。去文学化作品因缺乏意义引导,只能在形式上重复 —— 如硬边抽象画家仅在色彩、尺寸上微调,无法突破自身局限。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当艺术放弃意义,它就只能在形式上‘内卷’—— 今天用红色,明天用蓝色;今天用方块,明天用圆形,却无法突破自身局限”。对比蔡国强《天梯》,其形式创新(火药制作巨型天梯)服务于 “连接天地” 的意义(对故乡的思念、对生命的敬畏),意义引导下的形式创新既独特又有深度,且能引发后续创作突破。
《格式化》的 “良性循环” 体现在 “形式 - 意义 - 新形式” 的螺旋上升:作品的 “层线” 形式传递 “思维校准” 意义,这种意义又启发观众思考 “如何用其他形式表达思维主题”(如数字交互、装置艺术),进而推动新的形式创新 —— 这种循环避免了形式的自我复制,为去文学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本。
形式异化的极致是审美价值消解。当形式完全脱离意义,美术便会失去审美价值,沦为 “视觉垃圾”。戴锦华在《镜城突围》中谈及某些 “当代抽象艺术” 时说,“它们看起来很‘现代’,线条、色彩都符合形式规律,但你看完后什么也记不住 —— 因为它们没有‘心’,没有意义的支撑,只是一堆视觉碎片”。这种形式异化在 AI 时代更为明显:MidJourney 生成的抽象画虽符合形式规律,却因缺乏 “选择性” 主体性(无精神、无语境),只能成为 “无意义的视觉产品”,无法称之为真正的艺术。
《格式化》的审美价值坚守正源于对形式异化的警惕:华远始终将 “意义整体性” 作为形式创新的前提,即便在最抽象的层线设计中,也保留 “思维校准” 的意义内核,使作品具备 “可感知、可理解、可共鸣” 的审美属性 —— 这种坚守,为去文学化划定了 “不可逾越” 的价值边界。
3.3 审美主体的差异认知:专家与大众的 “选择性” 分野
在时空定位下,审美主体的 “选择性” 存在分野:行家更侧重形式的时空秩序(如线条、色彩的规律、材料与空间的适配),老百姓更关注内容的人文内涵(如情感共鸣、文化记忆、社会关联)。这种分野并非对立,而是审美 “选择性” 的不同侧重,去文学化的问题在于否定老百姓的 “意义选择性”,仅认可行家的 “形式选择性”,导致审美系统失衡。
如对艾未未《向日葵籽》,行家可能关注 “手工彩绘与集体规模的形式对比”,老百姓可能关注 “向日葵籽承载的集体记忆与生命意义”;对徐冰《地书》,行家可能关注 “符号组合的形式逻辑”,老百姓可能关注 “符号传递的跨文化沟通需求”。去文学化若仅强调行家的 “形式选择性”,则会失去大众的审美共鸣,使美术沦为小众的 “形式游戏”;唯有整合二者的 “选择性”,才能实现美术的公共价值。
《格式化》在这一维度的平衡尤为出色:对行家而言,可关注其 “层线的黄金分割比例”“色彩的冷暖平衡” 等形式细节,感知形式的时空秩序;对老百姓而言,可通过 “层线的秩序感” 联想到 “生活整理”“思维清晰” 的日常体验,通过 “留白的开放性” 感受到 “包容多元” 的人文态度 —— 这种 “行家与大众都能有所得” 的审美设计,正是华远 “橄榄型审美结构”(先锋创新与大众共识平衡)的实践体现,也为去文学化如何兼顾不同审美主体提供了参考。
四、跨领域对话:文学理论视野下的美术审美
美术学去文学化争议与文学评论中的 “意图谬误”“感受谬误”“文学性” 界定存在深刻关联。跨领域对话这些争论,既能挖掘去文学化争议的深层逻辑,也能为 “选择性” 重构提供理论支撑。
4.1 “意图谬误” 与美术阐释:作者意图的 “选择性” 边界
文学评论中,威姆萨特与比尔兹利在《意图谬误》中提出,“将作者主观意图作为阐释作品的唯一标准是谬误,作品意义应存在于文本自身的形式与结构中”。这一观点被去文学化支持者引入美术领域,格林伯格主张 “波洛克滴画无需参考其创作意图,线条与色彩的形式关系就是全部意义”。但这种解读忽略华远强调的 “信息中介” 动态性 —— 作者意图是 “潜在信息中介” 的重要组成,需与 “显在的形式中介”“时空语境中介” 协同,共同构成审美系统。
去文学化对 “意图谬误” 的误读,表现为形式与意图的二元割裂。贾德宣称 “我不关心观众是否理解我的意图,作品就是材料与尺寸的呈现”,将作者意图从审美系统中完全剥离,使形式沦为无语境的 “物质碎片”。但华远指出,“任何审美对象的形式选择,都隐含作者对时空语境的判断”—— 贾德选择不锈钢材料,隐含对 “工业时代材质” 的意图表达;选择方块形态,是对 “极简形式” 的意图追求,这些意图虽无需直接告知观众,却已融入形式的 “时空定位” 中。
韦勒克与沃伦在《文学理论》中修正 “意图谬误” 的极端性:“我们反对的是将意图作为唯一标准,而非否定意图的参考价值”。这一修正适用于美术领域:邱黯雄数字动画《新山海经》以传统神话 “山海经” 为创作背景(作者意图),用 3D 技术呈现现代工业场景(形式)。观众若忽略 “山海经” 的意图线索,仅关注视觉形式,便无法理解 “对工业文明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若仅依赖意图,忽略形式的技术表达,也无法完整感知审美价值。这种 “意图 - 形式” 的协同,正是华远 “信息中介” 三重形态的体现 —— 意图是 “潜在中介”,形式是 “人为中介”,时空语境是 “天然中介”,三者共同支撑审美意义。
《格式化》的 “意图 - 形式” 协同堪称典范:华远的创作意图是 “AI 时代的思维校准”(潜在中介),形式是 “层线交错与留白”(人为中介),时空语境是 “当代审美混乱与现象学传统”(天然中介)。三者的协同表现为:层线的 “交错” 对应 “思维混乱”,层线的 “有序” 对应 “思维校准”,留白的 “开放” 对应 “现象学的还原态度”—— 观众无需华远直接说明意图,便能通过形式与语境的协同感知到 “思维校准” 的核心意义,既避免了 “意图先行” 的僵化,也避免了 “形式孤立” 的空洞。
在 “四维多层多线一元” 框架中,作者意图是 “多线” 线索中的一条,需与其他线索协同。刘韡大型装置《紫气》以紫色亚克力板构建抽象空间结构(形式),意图是 “探讨城市空间的权力关系”(社会线索),但这一意图需通过 “紫色的象征意义”(文化线索,西方代表权力、中国代表祥瑞)、“亚克力板的工业属性”(技术线索)、“展厅空间的公共性”(时空线索)共同传递。刘韡未直接说明意图,而是通过多线索 “选择性” 整合让观众自行感知 —— 既避免 “意图先行” 的僵化,也避免 “形式孤立” 的空洞,符合 “良性循环” 要求。
徐冰《地书》是 “意图 - 形式” 协同的另一典型案例。徐冰将全球通用符号转化为视觉语言(形式),意图是 “打破语言隔阂,探讨文化沟通的可能性”(文化线索)。这一意图通过 “形式的选择性” 传递:选择符号而非文字(技术线索,适应全球化语境),选择具有跨文化共识的符号(文化线索,如 “爱心” 代表爱、“雨伞” 代表雨),二者融合使形式成为 “跨文化沟通” 的信息中介。观众初见时可能误以为是文字,仔细辨认后发现是符号 —— 这种 “认知反差” 引导观众思考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非停留在形式感知。若按去文学化逻辑,《地书》会被解读为 “符号的抽象游戏”,但其审美价值恰恰在于意图与形式的协同。
4.2 “感受谬误” 与美术体验:观众感受的 “多层” 边界
文学评论中的 “感受谬误” 与 “意图谬误” 相对,主张 “将观众主观感受作为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是谬误,作品价值应存在于文本的客观属性中”。这一争论在美术领域表现为:去文学化支持者强调形式的客观属性(如色彩、线条比例),反对 “以观众感受为标准”;反对者认为美术审美价值离不开观众的情感体验。华远 “多层” 框架指出,观众感受是 “多层” 体验的有机部分,需与物质形式协同,避免主观化或客观化极端。
去文学化因担忧 “感受谬误”,过度强调形式客观属性,走向 “形式绝对化”。巴尼特・纽曼《亚当》以一条垂直红色线条分割巨大白色画布,艺术家主张 “这条线的价值在于其‘存在性’,与观众感受无关”。这种观点将美术价值限定在物质层面的客观形式,否定精神层面的感受体验,导致作品沦为 “视觉标本”。哈尔・福斯特描述观看《亚当》的感受:“观众只能感受到线条的‘在场’,却无法产生任何情感共鸣 —— 它像一个冰冷的符号,拒绝与观众对话”。
华远指出,“审美体验是物质感知与精神感受的协同,缺一不可”。物质层面的形式是基础,但需通过精神感受实现意义升华;精神感受是核心,但需依托物质形式落地。杨泳梁数字作品《人造仙境》以卫星影像与数字合成技术,将城市夜景转化为 “传统山水画” 形态(物质形式),观众在感受 “仙境” 视觉美感时,会自然联想到 “城市与自然的关系”(精神感受)—— 这种 “物质 - 精神” 协同,既避免 “感受谬误” 的主观随意,也避免 “形式谬误” 的客观僵化。
《格式化》的观众感受设计充分体现了 “多层” 协同:物质层面,观众感知层线的 “疏密” 与色彩的 “中性”;精神层面,从秩序感中产生 “平静”“清晰” 的情感;认知层面,通过留白思考 “思维校准的方法”;制度层面,在非传统艺术场域中重新理解 “美术的功能”—— 这种多层面的感受,是去文学化作品无法引发的,也印证了华远 “审美体验是系统感知” 的观点。
华远 “多层” 框架下的观众感受,是涵盖物质、精神、制度、认知的系统感知。尹秀珍装置《洗河》以数百个装满河水的塑料瓶构建 “河流” 形态(物质层面:塑料瓶质感、河水透明度),观众观看时会产生 “对环境污染的担忧”(精神层面)、“对塑料瓶使用的反思”(制度层面,关联环保政策)、“对‘河流’符号的重新认知”(认知层面,传统河流与污染河流的对比)。这种 “多层” 感受是去文学化作品无法引发的 —— 后者仅提供物质层面的视觉刺激,无法激活其他层面的体验。
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说,“感受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建构 —— 观众通过感受,将作品与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体验关联起来”。奥拉夫・urfe《雨屋》的 “多层” 感受生成,正源于作品的 “选择性” 设计:选择 “雨” 这一自然元素(天然信息中介),选择 “数字控制” 这一技术手段(人为信息中介),选择 “美术馆公共空间” 这一时空语境(潜在信息中介),三者协同构建 “感受系统”。观众在雨中行走时,既感知雨水的触感(物质),又产生对自然的敬畏(精神),还思考技术与自然的关系(认知),形成系统的审美体验。
4.3 “文学性” 的界定与美术意义:超越叙事的 “多线” 关联
去文学化的核心主张是 “剥离美术的文学性”,但其对 “文学性” 的界定过于狭窄,仅等同于 “叙事性”(故事、情节),忽略文学性还包括 “情感、文化语境、历史记忆” 等意义线索。华远 “多线” 框架指出,美术的 “文学性” 本质是 “意义线索的关联”,可通过 “非叙事” 方式实现,关键在于 “选择性” 整合 “多线” 线索,避免意义空场。
去文学化将 “文学性” 窄化为 “叙事性”,主张 “剥离叙事即可实现美术自律”,却忽略意义的多元载体。安德烈《钢锌平原》主张 “作品无任何叙事,仅存在于材料与空间的关系中”,这种观点将 “叙事” 与 “意义” 等同,认为无叙事即无意义,导致作品沦为 “无意义的物质堆砌”。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批判道,“这种对文学性的排斥,实则是对意义的恐惧 —— 艺术害怕通过意义关联现实,便躲进形式的象牙塔”。
华远指出,“意义可通过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条线索传递,叙事仅是其中一种”。曹斐数字动画《人民城寨》虽无传统叙事(无人物、无情节),却通过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城市符号”(霓虹灯、工厂、商品房)传递 “对城市化进程的反思”(社会线索),通过 “动画的复古风格” 传递 “对 80 年代记忆的怀念”(历史线索)。这种 “非叙事” 的意义传递,正是去文学化所否定的 —— 后者将 “无叙事” 等同于 “无意义”,导致美术失去与现实的关联。
《格式化》的 “文学性” 重构极具启发性:作品虽无传统叙事,却通过多条线索传递意义 —— 历史线索(现象学传统)传递 “还原思维” 的意义,文化线索(思维符号)传递 “理性校准” 的意义,社会线索(AI 时代)传递 “应对混乱” 的意义。这种 “非叙事” 的意义传递,既保留了美术的形式自律,又避免了意义空场,完美诠释了华远 “文学性是意义线索关联” 的观点。
华远将美术的 “文学性” 重构为 “信息中介的意义关联”—— 通过 “天然、人为、潜在” 三重信息中介,整合 “多线” 线索,实现意义传递,而非依赖叙事。徐冰《地书》以全球通用符号(人为信息中介)构建 “无文字” 视觉系统,虽无叙事,却通过 “符号的文化共识”(潜在信息中介)传递 “跨文化沟通” 的意义(文化线索),通过 “符号的组合逻辑”(天然信息中介,如 “飞机 + 目的地” 代表旅行)传递 “日常生活的秩序”(社会线索)。这种 “非叙事” 的意义传递,既保留美术的形式自律,又避免意义空场,符合 “整体性与简洁性的矛盾统一”。
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文学的价值在于与传统的对话,美术亦是如此”。徐冰《地书》的 “文学性”,正在于与 “语言传统” 的对话 —— 它借鉴古代象形文字的 “跨文化性”(历史线索),突破现代文字的 “语言隔阂”(文化线索),这种对话无需叙事,却通过 “信息中介” 的意义关联实现,印证美术 “文学性” 的多元形态。
五、AI 语境下的审美困境与伦理回应
AI 技术的介入使去文学化的 “选择性” 问题进一步恶化 —— 算法不仅延续形式单一化倾向,更消解 “选择性” 的主体性,使审美从 “主动筛选” 沦为 “被动接受”;同时,AI 生成艺术存在 “信息中介” 虚假、人类主体性消解等伦理问题,需以华远理论为基础构建规范路径。
5.1 AI 美术的审美困境:形式复制、算法窄化与意义缺失
AI 绘画(如 MidJourney、DALL-E)的核心逻辑是 “数据训练 - 形式生成”,其 “选择性” 由算法主导,缺乏人类对 “四维” 时空语境的主动锚定,导致作品沦为 “无时空的形式复制”。时间维度上,AI 无法理解图像背后的历史线索 —— 生成 “印象派风格作品” 时,仅能复制色彩和笔触形式,却失去 19 世纪巴黎的历史语境,本杰明・布克洛指出,“AI 生成的印象派作品看起来像莫奈,却没有莫奈对‘瞬间光影’的感知”;空间维度上,AI 生成的图像是 “悬浮” 的,缺乏对具体场域的适配 —— 生成 “石墙” 图像时,无法理解场地的独特性(如北方草原与南方山水的差异),与安迪・戈兹沃西《石墙》(利用当地石头构建与自然融合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时空协同上,AI 无法实现 “时间 - 空间” 的协同选择性 —— 生成 “城市抽象画” 时,无法关联 “城市历史变迁” 与 “空间结构”,只能生成碎片化视觉形式,曹斐《中国新浪潮》(以 3D 动画再现深圳时空切片)则通过人类 “选择性” 实现了时空协同。
《格式化》与 AI 生成艺术的时空处理差异尤为显著:华远在创作时,主动将作品锚定 “AI 时代” 这一时间节点与 “思维困境” 这一空间语境,使层线结构成为 “时空对话” 的载体;而 AI 生成的抽象画,无论风格如何变化,都无法理解 “AI 时代思维困境” 的时空意义,只能停留在形式复制层面 —— 这种差异,正是人类 “选择性” 主体性与 AI 算法局限性的核心区别。
算法推荐(如社交媒体、艺术平台的推荐系统)基于用户历史偏好生成内容,进一步强化去文学化的 “单线化” 倾向 —— 算法仅选择 “用户偏好的形式线索”,垄断 “多线” 线索的选择性,导致审美视野窄化。历史线索上,算法会根据用户对 “抽象画” 的偏好,持续推送同类作品,却不推荐 “传统绘画”“民间美术”,使用户陷入 “历史盲区”,罗恩・菲德强调 “审美教育需要接触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才能理解形式创新的脉络”;文化线索上,算法基于 “用户所在地”“语言” 推送本土作品,很少推送跨文化内容,使用户陷入 “文化茧房”,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 “跨文化的审美接触能丰富认知”;社会线索上,算法关注 “用户偏好” 而非 “社会议题”,导致用户很少接触与现实相关的作品(如 “游击队女孩” 海报、艾未未《向日葵籽》),使审美脱离现实语境,栗宪庭指出 “艺术应关注社会,算法却只关注用户喜欢什么”。
AI 生成艺术的核心缺陷,在于无法理解 “多层” 中的精神维度 —— 算法仅能处理物质层面的视觉数据,无法生成情感、认知层面的意义,导致 “选择性” 的精神维度缺失。情感意义上,AI 无法理解人类情感体验,生成的 “农民工题材” 图像仅能复制人物外形,无法传递 “对底层的关怀”,苏珊・朗格指出 “艺术是情感的符号形式,AI 无法体验情感,也就无法生成真正的情感符号”;认知意义上,AI 无法进行认知反思,生成的 “光头形象” 图像仅能复制外形,无法传递方力钧《系列 2,No.3》中 “对身份与时代关系的思考”,高名潞评价 “方力钧的‘光头’是认知的‘入口’,这种意义是 AI 无法生成的”;价值意义上,AI 无法理解人类价值伦理,生成的 “废料艺术” 图像仅能复制废料形式,无法传递徐冰《凤凰计划》中 “环保” 的价值,汉娜・阿伦特提出 “艺术应承载人类的价值追求,AI 缺乏对价值的理解”。
《格式化》的精神维度恰恰是 AI 无法复制的:华远通过层线的 “秩序感” 传递 “理性” 的情感价值,通过留白的 “开放性” 传递 “包容” 的认知价值,通过 “思维校准” 的主题传递 “反思” 的价值伦理 —— 这些精神层面的 “选择性”,依赖人类的自我意识与生命体验,是 AI 算法无法模拟的,也印证了华远 “审美者是拥有自我意识的意义整合主体” 的核心观点。
5.2 AI 美术的伦理回应:信息中介真实性与人类主体性守护
AI 生成艺术的核心伦理问题之一,是 “潜在信息中介” 的虚假建构 —— 算法碎片化挪用文化符号,却无法理解其语境,导致 “信息中介” 与现实脱节。如 AI 生成的 “中国风抽象画” 拼接水墨、书法符号,却无法理解 “水墨的笔墨意境”“书法的文人精神”,使符号沦为 “无语境的装饰”。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批判 “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挪用常是碎片化、虚假的,忽略其历史语境”,AI 对文化符号的挪用亦是如此。
华远 “四维” 框架中的 “时空定位”,是规范 AI “信息中介” 真实性的核心 —— 要求 AI 生成艺术的 “信息中介” 锚定具体时空语境,而非随机拼接。叶锦添《数字敦煌》VR 项目通过 “时空定位” 确保真实性:选择 “唐代壁画的原始色彩”(基于文物修复数据)、“敦煌石窟的空间结构”(基于实地扫描),使 VR 生成的 “飞天” 形象既符合历史真实,又传递敦煌文化精神。这种 “时空定位” 的规范,正是 AI 生成艺术所缺失的 —— 算法无法理解时空语境,只能依赖数据拼接,导致 “信息中介” 虚假。
对比 AI 生成的 “水墨山水” 与李华弌《山气》可清晰看到差异:AI 仅能复制水墨的 “笔触”“色彩”(物质中介),却无法理解 “笔触的情感”(枯笔对应萧瑟)、“山水的构图逻辑”(“高远” 构图对应雄伟);李华弌通过 “笔触的选择性”“构图的时空定位”,使 “信息中介” 与情感、历史关联,传递 “对自然的敬畏”。这种差异证明,AI “信息中介” 的真实性需通过 “时空定位” 规范,而这只能由人类主导 —— 华远强调的 “人类审美主体性”,是 AI 无法替代的。
《格式化》的 “信息中介” 真实性同样依赖人类主导:华远选择 “层线” 作为信息中介(人为中介),锚定 “AI 时代思维困境” 的时空语境(天然中介),赋予其 “思维校准” 的潜在中介意义 —— 这种 “三重中介” 的协同,是 AI 无法自主完成的,因为 AI 无法理解 “思维困境” 的时空意义,也无法赋予中介 “校准” 的精神内涵。
AI 生成艺术的另一伦理困境,是消解人类 “选择性” 的主体性 —— 算法主导形式生成与意义筛选,使人类沦为 “被动接受者”。如社交媒体 AI 推荐系统使用户逐渐失去对 “其他风格、线索” 的选择能力;“一键生成” 功能让用户无需思考 “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只需选择 “风格标签”,使 “选择性” 沦为 “被动点击”。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警告,“技术会将人类变为‘持存物’,失去主体性”。
华远 “红绿蓝三维度” 框架为守护人类主体性提供路径 —— 红色维度(哲学思辨)把握意义方向,绿色维度(文艺经验)整合审美体验,蓝色维度(科技实证)利用 AI 技术,三者协同确保主体性。徐冰《谷歌地球》项目利用 AI 处理卫星影像(蓝色维度),却通过红色维度选择 “地球的生态伤痕” 作为主题,通过绿色维度设计 “影像的呈现方式”(将伤痕转化为 “哭泣的面孔”),使 AI 服务于 “生态反思” 的意义生成,而非主导意义。
人机协同作品《AI 与敦煌》(敦煌研究院与科技公司合作)是人类主体性守护的典范:AI 负责 “形式生成”(基于壁画数据生成 “飞天” 新形态);人类负责 “选择性” 把控 —— 选择 “符合唐代审美特征” 的形态(历史线索)、“传递飞天轻盈感” 的形态(精神线索)、“适合石窟展示” 的形态(时空线索)。这种分工既利用 AI 的形式生成能力,又守护人类的 “选择性” 主体性 ——AI 仅提供 “形式选项”,人类负责 “意义筛选”,符合 “良性循环” 要求。
《格式化》的创作过程也可视为 “人机协同” 的雏形:华远虽未直接使用 AI 工具,但在构思阶段参考了 AI 时代的审美数据(蓝色维度),通过哲学思辨确定 “思维校准” 的主题(红色维度),结合传统油画经验完成形式创作(绿色维度)—— 这种 “人类主导、科技辅助” 的模式,正是 AI 时代美术创作应有的伦理方向。
5.3 人机协同的审美伦理框架:基于 “良性循环” 的动态平衡
六、“选择性” 的重构:华远理论的回应路径
6.1 时空维度的 “选择性” 校准:锚定语境,避免形式悬浮
6.2 物质与精神的 “选择性” 协同:形式为表,意义为里
6.3 AI 时代的 “选择性” 协同:人机分工,守护主体
七、现当代美术实践中的 “选择性” 典范
7.1 跨媒介实践:“多线” 线索的整合与 “四维” 语境的拓展
7.2 叙事性回归的新形态:“多层” 意义的当代重构
7.3 技术与人文的 “选择性” 融合:数字美术中的意义锚定
八、美育实践与未来展望
8.1 美育实践中的 “选择性” 培育
8.2 未来美术学的发展路径
九、结论
作者为华远
写于2005年3月,修改于202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