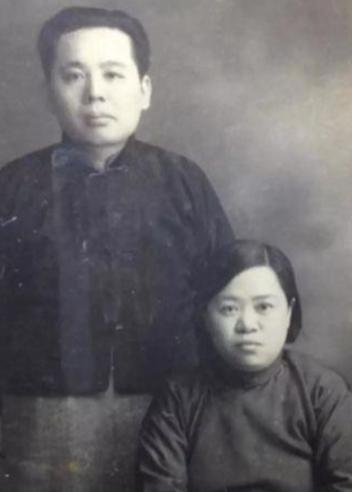1914年,作家张恨水被迫结婚,他嫌弃妻子貌丑,却经常和妻子同房,不久后,妻子怀孕生下一个女儿,他却怒骂:真是晦气!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14年冬天,安徽潜山的张家张灯结彩,堂前高挂红绸,锣鼓喧天,十八岁的张恨水站在堂屋中央,身穿长衫,神情拘谨,他是家中长子,自幼喜爱读书,曾梦想出国留洋,成为一名大作家,但父亲病逝后,他不得不放弃理想,挑起家庭重担,母亲为他安排了一桩婚事,新娘是邻村的徐文淑,一位出身清贫的乡间女子。 婚礼如期举行,新娘在喜轿中被迎入张家,那一夜,张恨水面对眼前这个矮胖、皮肤黝黑、五官不甚端正的新娘时,心中顿生失落,他从小深受新文化影响,对婚姻充满幻想,理想中的另一半是聪慧端庄、知书识礼的才女,但现实却是一个他从未接触、也未曾了解的陌生女子。 成婚后的生活冷淡疏离,徐文淑每日早起挑水做饭,照顾婆婆和家中弟妹,尽力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她不识字,不懂丈夫心中的文墨世界,却尽己所能地维护这个家,张恨水则将自己关在书房,埋头写作,不愿与妻子多有交流,他寄情于笔墨,认为婚姻只是孝道的延续,而非情感的归宿。 一年后,徐文淑怀孕,婆婆满心欢喜,四处采购婴儿用品,希望这孩子能为这个沉闷的家带来些许生气,可孩子出生那天,天空阴沉,寒风刺骨,接生婆抱出一个女婴时,张家上下的喜悦顿时冷却,张恨水听闻是女儿,神情漠然,转身而去,那孩子不到百日便夭折,张家挂起白灯笼三日,院子里阴霾久久不散。 不久之后,徐文淑再度怀孕,她依旧安静操持家务,从不抱怨,也不多言,她心中期待着再一次的希望,但命运再次捉弄她,那个早产的男婴出生后没多久便咽了气,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啼哭,张恨水此后彻底搬出卧房,独自一人住进书房,白天在外谋生,晚上伏案写稿,彻底将婚姻视若无物。 张恨水外出办报期间,生活逐渐稳定,作品开始在北方小有名气,他寄钱回家赡养母亲和家人,却极少回信问候妻子,母亲见儿媳独守空房多年,心中不忍,多次写信劝张恨水回乡探望,他终究还是回来了一次,带回北方的一位女子——胡秋霞。 胡秋霞原是北平习艺所的女工,年纪轻,性格开朗,与张恨水相识后,两人迅速亲近,他带她回老家,纳入家中,胡秋霞进门后改名,开始学习识字写字,短短几个月,她便与张家格格不入,她不爱持家,喜好跳舞饮酒,夜不归宿,常与张恨水争执,日子没过多久,她便自行离开,留下一地纷扰。 徐文淑从未说过一句怨言,她继续在家照顾婆婆,打理家务,甚至将胡秋霞留下的女儿视若己出,她心中那份母性从未熄灭,只是转移到了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她不曾指责,更未争宠,始终默默守着那个早已冷却的家。 几年后,张恨水在一次慈善晚会上认识了一位弹钢琴的女孩,她年仅十六岁,出身江南,名叫周南,她衣着得体,气质温婉,与张恨水笔下的才女如出一辙,两人相识甚欢,情感迅速升温,不顾女方家人的强烈反对,张恨水执意将她迎入家中,周南进门后,态度得体,行事有度,不但懂得照顾丈夫,还与徐文淑保持应有的礼节,称呼她为“姐姐”。 徐文淑并未表现出排斥,依旧如常料理家中事务,她看着这个年轻女子渐渐成为家中的主心骨,心中难免有些感慨,却从不流露,周南聪明伶俐,懂得照顾张恨水的情绪,他写稿疲倦时,她端上莲子羹;夜深时,她为他整理书稿,张家在那个时期迎来了短暂的安定与温情。 可好景不长,周南年纪轻轻便染上痨病,她病中依旧坚持帮张恨水修改文稿,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的离世给张恨水带来沉重打击,葬礼那日,徐文淑亲自为她烧纸,脸被烟熏得通红,仍不忘添上一把纸钱,一个从未得到丈夫真心的女人,却为另一个女子送上最温柔的告别。 晚年的张恨水身体虚弱,常年头痛,卧病在床,他的第二任妻子已离去,第三任妻子已故,其余的感情也都如风烟散尽,家中子女渐长,却无人愿意照料他,此时的徐文淑,仍旧每日早起,煎药送饭,操持家务,她不曾因被冷落而怨恨,也不因丈夫年迈而懈怠。 张恨水临终那段日子,常独坐书房,桌上摆着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他眼神黯淡,沉默寡言,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笔下那些曲折的爱情,终究敌不过现实中的平淡冷暖,临终前,他将一张存折交到徐文淑手中,口中无言,神情复杂,她接过那张纸,眼中泛起泪光。 多年后,张家的孙辈已成家立业,徐文淑仍旧住在老宅,院子干净整洁,灶台上每日煮着鸡汤,她年岁已高,却不愿歇息,邻人劝她安心养老,她总是摇头,说自己命里注定是干活的人。 信息来源:那些张恨水曾“缄口不谈”的情事(图)凤凰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