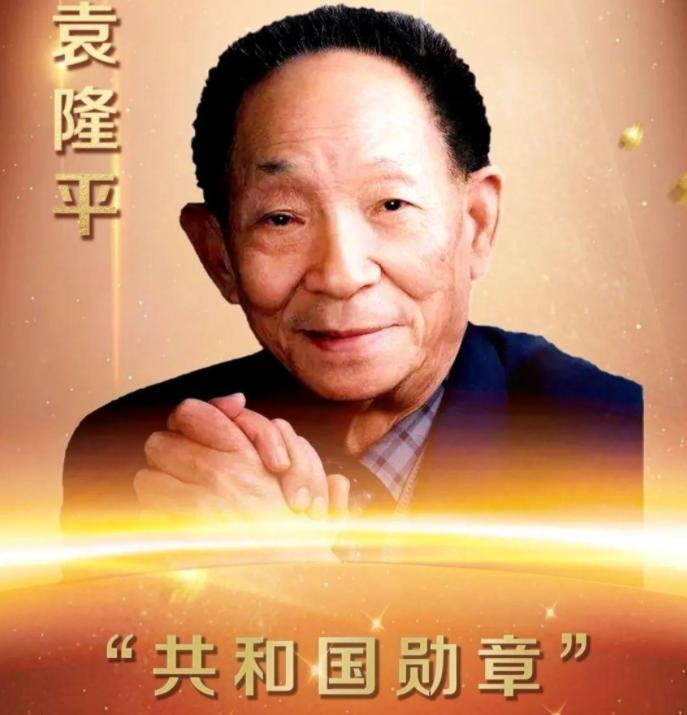袁隆平研究杂交稻,离不开毛主席与华国锋,华国锋:中央拨150万 “1970年3月15日,长沙,省政府小会议室——’老袁,你真能让稻子亩产千斤?’华国锋压低声音问。”袁隆平闻言,抬头一笑:“只要能撑到明年试种,我们就能让结果开口说话。” 那天的对话很短,却像一粒火种,迅速点燃了接下来十几年中国水稻科研的熊熊烈焰。袁隆平后来回忆:“领导不是在考我,而是在给实验撑腰。”事实也确是如此,此后150万元专项款迅速拨到安江农校,成为杂交稻爬坡过坎的第一桶真金白银。 把时间往前拨十五年,新中国百废待兴,大争论也此起彼伏。1956年,中科院和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摩尔根学派与李森科学派吵得面红耳赤。多数人担心挨批,噤若寒蝉。毛主席一句“让他们都说”打消顾虑,摩尔根学派得到喘息空间,孟德尔遗传规律得以保住讲台。不得不说,没有这层思想土壤,后来任何“水稻杂交优势”的设想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再看袁隆平自身的轨迹。1961年湖南大旱,他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捡到那株“鹤立鸡群”的稻株,一株230粒饱满籽粒,像明灯一样扎在他脑海中。连续两年复种,杂样不断,他却从反复失败里嗅到“杂交”二字的机会。在毛主席《实践论》的思路指引下,他认定答案不在课本,而在田埂与稻穗之间的矛盾运动。于是,1964年,他正式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方案;1966年2月,《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见刊——标志性一步走出去了。 纸上谈兵易,找到雄性不育系才是真功夫。1965年冬,他带三名助手跑到海南昌江,白天插秧,夜里点灯剖花,累计观察六万余株野生稻。1966年春节前夕,他们终于在一片湿地里发现“野败”。那天夜里,袁隆平激动得合不上眼,不停琢磨“若真配成三系,中国人就不用把饭碗端在别人手里”。 进入70年代,国家层面显然也意识到粮食与工业同等重要。华国锋主政湖南后,多次听取杂交稻汇报。1970年初那场长沙座谈会,他当场拍板:“中央支持150万,专款专用,只要实验合理,钱还会追加。”要知道,当时湖南全省财政才刚过十亿,这笔科研经费可不算小数目。陈洪新后来笑言,那感觉像是“苦练多年终于有人给换了好枪”。 有了资金,袁隆平的节奏明显加快。安江、南岳、三亚三地同时建立育种基地,三系配套试验同步推进。1973年10月,“野败”ד培矮64S”组合彻底攻克难关,新中国第一代籼型杂交稻正式定型。湖南常德试验田亩产超过650公斤,华国锋远程听取数据时连说三声“好”。 三系成功后,袁隆平并不满足,他琢磨能不能再减一道工序,于是两系法被提上日程。两系法不育系受光温影响大,一旦温度低就翻车。为此,他把实验田一路南移到三亚崖州湾,用更稳定的高温光照保底。1995年两系法问世,亩产再度抬头,达700公斤级别。有人打趣:“老袁像是给稻谷装了涡轮。” 资金、政策之外,更大的空间在国际舞台。198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邀请,袁隆平领衔的第一期杂交稻技术培训班在长沙开张,来自菲律宾、尼日利亚等国的学员挤满教室。袁隆平常把一句话挂嘴边:“咱中国人吃饱了,也得让世界其他地方搭把手。”截至2019年,累计有八十多个国家一万四千多名学员在中国学会了杂交稻技术,尼日利亚科贝项目甚至让当地农民第一次出现稻米卖不完的情况。 科技是冷冰冰的数据,背后却也是热腾腾的情怀。若没有毛主席在学术道路上的“开闸放水”,遗传学家不敢提“基因”“杂种优势”;若没有华国锋坐镇拍板,杂交稻团队可能还在为一把电动扬谷机四处借款。国家意志与科学理想在那一刻握手,才成就如今中国人碗里坚挺的白米。 有人问:袁隆平最该被历史记住的是什么?我个人的答案是两个字——敢闯。他敢在饥荒年代说“亩产千斤”,敢在争论最激烈时说“杂交有利”,同样敢把技术送到非洲的红土地上。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这句口头禅贯穿他的全部科研岁月。 如今,稻穗依旧年年低头,田埂上的故事却越说越久远。那段群策群力、举国为粮的年代已然过去,但“民以食为天”没有一刻过时。下一代的科研人若能记住毛主席“百家争鸣”的胸襟、华国锋果断拍板的担当,再加上一点袁隆平式的倔劲,中国农业的精彩仍大有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