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5年,元军南下,潭州孤立。就在这场围困将近尾声的夜里,知府李芾悄悄吩咐家人全体灌醉。他一言未发,只望着心腹沈忠。等家人一个个昏睡,李芾才低头落泪,轻声开口。那一刻,他已下定决心,绝不落入元军手中。等沈忠含泪跪下、拼命摇头,李芾斩钉截铁,只吐出三个字:军中令。 潭州之战,从来不是一场注定取胜的抵抗。从李芾受命那刻起,他就明白,这座城可能守不住,但一定得有人,给它留下点骨气。 李芾本不是草莽英雄,他是个文官。1275年夏天,他刚到潭州上任,就接到战报:元军南线攻势凶猛,主力阿里海牙正从江西杀向湖南。城中兵力不足三千,临时拼凑的守军人心不稳,军械补给几乎为零。放弃也能理解,投降也不丢脸,可李芾偏偏认了死理:这座城得死撑,得硬扛。 他没有选择逃避,也没有上书推辞,而是马上召集府衙官员开会,下令加固城墙,搜集粮草、盐、油,储备一切能支撑围城的资源。他把自己关进书房整整三天,翻遍《武经》、《兵要》,每一页都画满圈点。他不是将军,却想当将军。守城不只是军事,更是心理战。百姓能否坚持,全靠他给不出希望时,自己站出来扛。 修墙、练兵、调度、征粮,一桩桩、一件件,李芾亲自监督。有官员劝他缓一缓,说这是死路,没用。他摆摆手,说只管干,干一天是一天。哪怕只撑一周,也是北上战局争取来的时间。 几周之后,元军兵临城下。整个潭州陷入死寂,连狗都不叫。阿里海牙带来的不是讨价还价的兵,是雷霆万钧的猛将。他想速战速决,不想在这片小城耽误太久。第一波攻城,元军试探性进攻,城头弓箭零落,投石机用的是老旧齿轮,击不动石弹。李芾站在城墙上,不说话,只抿着嘴看。他知道这个仗撑不久。 可他又不能退。只要潭州一天没破,宋廷就还有底气。 几次进攻后,元军换了战法,断水源,烧庄稼,挖地道。城里人吃盐变得奢侈,李芾下令拆椅子桌子煮水提盐,熬饭只剩一碗汤,战马饿得发抖,守军靠嚼干草硬顶。几位副将开始动摇,李芾让人把他们关进大牢,说“士可杀,不可降”。 到了年底,战线已被压到内城。元军包围圈层层叠叠,李芾开始做准备。不是准备投降,而是准备断后。他让人收集文书,整理历年政务档案,火堆架好,一点火就是一屋公文灰飞烟灭。他清理粮仓,把最后剩下的三口袋粮送进衙门兵站,把自己卧室的水缸腾出来装沙土。然后他找来了沈忠。 沈忠是他从年轻时就跟着的亲信,能打也能断事。他没有亲生儿子,只认沈忠这个干儿子。他没有说太多,只说了一句:“等元军进城,别让家人落人手里。”沈忠听懂了,连头都没抬,只说:“知道。” 这件事他准备得很早,家人都安排在熊湘阁,喝的是掺酒的汤。酒不浓,却够让一个妇人倒头酣睡。孩子先醉倒,大人后醉倒,一圈下来,屋内只剩沈忠手抖着刀,和李芾站在窗前抽风。 沈忠到底还是下不去手。他把刀放下,跪在地上直磕头。李芾没看他,只看着窗外一点火光,元军营火映得半城红。他轻声说:“不做俘虏,不让后人笑。” 沈忠咬着牙,举起刀。那夜潭州没有月亮,风很大,火光飘得很远。到了黎明,元军冲进衙门,只看到熊湘阁内横陈的尸体。李芾头戴乌纱,躺在文案前,身穿官服,一字未留,只在他胸口写了两个字:尽忠。 那天之后,潭州没再有抵抗,守军放下兵器,百姓开门投降。元军进入时没动屠刀,反而下令厚葬李芾一家。这不是恩赐,是敬重。他们看得出来,这个文官守了个将军的规矩。 几十年后,有人重写潭州史时,把那一夜称作“绝命酒席”。那一顿饭,成了南宋最后几位忠臣留下的背影。后人立祠纪念,说李芾不懂兵法,却守得比兵法还像样;沈忠是个下人,却替主子守住了节义。 这不是战争胜负的故事,而是一个文官决定一座城的意志,在风雨欲来的时刻,把命豁出去,把忠写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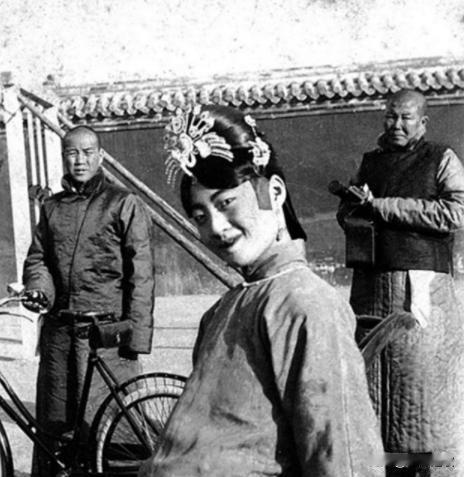





刘建波
是宋朝官员,不是清朝官员!
&山间
史盲,配图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