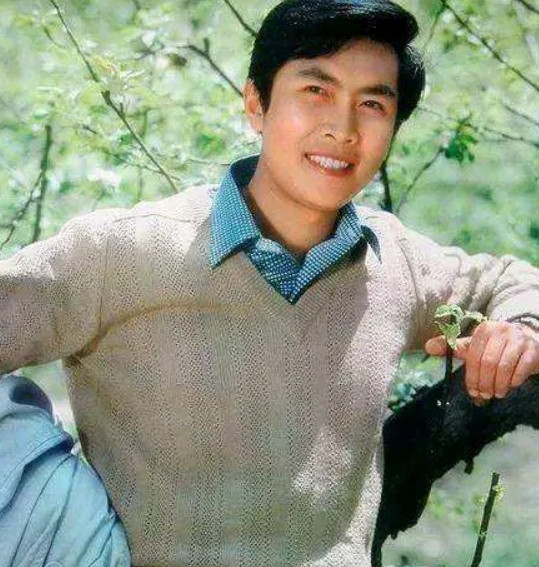1907年,林风眠母亲被族人抓去“沉塘”,年仅7岁的他抓起菜刀就冲向了人群,大声怒吼道:“放开我妈,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900年,广东梅州山村里一户石匠家添了个男娃,这孩子生下来瘦得跟小猫似的,家里人瞅着直摇头,那年头穷人家养不活病秧子,当爹的抄起襁褓就要往山沟里扔。 刚生完孩子的妇人硬撑着爬起来,光着脚追出三里地,硬是把孩子抢了回来。这个差点喂了野狼的娃娃,就是后来名震画坛的林风眠。 林家祖辈都是跟石头打交道的匠人,爷爷原本想把刻石碑的手艺传给儿子。可林风眠他爹是个怪人,放着祖传饭碗不端,偏要摆弄笔墨纸砚。 五岁那年,林风眠蹲在染坊门口看人家调颜料,五颜六色的布匹在水里翻滚,染缸里腾起的热气裹着染料味儿,把这个山里娃的眼睛都看直了。 打那天起,他成天缠着母亲往染坊跑,捡人家用剩的颜料渣在石板上涂涂抹抹。 要说林风眠的娘,那可是个苦命人,早年间被人从苗寨拐来,卖给林家当媳妇。丈夫比她大20岁不说,还是个瘸子,婆婆嫌她说话带苗音,村里人当她是异类。 唯独七岁的小风眠,最爱趴在娘膝头看她梳头,乌黑的长发像绸缎似的垂到腰际,沾着山泉水的木梳子一滑到底,这画面后来成了林风眠画里仕女的原型。 变故发生在1907年,村里新开的染坊老板是个读过书的斯文人,见林风眠娘俩常来,偶尔教孩子认几个字。 日子久了,风眠娘动了心思——她想跟着这个能写会算的老板逃出山沟。私奔的事还没出村就败露了,族老们敲着铜锣聚众,要把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绑去沉塘。 那天晌午,7岁的林风眠正在祠堂后墙掏鸟窝,忽然听见前院闹哄哄的。他扒着墙缝一瞅,浑身血都凉了——亲娘被麻绳捆成粽子,十几个汉子抬着往村口池塘走。 孩子顺手抄起墙角的砍柴刀,嗷一嗓子就冲进人堆,7岁的娃娃举着刀乱挥,还真唬得大人们后退两步。 亲爹上来要夺刀,被他一口咬住手腕子,最后还是爷爷拄着拐杖赶来,说沉塘晦气,改把妇人关进祠堂。 没曾想,转过年来,风眠娘竟突然不见了,有人说被卖到外乡,有人说送进了尼姑庵。小风眠攥着娘留下的木梳,在染坊门口蹲了三天三夜。 后来他画《宝莲灯》,画白娘子破塔,画里那些冲破牢笼的女子,眼角眉梢都带着他娘的影子。 15岁那年,林风眠揣着家里卖猪的钱去县城念书,在梅州中学,他遇见了贵人梁伯聪先生。这位前清秀才不教八股文,专教西洋画册里的透视光影。 有回梁先生看见他在作业本背面画的染坊,惊得眼镜都滑到鼻尖:“这小子将来要成大气候!” 1919年,林风眠揣着家里卖祖宅凑的200大洋,他和同乡林文铮挤上开往马赛的邮轮。在巴黎美术学院,这个山里娃头回见着真人裸体模特,羞得躲到画架后头。 教授扬西斯看他画的水墨荷花,激动得胡子直翘:“东方人的线条配上欧洲的色彩,妙啊!” 1926年,26岁的林风眠成了北平艺专最年轻的校长,他三顾茅庐请齐白石出山,把法国学来的色彩课搬进课堂。 然而,惜好景不长,军阀混战时学校停办,他转去杭州筹建国立艺术院。西湖边的小白楼里,他带着学生捣鼓“中西合璧”的新画法,后来成名的赵无极、李可染都是这时候打下的底子。 到了动荡时期,为了保命的林风眠把2000多幅画泡在浴缸里,拿手捣成纸浆。有人看见他蹲在抽水马桶前,一张张冲掉自己的心血。 80年代在香港重拾画笔,林风眠凭着记忆把毁掉的画又描出来,只是仕女的眼睛里多了层雾蒙蒙的哀伤。
1991年,92岁的林风眠躺在香港病床上,弥留之际反复念叨“想回家”。守床的徒弟问他回哪个家,是梅州老屋还是西湖画室? 老人没答话,手指在空气里画了道弧线,咽气时枕边摆着把断齿的木梳,乌木柄上还留着牙印——那是七岁那年护母时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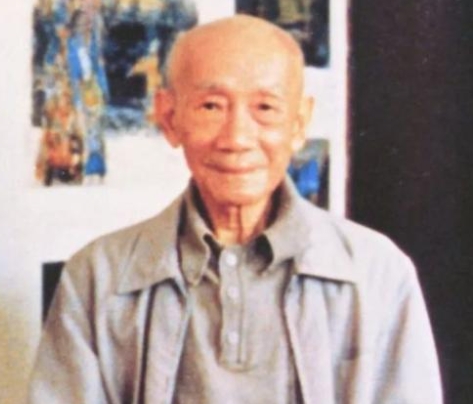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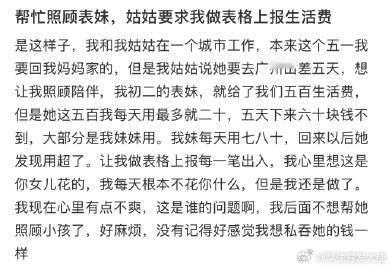


![美国🇺🇸:民主党再进一步就要拿起两把菜刀闹革命了![大笑][大笑][大笑]](http://image.uczzd.cn/10074786608684607427.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