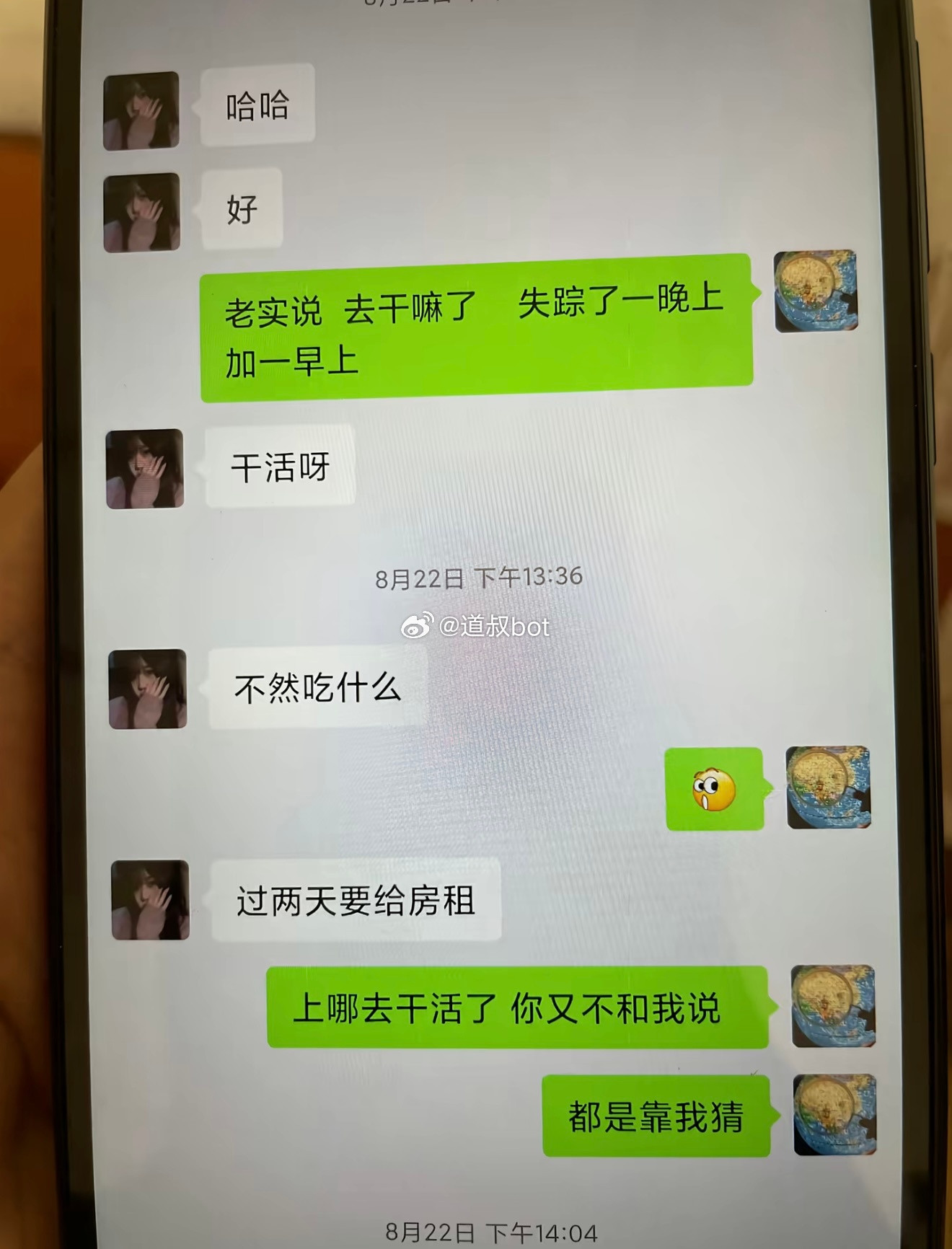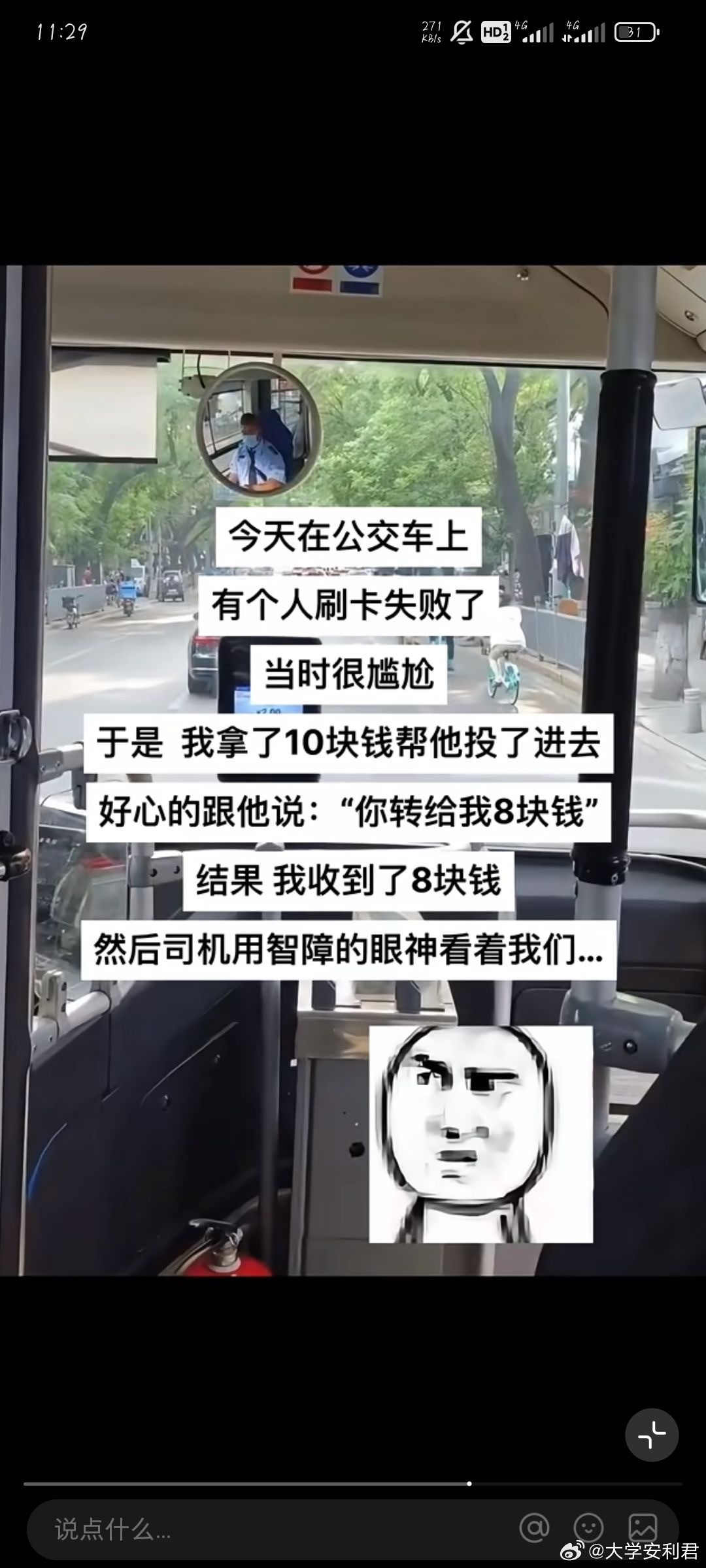元代大画家倪瓒因为洁癖,大半辈子不咋碰女人。有回心一横招当红歌姬赵买儿来陪宿。姑娘没进门先洗了回澡,刚在床榻躺平,倪瓒便从脖子到脚开始且扪且嗅,扪至阴,觉着不好闻,让她再去洗,来来回回一直搓澡到天亮,倪瓒啥也没干成,白白付了钱…… 1374年,一代画坛巨擘倪瓒在痢疾的折磨与尸身腐臭的里溘然长逝。 这极具反讽意味的结局,为他那以极端洁净著称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1301年,倪瓒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富庶的地主之家。 正是因为家境足够殷实,才让他可以有空闲时间去远离俗务、潜心艺文的资本。 然而,却也滋养了他异于常人的习性。 他的洁癖,并非寻常的讲究卫生,而是一种对“污秽”近乎偏执的恐惧与排斥。 这种特质,早在他青年时代便显露无遗。 家中仆役终日忙碌,不是简单的打扫卫生,而是为了满足主人那永无止境的洁净要求。 文房四宝须时刻纤尘不染,桌椅几案需反复擦拭。 他甚至强迫到自家庭院中的草木山石,命童子日日为梧桐树和湖石“沐浴”。 可怜那株梧桐,因过度频繁的擦洗下,最终叶落枝枯,竟被活活“洗”死了。 水至清则无鱼,倪瓒对洁净的苛求,已然超出了自然的限度。 这份洁癖,最直接地体现在他对人际交往的疏离上。 朋友来访本是乐事,于倪瓒却是莫大的精神负担。 曾有友人在家留宿,夜间一声咳嗽,便让倪瓒彻夜难眠,唯恐客人留下不洁之物。 第二天一大早,友人告辞,他立刻下令仆役搜寻那想象中的痰迹。 仆人遍寻不着,无奈之下以树叶沾唾沫搪塞,倪瓒见状,不仅严令将“秽物”丢弃远方,更迁怒于无辜的梧桐,再次进行大清洗,导致梧桐也死了。 最能体现倪瓒洁癖之荒诞与极致的,莫过于他与歌姬赵买儿的那段轶事。 这位以清高自许、大半生不近女色的画家,某日心血来潮,招来了金陵当红歌姬赵买儿侍寝。 赵买儿初入别院,倪瓒便命她先行沐浴。 待她洗干净,满怀期待地躺卧榻上,倪瓒却并未如寻常恩客般亲近,而是俯身下来,从她的脖颈开始,一寸寸地嗅闻、触摸。 当触及私密之处,他骤然蹙眉,断然认定有异味,不容分说地命令她再去清洗。 如此反复,赵买儿一次次踏入浴桶,肌肤被泡得发皱。 从晚上洗到大早上,倪瓒始终未能克服心理障碍。 最终,他只支付了酬金,而赵买儿则带着满腹委屈与不解离去。 这一夜徒劳无功的“共处”,成了倪瓒洁癖最生动的注脚。 而他如此荒诞的行为,早已印证他对“洁净”近乎神圣的苛求,已深入骨髓,甚至超越了最原始的本能。 倪瓒的洁癖并非仅作用于生活琐事,更深刻地渗透进他的精神世界与艺术创作。 他厌恶尘世的喧嚣与“俗气”,这种精神上的“洁癖”让他对权贵产生蔑视与不合作。 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仰慕他,携重金厚礼求画。 倪瓒非但不为所动,反而将作画的绢帛撕毁,将金银掷还,直言不屑为权贵走狗。 此举彻底激怒了张士信。 后来两人在太湖狭路相逢,张士信命人将倪瓒拖下船来,痛打一顿以泄愤。 倪瓒被打倒在地,却始终紧咬牙关,不发一言。 事后有人问及,他竟答曰:“一开口说话,就让人觉得满是低俗、没格调的东西。“ 他孤傲清高,宁折不弯的性子,由此可见一斑。 即使被关进牢狱,他的洁癖也未曾稍减。 元末乱世,他曾因得罪权贵而入狱。 狱卒送饭时,他要求对方必须将碗高举至眉际,以防唾沫溅入。 狱卒咒骂他挑剔,故意将他捆绑在厕所旁。 倪瓒身陷污秽之地,饱受煎熬,精神洁癖与现实污浊的冲突达到顶点,却依然未能磨灭他内心的坚持。 然而,正是这份常人难以理解的极端洁癖,在另一个维度上成就了倪瓒的艺术巅峰。 他笔下的一山一水,一树一石,无不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清冷与空寂。 画面中罕有人迹,远离尘嚣,营造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意境,如《六君子图》、《容膝斋图》等传世名作。 这种“疏体”山水,简淡高逸,正是他内心追求极致纯净与精神超脱的外化。 他的画风,深刻地影响了明清两代的文人画,被奉为逸品之宗。 晚年的倪瓒,散尽家财,漂泊于太湖一带,生活清苦,但洁癖依旧。 1374年,他在病痛的折磨中离世。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一生都在与“污秽”抗争的艺术家,最终却因疾病导致尸身腐臭,与他毕生追求的洁净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倪瓒的一生,是洁癖与艺术交织的一生。 他的洁癖,是枷锁,亦是阶梯,是病态,亦是风骨!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他的洁癖,无人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