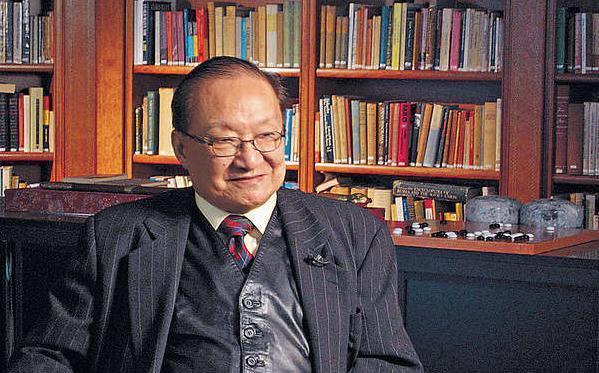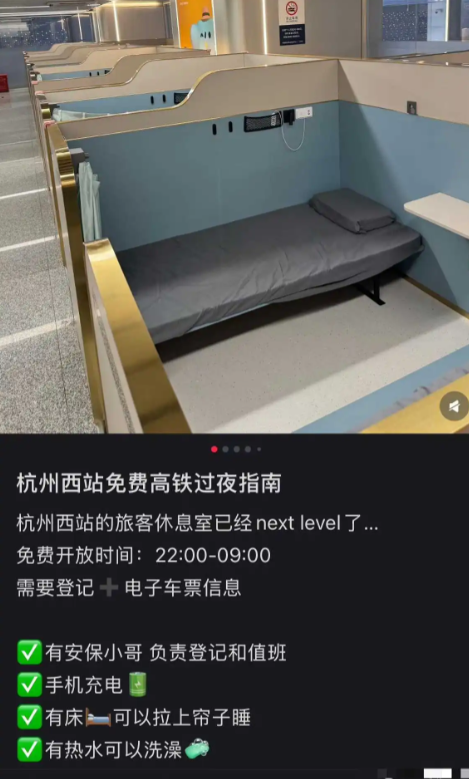杭州有苏、李两位书生,去京城参加秋试,在贡院左边租了房,考完等放榜时,盘缠快撑不住了,就商量换个便宜点的地方,有个同乡来的和尚介绍了一处东城外的房子,说是很清净。 两人揣着和尚给的地址,踩着露水就往东城外走。越往城外走,街面越窄,最后拐进一条青石板坑坑洼洼的巷子,尽头果然有个小门楼,门楣上刻着“静云巷”三个字,看着有些年头了。 开门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攥着串菩提子。“是慧能师父说的苏相公、李相公吧?”老婆婆眯着眼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进来看看,就这小院,你们不嫌弃就好。” 院里铺着碎砖,墙角堆着半垛柴火,正屋两间,里间摆着张旧木床,外间有张掉漆的书桌,窗台上还摆着盆叫不上名的草花,倒真像和尚说的——清净。李书生性子爽朗,一摸钱袋叹了口气:“婆婆,我们俩实在囊中羞涩,您看这租金……”老婆婆摆摆手:“不急,住下再说,能帮衬念书人,是积德的事。” 搬过来头几天,两人除了早晚在院里背背诗文,就缩在屋里算账。苏书生掏出钱袋倒出铜板,数了三遍:“省着点吃,顶多还能撑十天。”李书生挠挠头:“要不我去街口帮人写家书?听说一封能挣两个铜板。”苏书生点头:“我字比你工整,我去写,你帮隔壁王屠户劈柴,他昨天还念叨没人手。” 第二天起,苏书生就揣着笔墨在街口摆了个小摊,李书生扛着斧头去了屠户铺。深秋的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苏书生握笔的手冻得发红,写几笔就得往袖口里揣一揣;李书生劈柴劈得满头汗,脱了外衫露出里面打补丁的单衣,斧头起落间,木柴“咔嚓”作响,倒也痛快。 傍晚收摊回来,两人总能在门口看见一碗热粥,有时是小米的,有时掺了红薯,碗边还放着两瓣腌萝卜。“准是张婆婆送的。”苏书生端着粥,心里暖烘烘的,“明天我给她抄本《孝经》吧,她上次说想看。”李书生扒着粥点头:“我多劈点柴,给她堆得高高的,过冬烧着方便。” 就这么着,日子在笔墨香和柴火气里过着。苏书生的家书摊前渐渐有了回头客,有人夸他字好,给的铜板多些;李书生劈柴劈出了门道,王屠户常塞给他块碎肉,让他带回给“那个写字的兄弟”。张婆婆看在眼里,偶尔会拎着针线筐过来,帮他们缝补磨破的袖口,嘴里念叨:“念书人不易,可这苦日子,熬过去就甜了。” 放榜前三天,出了点岔子。李书生劈柴时没留神,斧头滑了,擦着膝盖划了道口子,血珠子直冒。苏书生赶紧扶他回来,正着急没铜钱请大夫,张婆婆颠颠跑进来,手里攥着个布包:“别慌,我这有膏药,是我当家的生前留下的,治外伤灵着呢。”她打开布包,里面是个油布裹着的小瓷瓶,倒出些黑乎乎的药膏,小心翼翼抹在李书生伤口上,“歇两天,别碰水。” 那天晚上,两人躺在被窝里,听着窗外的风声,李书生叹:“要是中不了,可对不住张婆婆的膏药。”苏书生拍他一下:“想啥呢?咱们写的文章,自己心里有数,就算不中,这趟京城也没白来——至少知道,好人还是多。” 放榜那天,天还没亮,两人就往贡院跑。挤在看榜的人堆里,苏书生眼尖,指着榜单中间:“快看!李兄,你的名字!”李书生揉了揉眼,果然看见“李修远”三个字,正想喊,又听苏书生叫:“还有我!苏明远!”两人愣了半晌,突然抱在一起,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回静云巷报喜时,张婆婆正在院里晒萝卜干,听了消息,手里的笸箩“哐当”掉在地上,抹着眼泪笑:“好,好,我就知道你们是有出息的!”苏书生这才注意到,婆婆屋里墙上挂着幅字,墨迹有些淡了,题着“寒窗十年”,落款是个陌生的名字。“这是我当家的写的,”张婆婆摸着字幅,“他当年也考了,没中,病着的时候总说,念书人只要心正,中不中都体面。” 后来苏、李二人都做了官,清正廉明,常寄银子回静云巷,可张婆婆总让来人捎信:“银子不用多,记得常回来看看那盆草花就行。”再后来,两人告老还乡,还特意绕道京城,静云巷的老门楼还在,院里的草花开得正好,只是张婆婆已经不在了,只留下那本苏书生抄的《孝经》,放在窗台上,被太阳晒得暖暖的。 故事改编自民间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