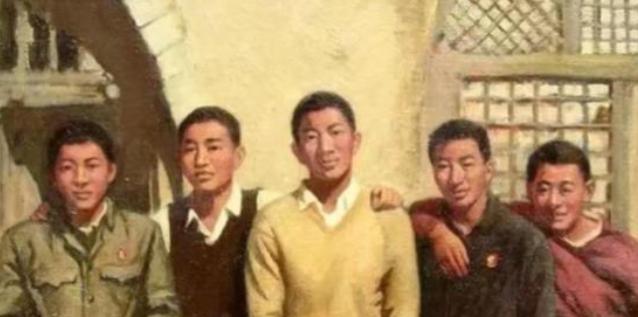1973年,知青王文清发烧39度,赤脚医生张秀巧给他打了一针,第二天,王文清说针打的地方还痛,张秀巧便脱下他的裤子检查,奇怪的是,那里既不红也不肿,怎么还会痛呢?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3年,赤脚医生张秀巧正朝着当地知青的宿舍赶,当时天上还下着雨,她身上裹着块塑料布,背后的药箱被雨水泡得发沉,裤脚上全是泥,谁知,这一趟出诊,竟成了她后半辈子故事的开头。 她要看的病人是北京来的知青王文清,当时的他正发着高烧,在土炕上缩成一团。 而张秀巧一看他烧得通红的脸,心里就有了数,是疟疾,所以她熟练地准备好一支珍贵的柴胡注射液,可就在消毒棉擦过皮肤时,王文清的耳朵尖一下就红了,支吾着想自己来。 张秀巧憋着笑,轻轻按住他的手腕,语气平静却不容商量:“别闹,针要打在屁股上。”一句话,让炕上的年轻人僵得像块木头。 而张秀巧当时并不知道,这短暂的尴尬,竟是两人缘分的开端。 第二天一早,王文清就找上了门,一脸痛苦地说:“秀巧,昨天打针的地方还疼得厉害。”张秀巧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让他脱下裤子检查。 可奇怪的是,针眼处既不红也不肿,所以她很是纳闷,但王文清却一口咬定就是疼。 从此,他成了卫生室的常客,嘴里总念叨着那针打坏了,这让张秀巧又困惑又委屈,村里也开始有了风言风语,说她医术不行,她想不通,这王文清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其实,王文清哪里是真疼,这小伙子三天两头往卫生室跑,说是量血压,结果是帮她整理药柜;说是测体温,顺手又把她的旧血压计擦得锃亮。 其中最离谱的一次,他捂着脑袋说头晕,结果却蹲在灶前,给她煮了锅红糖姜茶,腾腾的热气熏得他自己直咳嗽。 张秀巧终于忍不住了,一天,她把王文清堵在门口,气恼地问:“王文清,你到底怎么回事?村里的闲话你听见没有?我行医这么久,从没出过这种事,你是不是故意捉弄我?” 见她真生了气,王文清涨红了脸,这才道出实情:“秀巧,我……我是喜欢你,不知道怎么接近,才想出这么个馊主意,那地方早就不疼了。” 原来,从第一眼见到这个善良干练的村医起,他就动了心,他知道知青和村里姑娘身份有别,只好用这个“笨办法”制造机会,每次看她为自己着急、认真检查的样子,他心里就又暖又愧。 张秀巧听完,又气又好笑,抬手在他胳膊上轻轻捶了一下:“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嘴上嗔怪着,心里却泛起了涟漪。 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就明朗了,王文清干完农活,总会来帮张秀巧打扫卫生室;而张秀巧也会在他干活受伤时,格外细心地为他包扎。 她开始留意到这个北京青年身上的闪光点:修水渠时,他扛的石头比壮劳力还多;队里分自留地,他主动把向阳的好地块让给五保户。 有一回,村里为谁家多生的小羊羔归属闹纠纷,几个年轻人眼看要动手,王文清却掏出本皱巴巴的《农业六十条》,一字一句地念:“集体财产归集体,私自哄抢要受罚。” 他声音不大,可那几个后生竟真把鞭子收了回去,张秀巧听着村里老太太们夸他“有文化,心眼儿正”,脸颊发烫,心里却比谁都认可。 她本以为自己会嫁个本分的庄稼汉,可王文清的出现,让她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一直到1975年秋天,两人在老槐树下结了婚,没有鞭炮,只有村支书用大喇叭念了段毛主席语录,张秀巧穿着红布衫,王文清套着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就这么定了终身。 日子一晃到了1978年,知青返城的浪潮席卷全国,王文清却舍不得走,他放不下张秀巧,也放不下这片土地。 正巧县邮电局招话务员,看中了他脑子活络,他便成了村里第一个“走读”干部,户口却坚持留在了村里。 张秀巧问其缘由,他挠挠头应道:“邮电所打算在各村设立代办点,我欲回来操办此事,如此一来,咱们村也能接通电话了。”” 于是,他白天骑车去县城上班,晚上回来继续帮妻子整理药柜;周末还背着相机给乡亲们拍全家福,要把“农村的新变化”寄给北京的家人看。 而张秀巧,则一直坚守在乡村医疗的一线,她的药箱变成了设施齐全的卫生室,还带出了两个徒弟,让张家坪村的医疗服务有了传承。 如今,村口的“知青故里”石碑旁,王文清和张秀巧院子里的月季年年盛开,七十多岁的张秀巧腰板依旧挺直,给孩子们打疫苗时手法还是那么稳。 老两口于葡萄架下剥玉米,王文清会冷不丁发问:“秀巧,可还记得1973年那针?””张秀巧总会笑着答:“怎么不记得?没那针,哪有你这个人。” 或许有时候,一个看似自私的念头,反而能催生出一辈子无私的坚守,毕竟,再宏大的时代叙事,也得从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小事开始说起...... 【信源】中华网文化——暮色青春——知青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