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侯宝林在看了杨振华与金炳昶的一段吉他相声之后对苏文茂说:“文茂,你觉得杨振华的吉他相声算得上是相声吗?” 当北方曲艺界的各路名家齐聚在天津的时候,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表演,其中杨振华和金炳昶的吉他相声,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观众的反响那是相当热烈,大伙儿都觉得新鲜、好玩儿。吉他这洋乐器一抱,叮叮咚咚地弹起来,再加上包袱,确实给现场添了不少彩头。侯先生那句话,问得可真够劲儿,“这还算相声吗?”像根刺儿一样扎在那儿。老爷子不是保守派,他那双眼睛毒着呢,一眼就看到了问题的关键。 说白了,艺术需要新玩意儿,没人反对。杨振华他们敢把吉他整进相声,这份创新胆量值得竖大拇指。观众乐呵了,场面炸了,演出效果杠杠的,证明这条路子有它的价值。相声不是供在庙里的祖宗牌位,它得活,得跟着时代往前蹭。但侯宝林先生的疑虑,点的是相声这门艺术的根儿。老祖宗传下来的“说学逗唱”,根基是语言,是嘴皮子上的功夫,是人跟人对话碰撞出来的火花。一把吉他弹起来,音符飘到天上去,它确实是表演的核心亮点,可也实实在在地把金炳昶这位捧哏的作用给压下去了。逗哏抱着吉他成了焦点,弹、唱、说都得一个人来,捧哏在旁边还能怎么递话儿、搭架子?传统的“一捧一逗”那种精妙的语言配合、节奏拿捏,被乐器声抢了风头。热闹是有了,可乐子似乎更多地是从弹唱里蹦出来的,不再是单纯靠俩人斗嘴皮子抖包袱带来的回味劲儿。 这事儿说到底,就是个“度”的把握。创新是好事,观众接受更是硬道理。但要是为了让场面热乎,把相声最核心的“语言艺术”给模糊了,让它往音乐表演、流行秀的方向跑偏,那侯先生这一问就问在了点上。吉他能不能用?能用。可用了之后,“相声”的灵魂还在不在?它是不是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表演?侯老问苏文茂那个问题,真不是否定效果,而是在问我们所有人:新玩意儿加进来,别图一时热闹,心里得拎得清,相声的“脉”是什么,得守住什么。观众的笑声很宝贵,但别让笑声淹没了相声之所以为相声的那个“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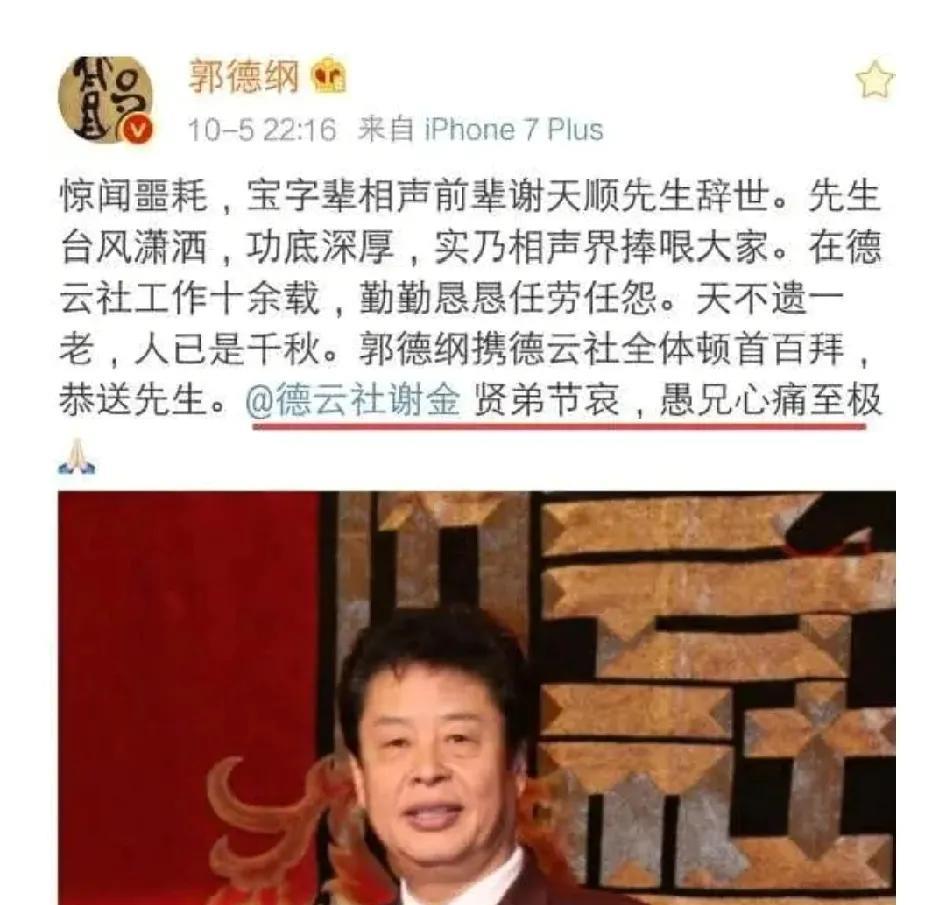






老张
杨振华真正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