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顺利爆炸,举国欢庆。而此时氢弹之父,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正和妻子儿女走在大街上。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咱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却愣了下,随即摆摆手:“哎呀!氢弹爆炸跟咱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 主要信源:(极目新闻——于敏,氢弹之父的姓名绝密28年;法治中原——「百年党史」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61年初春的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窗户蒙着厚厚的冰花。 34岁的于敏推开所长办公室的门,钱三强正盯着墙上的中国地图出神。 年轻的核物理学者刚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与杨立铭合著的《原子核理论讲义》刚被定为教材。 但当听到"氢弹理论预研"六个字时,于敏喉结滚动了一下:"我服从组织安排。" 回家路上,北平城的槐树刚冒新芽。 妻子孙玉芹正兴致勃勃展示新学的英文单词本,她为陪丈夫出国准备的厚厚笔记,在煤气灶跳跃的火光里化为灰烬。 于敏望着灶膛没说话。 从这天起他只能周末回家,从此世间少了个原子核理论专家,多了一位代号为"于敏"的绝密工作者。 1965年秋的上海华东计算所,计算机房的木地板被拖鞋磨得发亮。 于敏带着三十多人的团队进驻百日,办公桌下塞满行军床。 有天凌晨三时,他盯着数据图纸突然推倒水杯:"成了!" 助手们围拢过来,只见草稿纸上布满复杂的流线型构型,这是突破氢弹技术的关键物理方案。 此时距罗布泊的原子弹试验成功才过去十三个月。 戈壁滩的沙粒总往鞋里钻。 六次核试验场奔波中,于敏有三次险些丧命。 最大险情发生在零下二十度的试验场,他去查看装置时高原反应突发,鼻孔喷出的血染红羊皮袄,幸被警卫员背着跑回营区急救。 更凶险的是机密笔记本失窃事件,他在返京火车上发现文件不翼而飞,整车箱地毯式搜索三小时,最后在座椅夹缝里找回来时军装已被冷汗浸透。 北京某胡同小院里,孙玉芹正辅导儿子写作业,儿子指着报纸问"氢弹是啥",她只能摇头。 丈夫连续出差四个月,只有每月寄回的工资单证明人还活着。 当1967年6月17日氢弹在罗布泊腾起蘑菇云时,于敏回到家和妻子孩子一起出门逛街。 平常对吃什么没有要求的人,却在氢弹成功爆炸这天罕见的提出买只烤鸭庆祝庆祝。 尘封二十八年的名字1988年重见天日时,邻居张大妈挎着菜篮惊呼:"老于头!您不就是胡同口总帮修自行车的闷葫芦嘛!" 这年于敏家饭桌摆着罕见的三菜一汤,女儿终于能告诉同事"我爸造过氢弹",而孙玉芹数着丈夫带回来的"两弹一星"勋章,却先量了他的腰围:"瘦了三寸,得炖锅红烧肉。" 晚年在北大小区遛弯时,这位曾和邓稼先联手托起核盾牌的老人总戴顶旧鸭舌帽。 有次被物理系学生认出求教,他攥着树枝在沙地写公式,末了拍拍青年肩膀:"我吃亏在没留过洋,你们要出去多见识。" 2012年初春老伴猝逝,于敏把"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写在日记本首页,落款是"负心人"。 2019年寒风凛冽的冬日,九旬老人枕边还放着孙玉芹的绒线帽。 他留给世间的最后嘱托,是要求把骨灰撒在罗布泊试验场旧址:"让风沙掩了吧,功名都归国家。" 殡仪馆外,几辆军用吉普默默排成长队。 那是当年华东计算所的"百日战友"们,如今也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了。 对此您怎么看?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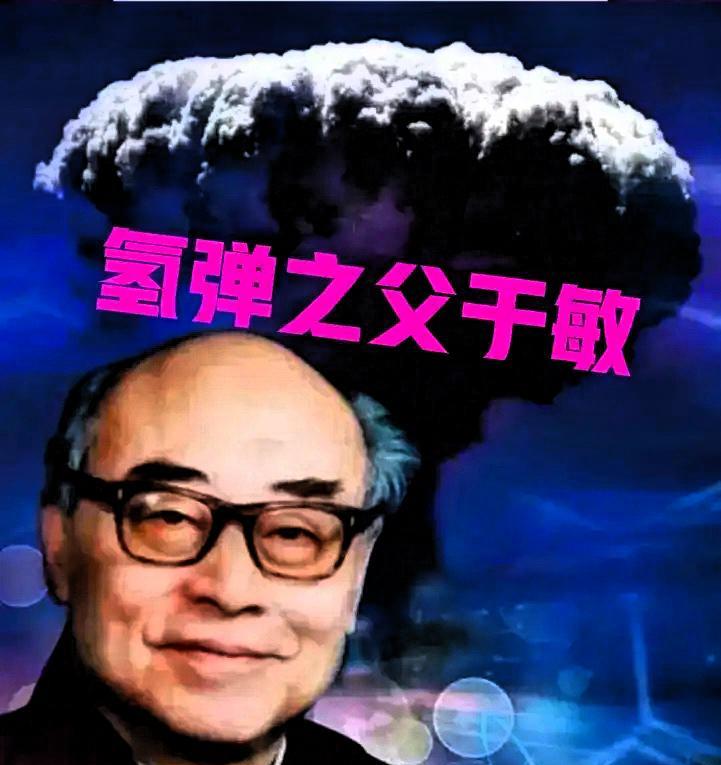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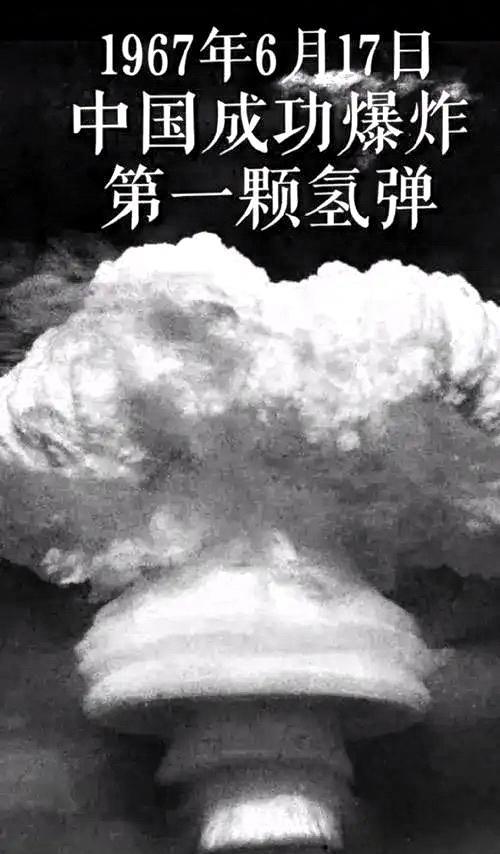

明月
这就是共和国的脊梁,“功”归于国家,“名”归于华夏,自己只是个“负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