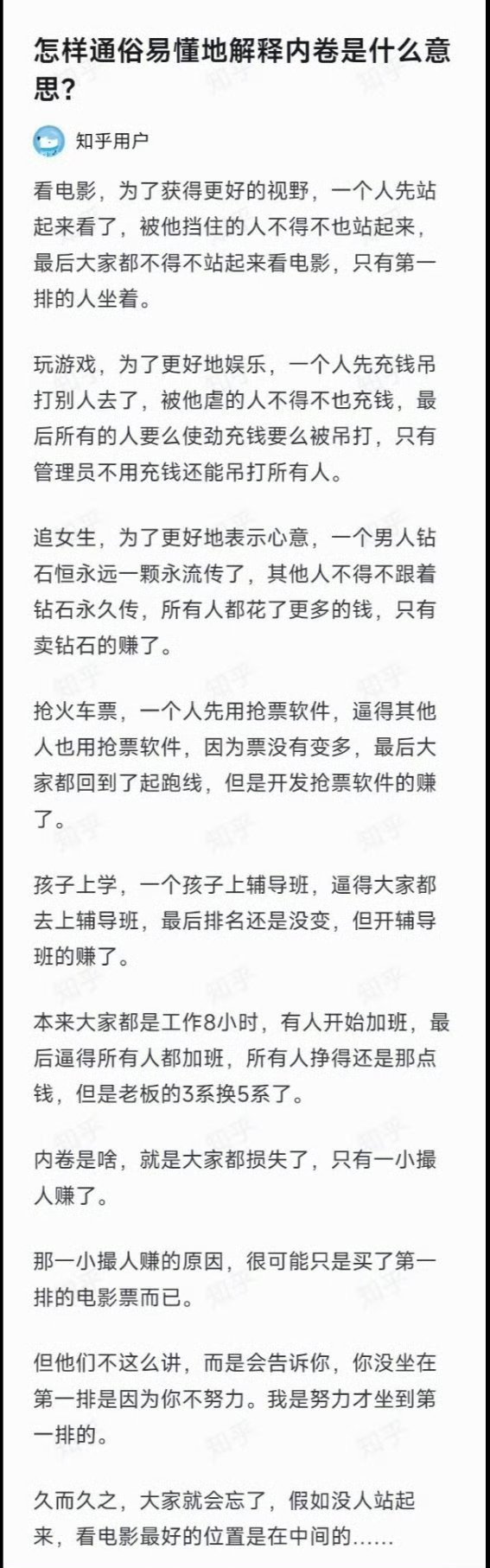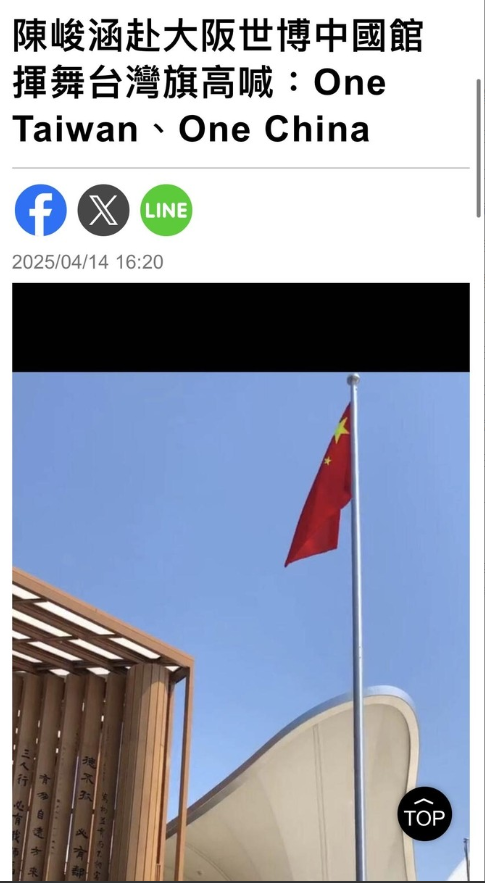【环保倒退?全球反环保浪潮背后的惊人矛盾】
反环保主义正在抬头。对净零目标的抨击,以及对环保措施和减排目标的敌意日益加剧。正如近期选举结果所揭示的,这些策略正逐步重塑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格局。
反环保主义不仅否定环保举措,也敌视环保主义者。尽管这一思潮骤然兴起且言辞激烈,其理论基础却相当薄弱。其传达的信息往往相互矛盾,且与人们的日常经验背道而驰。
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为例。他在任内撤销了大量环境保护政策,现又进一步废除剩余的环保措施——包括取消对涉及“气候”研究项目的资金支持。然而,他在2024年于威斯康星州的一次集会上却表示:“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希望拥有清洁的空气和清洁的水——真正清洁的水,真正清洁的空气。”
反环保主义的诸多矛盾,亦揭示其与传统保守主义理念的分歧。尽管被归类为“保守派”,美国共和党、英国改革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及法国国民联盟等民粹主义政党所推动的反环保政治,实质上对保守主义曾核心倡导的延续与保护理念构成了根本性挑战。
保守派环境网络(Conservative Environment Network)是一个自称“致力于支持净零排放、自然修复和资源安全”的英国及全球保守派独立论坛。该组织长期致力于提醒公众,从美国国家公园的设立到英国及其他地区在污染控制与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重要举措,许多关键性的环保政策正是由保守派所推动。
然而,右翼阵营对此似乎回应寥寥。一股民粹主义浪潮正在席卷这一保守传统,尽管事实上对环境保护的支持依然广泛存在。
民调显示,80%的英国人对气候变化表示担忧。美国环保署的工作也获得了压倒性的公众支持,其中甚至包括共和党选民。
这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环境破坏已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不可预测的气候、动物和昆虫种群的锐减,以及诸多其他挑战,不仅出现在媒体画面中,更在生活现实中一目了然。
在我为即将出版的关于全球环境怀旧现象的著作所做的研究中,我反复遇到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在西方国家,那些呼吁“夺回国家控制权”的右翼声音,却对旨在保护国家、确保其持续生存的环保政策表现出明显敌意。
这一错位现象的成因复杂多样,包括对要求改变生活方式与经济结构措施所引发的怨恨。然而,这种敌意与疏离感远非单纯的反自然情绪所能概括。
许多人——包括特朗普本人——声称自己是环保主义者,尽管现有证据明显与此相悖。环保的符号与象征已深植于商业与文化生活之中:若野生动物能够提起版权诉讼,恐怕早已有无数富有的熊出现在法庭之上。
我认为,环保主义可区分为“冷”与“热”两种形态。前者怀念并哀叹自然的流逝,但将自然视为供人欣赏的景观——一组赏心悦目的动植物图像;而后者则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联系,并因此产生焦虑与责任感。
前者使人能够自称热爱自然,却对拯救自然的具体措施漠不关心,甚至加以抵制。然而,“冷”与“热”、环保与反环保之间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也不具绝对性。
反环保主义的另一特征在于其信念的流动性,甚至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气候变化即为一例。
改革党领导人长期以来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2024年,前改革党领袖理查德·蒂斯曾表示:“气候变化已持续数百万年。认为人类可以对抗太阳或火山的力量是完全荒谬的。”尽管蒂斯未曾改变其立场,该党新任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却在同年晚些时候接受BBC采访时表示,他“不否认科学事实”。
与其他民粹主义政党类似,改革党在环境议题上的立场灵活多变:一方面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或否认其人为成因,另一方面又承认人为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却认为鉴于他国(特别是中国)“贡献不足”,相关环保目标既难以达成亦不公平。
研究人员方才开始对反环保主义进行系统性探讨。环境政治研究者约翰·赫尔特格伦在其著作《烟雾与战利品:美国反环保主义与阶级斗争》中,深入分析了共和党如何使工人阶级选民相信,“就业与环境保护、工人与环保主义者之间存在零和对立关系”。
这一对立逻辑亦出现在《反环境主义手册》的研究中。该书指出,西方多个国家已将环保主义刻板化为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的代言人。
然而,这些重要研究由于其地理聚焦,忽视了反环保主义的另一悖论:尽管其言说体系不断指责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无所作为”,但欧洲与美国之外的许多地区,在环保政策与公众态度方面已出现显著转变。
环保主义正逐步走向后西方化。这一趋势部分源于亚洲与非洲诸多地区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
极端高温和降水模式的不确定性,正在引发粮食安全问题与大规模人口迁徙。在非洲萨赫勒地区与南亚,环保主义或许更应被称为“生存主义”。
尽管中国仍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其以国家主导推动“生态文明”转型的愿景——即建设资源节约型和低碳发展社会——正使其逐步确立全球环保领导者的地位。
环保主义被视为西方国家主导理念的刻板印象正在瓦解。也正因此,再加之环保主义内部所面临的多重矛盾,反环保主义的兴起不仅复杂,更显得耐人寻味,难以持久。
热点观点海外新鲜事海外编译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