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于凤至身体发生溃烂,抛下丈夫张学良赴美治病。她憔悴走下飞机,正茫茫然。谁知,一个老外冲过来一把抱住她,还行了一个亲吻礼,说:“你终于到了!”
这年,一架从中国飞往美国的客机降落在旧金山机场。
四十三岁的于凤至裹着厚实披肩走下舷梯,左胸位置隐约可见药物渗透的痕迹。
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东北第一夫人,此刻面色青白双颊凹陷,连呼吸都带着隐忍的颤抖。
异国他乡的寒风卷着陌生语言扑面而来,她攥紧随身皮箱的把手,指甲几乎要掐进皮革里。
就在她茫然四顾时,人群中突然冲出个高鼻深目的洋人。
对方张开双臂将她搂进怀里,在她面颊重重亲了两下。
这个唐突的举动惊得于凤至踉跄后退,却见对方摘下礼帽露出满头银发,用生硬中文解释:"我是您的肿瘤医生威廉·瑞德,等您三个月了。"
这个拥抱成了于凤至在美国收到的第一份善意,她不知道,这个决定远渡重洋治病的夜晚,丈夫张学良正被秘密转移至贵州深山的囚室。
铁窗里摇曳的煤油灯下,少帅反复擦拭妻子留下的银质怀表,表壳内侧刻着"汉卿安好"四个小楷。
乳腺癌的阴影早在三年前就笼罩在于凤至身上,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她带着精神失常的长子张闾珣躲避战火,途经武汉时发现胸口肿块。
当时张学良已被幽禁在浙江奉化雪窦山,她既要照顾发病时用头撞墙的儿子,又要为丈夫送去御寒衣物,硬是把检查报告塞进箱底。
真正让病情恶化的,是接二连三的丧子之痛。
1938年春天,次子张闾玗在伦敦遭遇空袭,被炸断双腿后感染破伤风离世。
转年秋天,三子张闾琪因肺结核殒命上海广慈医院。
连续两个儿子棺木入土时,于凤至都强撑着操办后事,直到某天清晨咳出带血的丝帕。
张学良得知妻子病情已是1940年初,那天看守破例允许夫妻俩在贵州阳明洞相见,于凤至解开旗袍盘扣,露出溃烂流脓的部位。
少帅别过头去,听见铜盆里消毒棉球落水的声响,突然抓住妻子颤抖的手:"你走,带着闾瑛去美国。"
这个决定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轨迹,于凤至临行前托人给香港带口信,请赵四小姐北上照顾张学良。
她不会想到,这个看似周全的安排,竟让赵四在二十四年后取代她成为张夫人。
当飞越太平洋的客机冲破云层时,贵州山间的囚室里,赵四小姐正把新摘的野菊插进青花瓷瓶。
威廉医生的治疗方案堪称残酷,三个月内三次乳房切除手术,每次都要刮掉腐烂的胸骨。
最危险那次手术持续八小时,护士往于凤至嘴里塞纱布防止她咬断舌头。
术后感染导致高烧不退时,十八岁的女儿张闾瑛握着母亲的手,听见昏迷中的呓语全是"汉卿该添衣了"。
1945年日本投降消息传来时,于凤至正在华尔街证券交易所。
化疗后稀疏的头发藏在貂皮帽里,她握着变卖首饰换来的五千美元,全部买入即将崩盘的奇异电气股票。
交易所里此起彼伏的破产尖叫声中,这个中国女人凭着东北商贾世家的直觉,在股票暴涨400%时果断抛售。
炒股的意外之财开启了她的地产投资,从纽约长岛到洛杉矶比弗利山,于凤至专挑市郊荒地和法拍屋。
有次顶着暴风雪查看新购地块,六十岁的她摔进结冰的灌溉渠,爬起来时还攥着沾血的产权文件。
到1950年代,她名下的房产已遍布美国东西海岸,却在每份房契受益人栏都写着张学良的化名。
1964年台湾来的离婚协议书,是随着《纽约时报》塞进邮箱的。
于凤至盯着"张于凤至"四个字看了整夜,晨光爬上窗台时才用钢笔签下名字。
七十六岁的她不知道,这纸离婚是为让赵四小姐获得合法身份,更不知蒋介石在协议上加注"永不释放"的批文。
生命的最后十年,于凤至在洛杉矶城郊购置了两处相邻墓园。左边石碑刻着"张于凤至",右边空白碑面朝着太平洋方向。
1990年春天,九十三岁的她弥留之际,床头收音机里正播报张学良即将获释的消息。
女儿俯身听见母亲最后的呢喃,竟是在哼奉天城的民谣《月牙五更》。
当少帅真正踏上自由土地时,看到的只有好莱坞山上的汉白玉墓碑。
他摸着冰凉石面上"张学良"三个字,突然想起1934年那个雪夜,于凤至在东北大帅府为他缝制狐裘,暖黄灯光映着她低垂的睫毛。
赵四小姐在身后轻声提醒该去机场了,他掏出手帕擦了擦石碑,留下半块没化完的松子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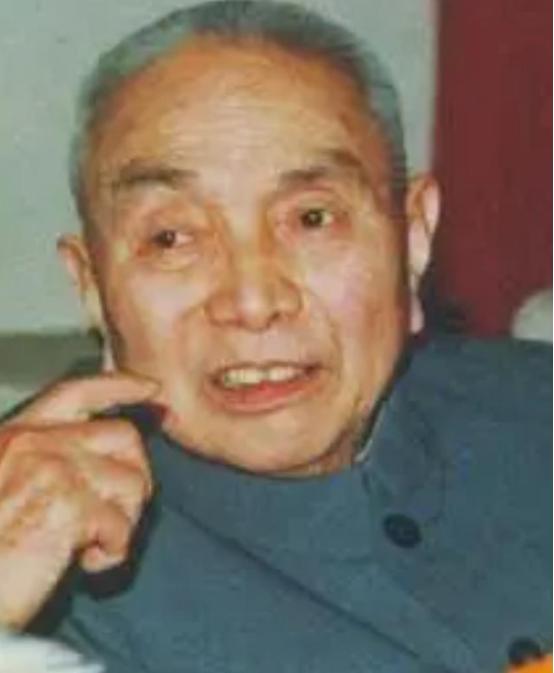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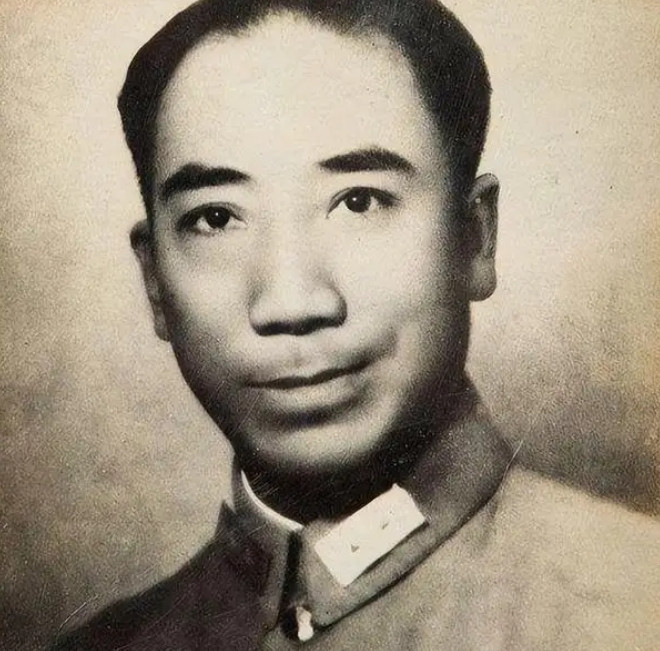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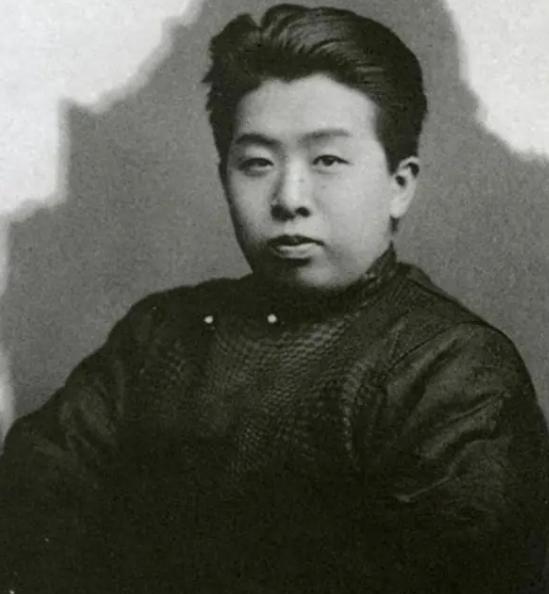



风雪夜归人
看来还是相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