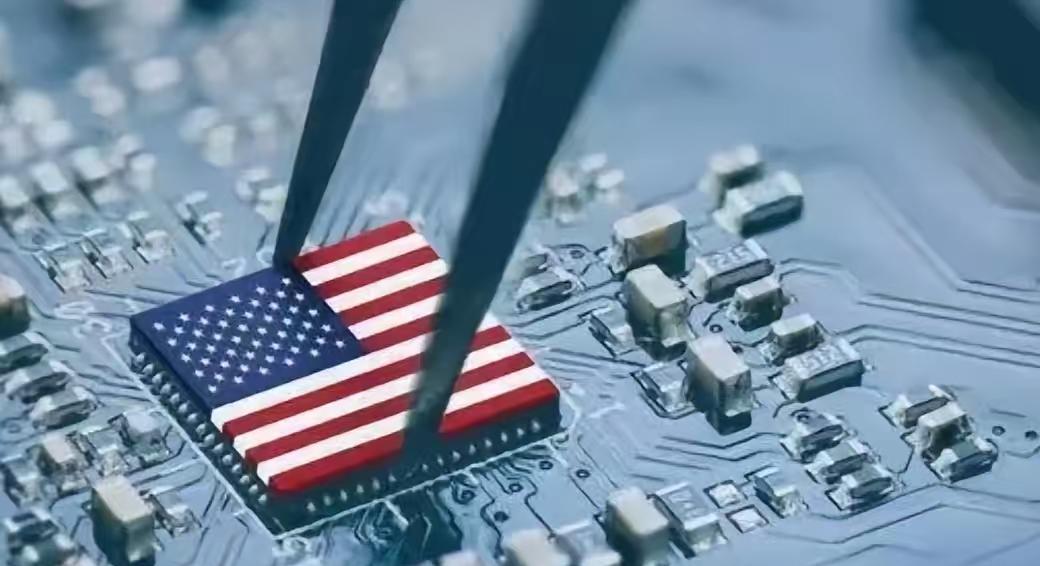“一天要服侍55个美军。”1945年,35万美军进驻日本,烧杀劫掠,民怨沸腾,日本为此制定了一个丧心病狂的方案。 西冈雪子小心翼翼地抚平手中那张皱巴巴的报纸,广告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但“高薪”“包吃住”几个字依旧刺眼。她咬了咬牙,推开宿舍的门,踏进了那个所谓的“涉外俱乐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墙角堆着破旧的木板,窗子上装着生锈的铁栅栏。她皱了皱眉,心中升起一丝不安,但很快被对未来的憧憬压了下去。 毕竟,战后的日本,活着就是最大的奢望。 几个月前,她的父亲在战场上阵亡,母亲不堪打击自尽,弟弟抢走家产后将她赶出家门。曾经的富家小姐,如今只能靠捡拾垃圾度日。报纸上的这份工作,像是一根救命稻草。她甚至幻想过,凭着自己会说几句英语,或许能在这家“俱乐部”里当个文员,攒点钱,重新开始。 然而,当她换上艳丽的和服,涂上浓重的口红,被领进一间昏暗的房间时,现实如一盆冷水泼下。房间里,几个美国大兵嚼着口香糖,吹着口哨,眼神在她身上肆无忌惮地游走。她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个士兵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粗暴地撕开她的衣襟。尖叫声在房间里回荡,却被门外士兵的笑声淹没。那一刻,西冈雪子才明白,这份“工作”是什么。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35万美军涌入日本。根据历史记录,美军占领初期,纪律松散,强暴、抢掠事件频发,引发日本民众强烈不满。为了“保护良家妇女”,日本内务省于8月18日下令在全国建立“慰安所”,征召女性为美军提供性服务,以平息士兵的“需求”。这一政策,表面上是“保护”,实则是将无数女性推向深渊。 西冈雪子并非孤例。19岁的田北夏江,家人在空袭中丧生,为了糊口,她也应聘了这份“女招待”工作。夏江性格温顺,喜欢在夜晚写日记,记录对家人的思念。然而,进入“慰安所”后的第一周,她的世界彻底崩塌。每天,她要接待15到60名士兵,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让她几近崩溃。一次,她试图趁夜逃跑,却被巡逻的日本警察抓回,毒打一顿后,她被关进一间更小的房间。几天后,夏江选择了卧轨自杀,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她的日记,被风吹散在铁轨旁,无人问津。 “慰安所”的设立,源于日本政府的无奈与妥协。战败后,日本经济崩溃,粮食短缺,失业率飙升。许多女性迫于生计,被“高薪工作”的谎言诱骗。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的记载,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约有6万至15万日本女性被征召为“慰安女”,其中许多是贫困家庭的女儿,甚至是未成年人。 这些女性被集中管理,每天以极低的报酬——有时仅1美元——换取无休止的屈辱。 美军士兵只需支付相当于半包烟的费用,就能获得“服务”,避孕措施形同虚设,导致性病迅速蔓延。据统计,驻日美军中有四分之一感染了性病,慰安所内的女性更是深受其害。 1946年3月,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迫于国际舆论和军属抗议,下令关闭所有慰安所。这一决定看似结束了女性的苦难,实则将她们推向另一个深渊。15万“慰安女”被解散,没有补偿,没有道歉,甚至没有身份证明。她们被社会贴上“玷污”的标签,无法回归正常生活。 许多人流落街头,靠在美军聚集的酒吧或咖啡馆继续“服务”维持生计。西冈雪子便是其中之一。她剪短了头发,换上破旧的洋装,站在东京街头,眼神空洞。曾经的琴棋书画,如今只剩一身病痛和无尽的屈辱。 夜色再次笼罩东京,西冈雪子站在街角,点燃一支廉价的香烟。她的身影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单薄而孤独。身后,酒吧里传来的美国士兵的笑声,刺痛了她的耳膜。她没有回头,只是深深吸了一口烟,吐出白色的烟雾,仿佛想将过去一并吐出。 “慰安所”制度的背后,不仅是日本战败后的屈辱,更折射出战争对女性的摧残。根据联合国1996年的报告,战时性暴力是全球性的历史问题,日本的“慰安女”制度并非孤例。战后,日本政府长期否认“慰安所”的强制性,直到1993年才发布《河野谈话》,承认部分责任。 然而,许多受害者至死未能等到赔偿与道歉。西冈雪子们的故事,提醒我们,战争的伤痕远不止战场上的硝烟,那些沉默的女性,同样是历史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