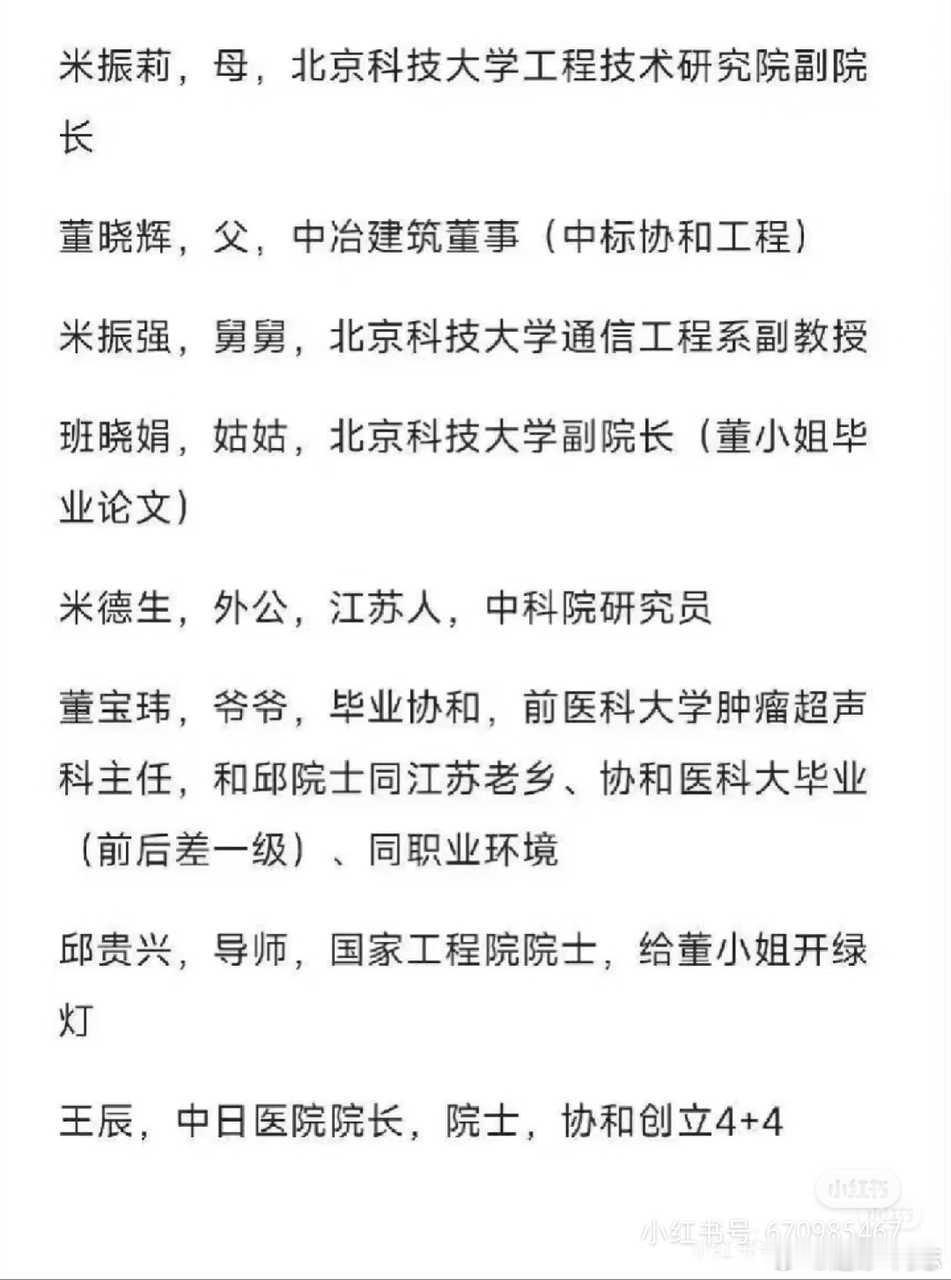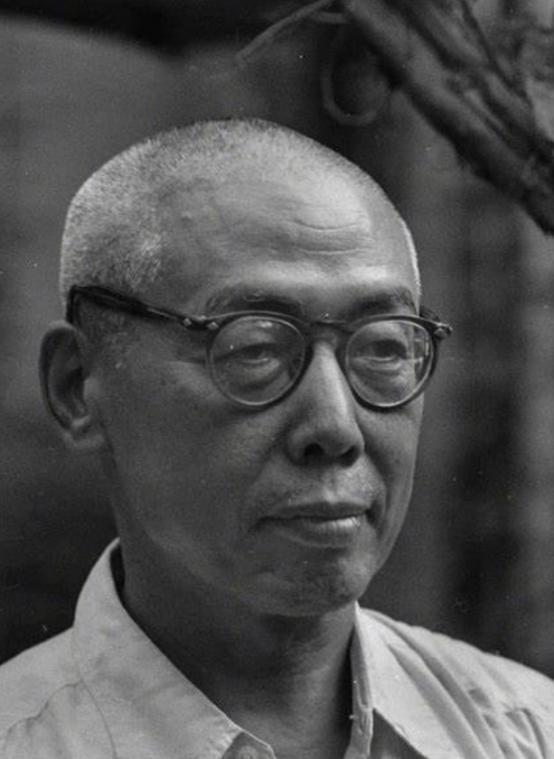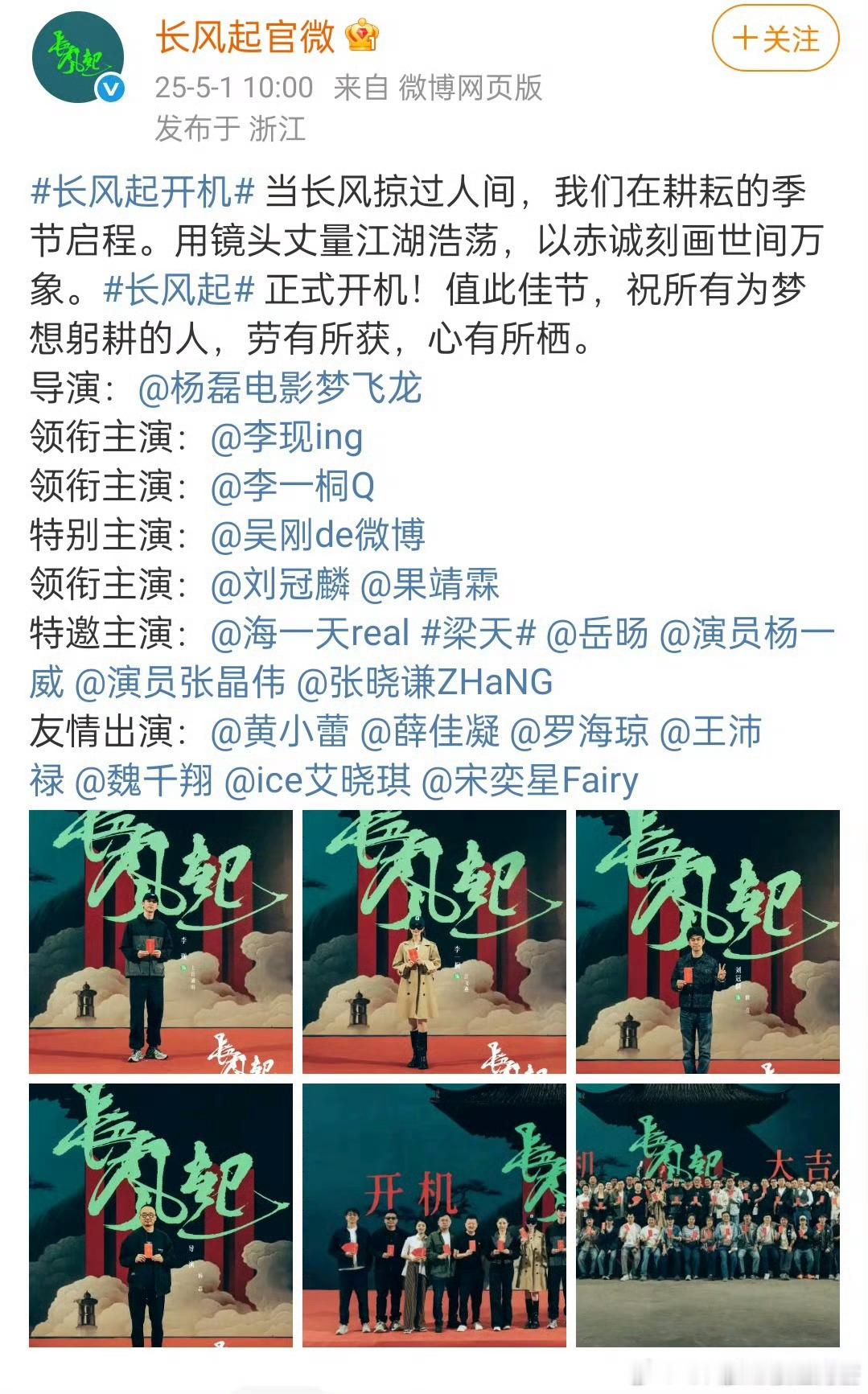1980年“中国第一性学家”李银河,嫁给了丑不拉几的清洁工王小波,婚前两人相约丁克,结婚17年无儿无女。一天,王小波从兜里掏出脏兮兮的50块钱,黯然泪下。李银河一把抱住他的丑脸说:“你那么聪明,就在家专心写文章吧,我养你!” 李银河与王小波的爱情,常常被传为佳话。 1980年代中期,李银河在《光明日报》供职。 彼时,她收到一篇署名为“王小波”的投稿稿件。 文章内容结构独特、语言幽默机智,又不乏哲思。 她详细研读数次,辨析文法、字句与结构安排,愈发觉得这位作者与众不同。 很快,她主动安排见面。 然而,初见王小波,他衣着随意、面貌普通,甚至略显邋遢,与她想象中的浪漫才子形象相去甚远。 虽然如此,两人依旧围绕文学与思想进行了一次长谈。 在这场交谈中,王小波的思维锋芒逐渐显露,谈吐间跳脱常规,极富个人见解。 此后,王小波开始频繁给李银河写信,信中洋溢着对自由、理性和人文精神的思索,并不时掺杂情感表露。 不久后,两人确定关系,并共同生活于一个不拘形式、自由开放的知识共同体之中。 结婚之后,他们达成共识,不生育下一代。 这种选择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相当罕见。 王小波继续写作,李银河也继续社会学研究。 然而,由于创作风格与主流出版格格不入,王小波的作品鲜有人问津。 当李银河赴美深造时,王小波毅然决定随行,并在异国努力维持生活。 他在繁重体力劳动之余依然坚持写作,直到李银河主动承担起家庭经济责任。 此阶段成为他产出最为密集的时期,《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等重要作品相继完成。 在他们的关系中,李银河始终以一种无所畏惧的态度面对世界。 她从不屈服于外界的评判,也从不被传统束缚。 王小波的去世对李银河而言,或许是人生中最为痛苦的时刻。 然而,李银河选择继续生活,继续追求自我。 她曾回应过外界关于她再婚的质疑,表示即便王小波依然在世,她也可能会爱上别人。 对于她而言,爱情不是一种奉献,更不是牺牲,而是自由与选择的体现。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她在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 她曾在年轻时对生命的意义进行过深刻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生命本身并没有固有的意义。 人活在世上,只有尽力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最重要的。 她不认为欲望是一种不洁或应被抑制的力量,反而认为人应该从中获得生活的动力。 王小波曾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李银河的爱中,王小波的情书《爱你就像爱生命》便是他对李银河深情的写照。 他并不以占有对方为目标,而是希望彼此自由地存在于彼此的生命中。 李银河也正是因为理解这种自由的爱,才敢于无所畏惧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而这种自由,并不仅限于爱情,也延伸至她对人生的所有选择。 尽管李银河的婚姻和爱情观遭到了一些质疑,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她与大侠的关系便是另一种对她人生观的体现。 大侠,这位跨性别者,原本是李银河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然而随着两人关系的发展,李银河开始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在其中找到情感的满足。 她从不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而是始终以自己为主导,去探寻更广阔的生活道路。 她对于“婚外情”的看法,亦如她对生活的看法那样直率。 她认为爱情的发生本身没有错,但处理不当则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她主张,如果真心爱上了别人,就应该及时结束现有的婚姻。 她的这一观点在当今社会尤为具有启发性。 1980年代,大多数中国人踏上出国之路时,都带着节衣缩食的紧张心态。 彼时的李银河,却显得格格不入。 她拥有能够独立谋生的学术能力,选择的是另一种不以功利为核心的生活方式。 与同时代人相比,她的行为举止更接近一种脱俗的从容。 1998年,她在《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中提出了独身主义在中国女性群体中的现实意义,并通过田野调查将研究深入至村落文化。 在早期的研究中,她已敏锐地指出农村女性承受的生育压力远超城市女性。 她并未停留于宏观理论,而是转向那些被长期忽视的边缘议题,包括同性恋、丁克家庭和虐恋现象。 她坚持认为,研究这些是试图让沉默群体的存在被看见。 尽管她本人坚定选择不育,但她因伴侣的心愿收养了孩子;她以爱情为人生核心,也对婚外情持明确反对立场。 退休之后,她与丈夫一同隐居威海,不再参与不愿意承担的公共事务。 她完成了自传《人间采蜜记》,并尝试小说创作。 参考文献:[1]姚俊采.爱情观现代转型与主体性觉醒:《傲慢与偏见》的女性主义分析[J].文学艺术周刊,2025(3):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