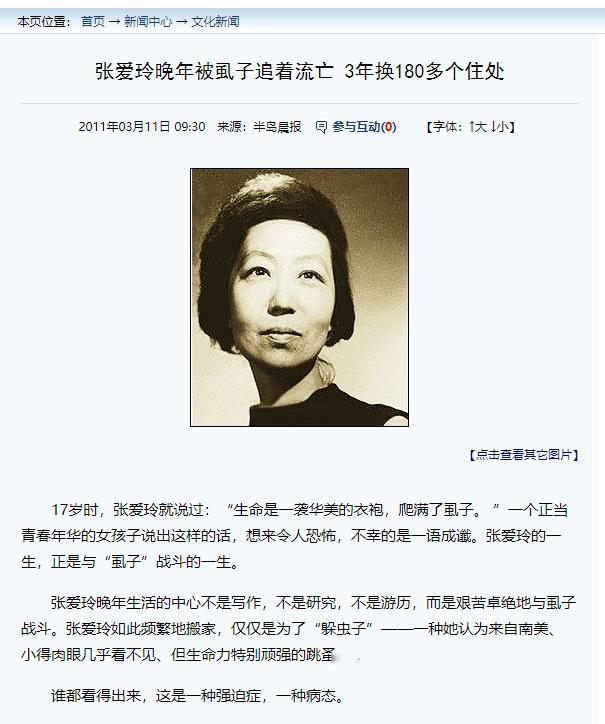1984年,年逾六旬的张爱玲拖着行李,在洛杉矶市内的汽车旅馆间不停搬家,只为了躲避虫子。 已经六十多岁的张爱玲在洛杉矶的汽车旅馆之间频繁搬家,只为了躲避虫子的困扰。她说自己被一种南美跳蚤叮咬,导致皮肤红肿,彻夜难眠。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虽然之后跳蚤问题得以解决,但她却始终担心身边有虫。医生认为这是她的心理问题,但这种咬啮性的烦恼却如影随形,即便她频繁搬家也难以摆脱。 张爱玲自幼生活在大上海的繁华与动荡之中,早早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她的文学作品广受赞誉,尤其是《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更是让她在文坛上声名鹊起。 然而,她的生活却并不如她的作品那般浪漫与美好。特别是晚年,孤身一人漂泊在异国他乡,生活中充满了各种烦恼和不安。 跳蚤事件不过是她晚年生活困扰的一个缩影。尽管搬家频繁,但她总是觉得身边有虫。 1989年,她的皮肤病终于痊愈,频繁搬家的日子暂时告一段落,她在一座条件不错的新公寓里定居下来。然而,好景不长,一位台湾女记者悄悄住到了她的隔壁,暗中观察她的行踪,翻检她的垃圾,并据此写了一篇《我的邻居张爱玲》,发表在台湾的报刊上。 这让张爱玲十分反感,她在朋友的帮助下立刻搬进了另一座公寓大楼,还小心地把信箱收件人改成了越南华侨的姓氏。 “她们为什么总是盯着我?”张爱玲无奈地对朋友说。 “别担心,我会帮你找个新地方。”朋友安慰道。 由于频繁搬家,张爱玲的信箱地址时常更换,很多寄给她的信件无法寄达,只好原路退回。后来,不断袭来的牙病、眼病让她疲于应付,就算信件到了她手里,她也经常无暇拆看。就这样,本来就喜欢“大隐隐于市”的张爱玲,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稀少,她的晚年生活也显得越发神秘。 1994年,张爱玲获得了台北文学界颁发的特别成就奖。为了这次盛事,她专门拍摄了此生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中,她头戴假发,面露微笑,手握一卷报纸,“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的黑体大字倚在脸侧,颇为怪异。她还专门配上了一首小诗,调侃自己已被死神绑架,“随时可以撕票”。 1995年秋日的一天,张爱玲的房东女儿发现她已两三天没有露面,就打电话报了警。待警察到达公寓,打开门,发现她独自静卧在客厅里唯一的行军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 她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毯子,手脚自然平放着,头发很短,遗容安详。行军床前的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在最后的日子里,她的皮肤病又一次复发,需要每天烤灯。另一侧地上堆放着一摞纸盒,纸盒前铺着地毯。 晚年的张爱玲已经习惯了因陋就简的写作环境,经常在纸盒搭成的“书桌”上写作。没有书籍,没有参考资料,倒是散落着不少报纸,有英文报,也有台湾寄来的联合报,还有几本翻烂了的侦探小说。 她喜欢将这些报纸铺展开来,摊在纸盒“书桌”上,寻找灵感。那些破旧的侦探小说,则是她在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陪伴,书页上留有她用红蓝笔画出的圈圈点点,仿佛是在与书中的人物对话。 临终前,张爱玲把重要文件和随身物品装进一个手提包,又把包放在门前的桌子上。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凝聚了她对人生最后阶段的深思熟虑。 她在整理这些文件时,手指轻轻划过纸页,每一页上都记录着她一生的心血。她的眼神虽然略显疲惫,却透着一股不易察觉的坚定。她知道,这些文件不仅是她个人生活的记录,更是她文学成就的见证。 那些散落的报纸也被她仔细地摞在一起,放在纸盒的旁边。每一张报纸上,都有她曾经读过的痕迹,有些地方甚至还有她写下的批注。她常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起一张报纸,静静地读上半晌,仿佛是在寻找某种久违的安慰。 她的手提包里,不仅装着她的重要文件,还有一些她最珍爱的个人物品。她把自己常用的钢笔、一本翻旧的日记本、几张珍贵的照片都小心翼翼地放进去。 每一样东西都承载着她的记忆,代表着她生命中某个重要的瞬间。她希望这些物品能够陪伴她走完最后的旅程,也希望它们能在她离开后,帮助她的朋友们更好地理解她的一生。 张爱玲在整理这些物品时,心中回荡着对过去岁月的无尽感慨。她曾经是那个站在文坛巅峰的天才作家,却在晚年过着如此简朴而孤寂的生活。 她的心中充满了对故土的怀念,对那些曾经陪伴她的朋友和亲人的思念。但她深知,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无法再回到那个充满欢笑和泪水的时光。 她离世后,前来处理后事的警察在第一时间就拿到了她的全部资料,这也方便了她的朋友们遵照遗嘱办事。她的朋友们按照她的遗愿,不露遗容、不搞葬礼,将她的骨灰撒在了大海里。在她去世后,经她修改多年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正式出版,这部作品以文学的语言回顾了她的一生,成为她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