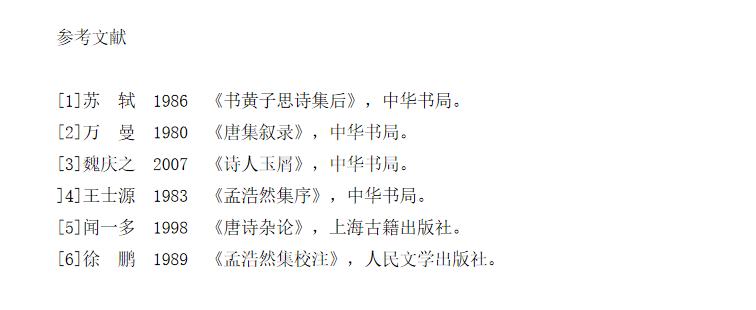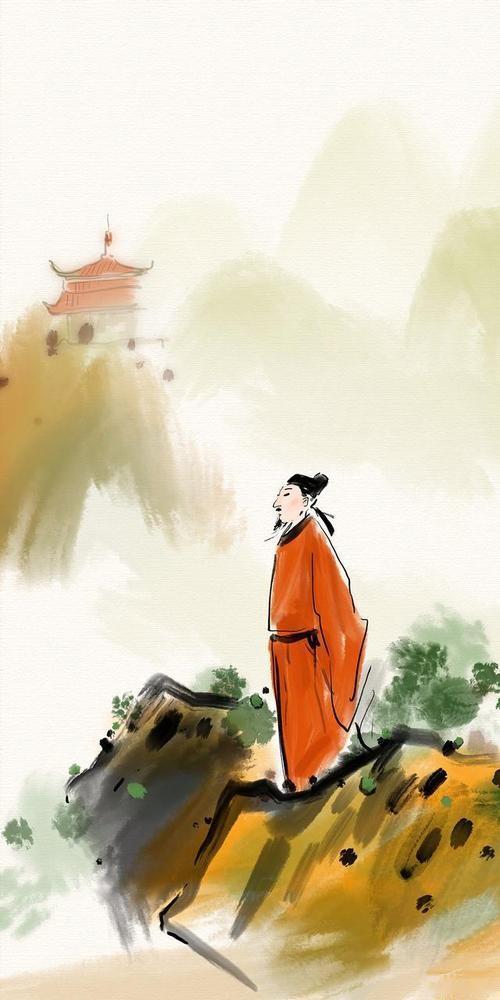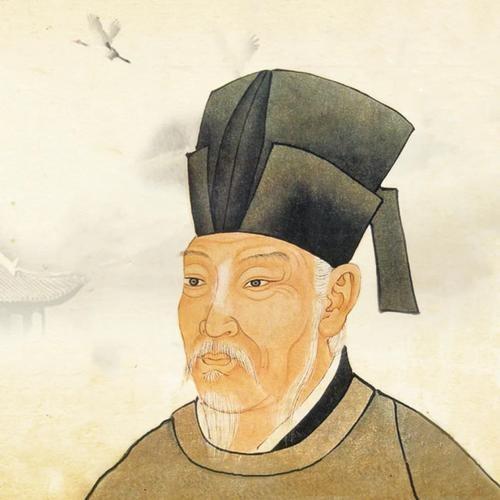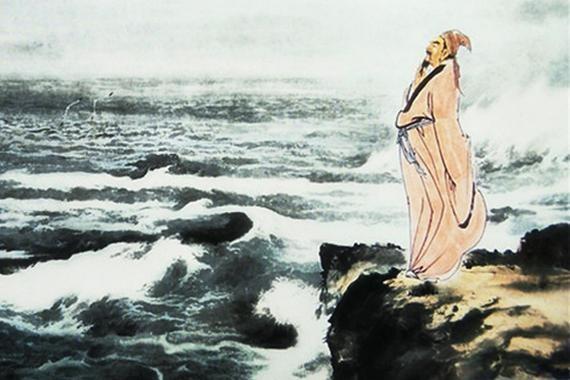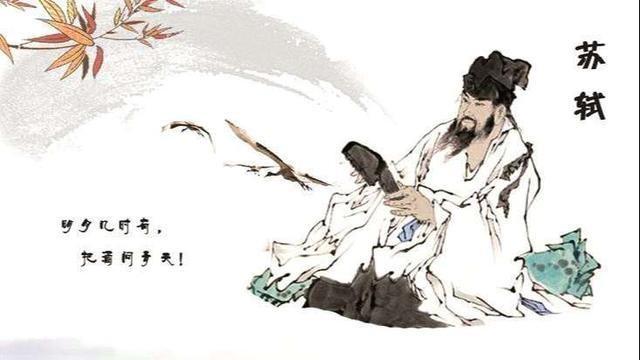苏轼如何理解“韵”与“才”?从他的诗歌理想,进而反思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 “韵高而才短”即苏轼基于个人诗歌理想所作出的评价,若要探求“韵高而才短”,仍需要还原苏轼心中的“韵”与“才”,进而反思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 苏轼以“才”闻名,其诗歌雄豪发露、酣畅淋漓的格调无不彰显他闪烁的才气。 其诗歌“才”的形成同题材、写作手法、诗歌体式等都密不可分,这正是苏轼评价孟浩然“才短”的原因,孟浩然之诗既得益于山水田园的主题和写作风格,也受其制约限制,苏轼正是在此意义上对孟浩然之诗进行评价。 苏轼的着眼点是对一个时代的一个诗人的整体评价。本文所提及的“才”不只是指诗人在作诗艺术上的精湛工艺和非凡学问,还涵盖了诗人的全面素养、文化修为及创作力,也就是说,诗作才华。 这种才华在他们的诗作中得到体现,需要诗人具备广泛吸收、融会贯通的能力,同时还得有超越时代,创作出彰显个人独特风格的艺术佳作的本领。 这也就是《书黄子思诗集后》上述这段话中苏轼不遗余力赞美李白与杜甫的诗歌的原因。 诗体单调总的来看,孟浩然对于诗体的把握稍显单调,多为五言,少有七言。而各代的批评家对此都有留意。 相关学者以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为准,对孟浩然不同诗歌体式进行统计。其中五言诗合计占其诗歌创作的94%有余,七言诗寥寥无几。 孟浩然所写诗歌大都选用前人反复沿用的诗体形式,缺少对新的诗体的关注与创新。 同时其五言古诗、五言排律七言古诗,篇幅都较短,在同一篇目之中缺少韵律节奏的变化,大都一韵到底,如《过故人庄》《春晓》《过洞庭湖赠张丞相》等都是全诗从头至尾一个韵,其较长的诗作如《田园作》《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行出东山望汉川》等也是一韵到底。 由此可见,孟浩然缺少对于诗歌的体式结构的创新,没有全面的发展。这是其“才短”的原因之一。 然而,从以上的数据仅能在一定程度反映孟浩然对于诗歌体裁的掌握并不全面,并不能全面反映孟浩然的诗歌创作能力。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考虑到孟浩然诗作中核心的主题和含义,以及他试图传递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意境,哪一种题材能最恰当地作为其表现手段?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山水田园诗以其独特的魅力占据了一席之地。这类诗歌,以其清新自然、宁静恬淡的风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象与田园风光。 在诗人的笔下,山水、田园、农村风物以及那种恬淡安详的隐居生活都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色彩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对于山水田园诗人来讲,如谢灵运、王维与陶渊明,所作之诗大多都为五言诗:陶渊明没有七言诗,多为五言,甚至还有四言诗;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也多为五言;谢灵运感受山水田园的时候更是没有七言出现。 虽然这与诗的形式进化紧紧相关,但同时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简洁精炼的五字古诗较之波澜壮阔的长篇作品,可能更适宜用以传达诗人在默观自然时的内心平静与和谐。 同样地,它更有力地包罗和显现了一种完美无瑕、洒脱自如的艺术境界。 同山水田园诗歌类型的创作表达需要不谋而合。因此,后世对于孟浩然“诗体单一”的论断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单一的诗体并不能完全证明孟浩然的诗料不充分,创作能力不高。 题材范围狭窄孟浩然是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但是其题材却大多囿于山水田园,没有跳出题材的局限,可见其诗歌题材选择范围并不宽泛。 首先,孟浩然生于盛唐,但其诗歌题材并未书写这个时代鼎盛繁华,而是逃避世俗囿于山水田园。 明活字本《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三卷将孟浩然诗分为“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田园、美人、时节十类”,但如果具体分析,其实其中不少诗歌类型可以合并在一起。 如《过故人庄》可以被划分类型为田园、旅行、游览、时节、宴乐等;万曼在《唐集叙录·孟襄阳集》也曾点评孟浩然诗“游览类既有《春晚》诗,又有《初秋》《九日》等诗别出时节一类。 孟浩然诗游览与时节可合为一类、美人与怀思可合为一类。 他的大部分作品,抒写了与一些高人、隐士以及与他同一知识阶层人士的交往,表达了他们之间宴游、酬赠、离别和怀念等等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或者表现对田园隐居生活的向往和歌颂,抒发自己因政治上不得志而产生的失意情绪”。由此可见,孟浩然的诗歌选题更多局限于诗人个体,没有抒写时代情怀,表现时代风貌。 总结: 对后世而言,对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的评价与对苏轼评价的分析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辅相成,共同揭示唐宋诗词的差异。 这种对比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唐宋两代诗歌的特点,还能为我们提供独特的视角来欣赏和评价这两位文学巨匠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