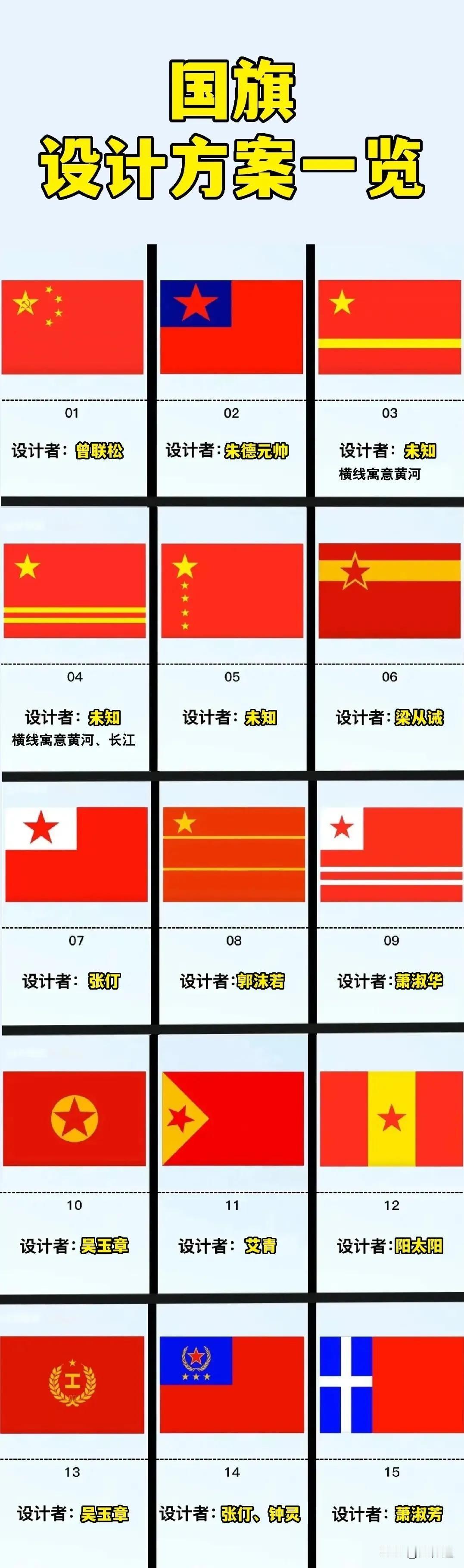1939年冬天,重庆嘉陵江边阴雨连绵。临江的一栋旧楼里,郭沫若正伏案写作,忽然停下笔,对身边人低声说了一句:“我在四川,还有一位名义上的妻子。”这句看似随口的话,背后牵出的是三段纠缠一生的情感,也是旧家庭制度、战乱年代与个人选择交织在一起的一段辛酸往事。
说到郭沫若,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学者、诗人、政治家这些耀眼身份,却很少有人真正去追问:那个在族谱里写作“元配”的女人,到底是怎样活完自己的一生。
转回时间,要从1912年前后的自贡说起。
那时的郭开贞(郭沫若原名),正从一个恢宏志向的青年,走向彻底反叛旧礼教的知识分子道路。而在同一片土地上,一个少女的命运,悄悄被系在他身上。
她就是后来“独守空房六十八年”的张琼华。
一、包办婚姻中的两个人
清朝刚刚覆灭,民国刚刚建立,许多旧习俗并没有立刻消失。四川自贡一带,重门深院、媒妁之言,依旧主导着多数女子的人生。
张琼华出身本地望族,自小在闺阁里长大。她读书不多,却很懂规矩。父母替她定下的丈夫,是已经考入名校、有“读书种子”之称的郭开贞。在长辈眼里,这门亲事,算得上门当户对。
张琼华并未对未来婚姻做过多少幻想。她知道的道理很简单:嫁过去,就要守本分,服侍公婆,照顾丈夫,延续香火。命怎么安排,就怎么活。
而另一边,郭开贞的内心,却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辛亥风潮席卷全国,新思潮、反封建、提倡男女平等等观念,接连传入西南。他在学校里读新书,接触《新青年》,对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渐渐生出强烈反感。这个时候忽然被告知婚事已经定下,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排斥。

抗争过。和家里红过脸。甚至想过逃婚。
可在父权极重的家庭里,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很难撼动既有安排。嘴上辩不过,手上也没有实际的反抗手段,最终只能被推上迎亲花轿那一天。
怨气压在心底,找不到出口,就只好转移到那个从未谋面的新娘身上。
洞房花烛之夜,红烛高烧,鞭炮未散。不少记述提到,郭开贞推门进新房,远远站定,先看到的是一双被绣鞋包裹的三寸金莲。
对于刚接触过西方思想、极力反对裹脚制度的青年来说,这一幕像是一盆冷水浇下来。旧礼教的象征,就这么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他几乎立即在心里做出判断:这不是想象中的伴侣,而是一种他正试图挣脱的旧世界的延伸。
按礼数,他还是替张琼华揭开盖头。烛光里的新娘,相貌普通,神色局促,眼神躲闪,身上带着传统女性那种小心翼翼的顺从。偏偏这些特点,与他所理解的“新女性”完全相反。
短短一个晚上,两个人的距离,不是从零起步,而是拉开得更远。
洞房夜本该是新生活的开端,对张琼华来说,却在悄无声息间,变成了漫长孤独岁月的起点。
第二天,第三天,郭开贞与族人应酬应付,而与新婚妻子的相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第五天,他干脆背起行囊,借口求学、谋前程,离家而去,再无归期。
婚房还在,新人的衣物还挂着。张琼华却从一个新嫁娘,一下被丢在名存实亡的婚姻里。
从旧礼教的角度看,她已经是郭家的人,是郭家的“媳妇”。从现实生活看,她却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姑娘,而成了一个夹在中间、不知如何自处的角色。

这种尴尬和无奈,在那时的很多旧式家庭女子身上,都不同程度存在。只是张琼华遇到的,是一个冲得更快、走得更决绝的丈夫。
1914年,郭开贞离川东渡,前往日本留学。这一去,不仅是求学,更像是对旧婚姻的一次“逃亡”。
张琼华则留在自贡,住在郭家宅院,起早贪黑照料公婆。邻里眼中,她是“郭家媳妇”,却几乎没有享受过丈夫在侧的日常。
二、远在日本的“安娜”和郭家旧宅里的张琼华
有意思的是,离开四川之后的郭沫若,很快迎来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感情选择。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接触新思想更密集,学习更加用功,社交圈也比在家乡广阔。也就在这段时间,他遇到了改变自己后半生创作状态的女子——佐藤富子。
这位日本姑娘出身书香门第,会日语、懂西学,气质开朗,与他热衷讨论文学与社会问题。两人初见,颇有一见如故的意味。久而久之,从学友走向恋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佐藤家得知女儿与一位中国留学生往来十分密切,自然不乐意。一边是有固定社会地位的日本男子,一边是境遇不稳定、未来还不明朗的外国青年,传统父母的态度可想而知。
按照当时的日本社会氛围,跨国婚姻本身就很少见,更何况是与一个来自战乱频仍国家的年轻人结成伴侣。
佐藤富子最终做出的选择,颇为决绝。她宁可与父母决裂,也要与郭沫若在一起。可以说,情感上的投入毫不保留。
郭沫若为她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安娜”。这个名字后来在很多文章、回忆录里频频出现,成为他创作生涯中的关键一环。
在安娜身边的那些年,郭沫若的诗歌创作非常旺盛,《女神》等作品相继问世。生活上,他们在日本组建起一个家庭,先后有了五个孩子。带孩子、操持家务、照顾丈夫的生活节奏,对安娜而言并不轻松,但她认准了这是自己甘愿承担的道路。

与此同时,远在四川自贡的郭家老宅里,张琼华仍然维持着“郭家媳妇”的身份。
她每日替公婆张罗三餐,料理家务,过年过节准备祭祀。邻里若提起郭家大少奶奶,评价多半是“勤快”“守本分”“不多嘴”。看上去,她和许多传统妇女一样,安静地被束缚在家庭责任里。
只是,在“媳妇”这件事之外,她没有别的角色。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
从法律上看,她仍然是郭沫若名义上的妻子。郭家也很明确地向外表示:张琼华“生是郭家人,死是郭家鬼”。既不提离婚,也不给她另寻生活出路的可能。看似保障了她的“名分”,实则是把她牢牢捆在一段空洞的婚姻里。
郭沫若在日本时,偶尔会写信回家。在给张琼华的信里,他曾表达过一种颇为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承认当年的包办婚姻对两人都不公平,希望她不要怨恨自己;另一方面,又坦言自己无法改变旧制度给她带来的束缚,只能远远表示一点歉意。
对张琼华来说,这些话并不能改变现实。她既无法像安娜那样主动追求爱情,也很难像一些性格激烈的女子那样冲破家庭束缚,离家另嫁。
长时间的等待与失望之后,她慢慢把一切归于“命”。既然进了郭家门,就要守到底。她曾被裹足,又被旧婚姻捆住,说到底,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娜后来遭遇的转折。
抗战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决定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参加抗战。这一步,出发点并不复杂——国家有难,知识分子希望尽一份力,这是许多人真实的心态。
但是,这个决定,对安娜和孩子们而言,就不只是政治选择,而是家庭命运的巨大转弯。
郭沫若回国后,并没有立刻接走安娜一家。他急于投入工作,再加上局势多变,一拖再拖。安娜原先以为,这只是短暂分离。可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失去丈夫后,原本就不太被家人看好的跨国婚姻,在日本当地舆论中更显尴尬。她带着几个孩子独自承担生活压力,名声也受到影响,日子一步步艰难起来。
很多年里,她始终坚信:“他总会回来的。”这种近乎执拗的信念支撑她走完长夜。但现实给出的答案,与她想象的并不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她干脆带着孩子来到了中国,试图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找回那个曾经许诺过未来的男人。
然而,这时的郭沫若,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三、于立群的出现与“衣锦还乡”的那一面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文化工作逐渐增多。他辗转多地,写文章,发表演说,参与组织。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另一位女性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于立群。
于立群出身破落官宦之家,少年时期并不宽裕。十四岁考入上海明月歌舞剧社,独自南下谋生。年轻女子独自闯荡大城市,在当时极不容易,既要养活自己,又时刻面对流言和偏见。
之后,通过邓颖超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接触到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在战地、在后方,她承担联络、宣传等工作,慢慢变成一个既能办事,又肯吃苦的女同志。
在共同工作、共同奔波的岁月里,她和郭沫若从战友逐渐靠近。彼此欣赏,对事业的认同感、对时代的理解,拉近了心灵距离。一些同志曾评价他们的结合,有利于在特殊环境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是政治立场与生活选择叠加后的结果。
这一段感情,与张琼华的“静”,与安娜的“执”,都不一样。它更贴近现实斗争、更带有时代色彩。
婚后,于立群其实并非天生“贤内助”。她缺少生活经验,第一次面对新生儿时手忙脚乱。为儿子做衣服,只会干脆把布铺在地上,把孩子放在上面,照着轮廓剪裁,成衣歪歪扭扭,却透着认真。
慢慢地,她学会缝衣做鞋,学会安排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学会如何在紧张的工作与家庭琐碎之间,找到自己的节奏。

抗战期间,郭沫若客居重庆,他在这里写下不少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作品,宣传抗战、抨击投降思潮,这些文字在当时的文化战线上起了不小作用。许多人后来回忆,若没有于立群在家中操持,腾出他的精力,他未必能够如此高产。
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交往,也多在这个时期增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从日本回国,一直希望前往延安,亲自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由于身处国民党控制区,多次尝试未果。
1945年抗战胜利,毛泽东应邀赴重庆谈判。这次历史性的重庆之行,让两人有了面对面交谈的机会。郭沫若对毛泽东的敬重,由来已久。见面之后,两人谈形势、论古今,相谈甚欢。
有一个细节流传很广:一次会面时,毛泽东腕上没有手表,郭沫若看到后,随手解下自己佩戴的那块表,递过去:“领袖总要知道时间。”这句客气话背后,是他对对方的真诚敬意。
毛泽东对这块表看得极重,多次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弄丢,不要随意借给他人。表曾经维修,表带也换过,但一直佩戴至晚年,由此可见两人之间情谊之深。
与此同时,在自贡的郭家老宅里,张琼华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时光一天天过去,她从二十多岁守到中年,又守到老年。郭沫若在国内外奔波、写作、演说,她则在老家与农事、家务相伴。两个人的世界,虽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却像分裂成完全不同的画面。
真正把这两幅画面强行拼在一起的,是郭沫若“衣锦还乡”的那一刻。
离家三十年后,他终于回到四川老家。身份今非昔比,人也已声名在外。这次返乡,身边多了一个光彩照人、说话干脆的新式女性——于立群。
族人亲友纷纷围上来迎接,气氛热闹。旧宅中,张琼华远远看着这一切。她年纪并不算太大,却因长期操劳、营养不济,看上去风烛残年。脸上皱纹极深,身形干瘦,衣着朴素,与那位从外地来的女伴形成强烈对比。
有亲友悄声议论:“这就是大嫂么?像老太太了。”类似的话,难免传进她耳朵。她看着只比自己小两岁的男人,仍然精神矍铄,风度不减。一瞬间,卑微之感几乎要把她整个人埋住。
不过,郭家长辈并没有忘记她这些年的辛苦。有人当面对郭沫若讲起:“要不是她撑着,这个家早就散了。”郭沫若听完,沉默了很久,随后在众人面前向张琼华深深鞠了一躬。那一躬,角度几乎是直角。

“谢谢你这些年替我尽孝。”大意不外如此。
对旁人来说,这是一幕颇为动人的场景。但对于张琼华,复杂心情外人很难代入。她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肯定,也得到了那一句迟来的感谢,却仍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改变——她依然是“郭家媳妇”,依然没有丈夫与子女的陪伴。
这次返乡,他只短暂停留,又匆匆离开。旧宅再次安静下来。院里晾着的衣服,又只属于她一个人。
四、北京的信件和每月十五元
时间到了1960年代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动,许多人的命运随之起伏。
1963年前后,郭沫若已经在北京担任重要职务,声望极高。就在这个阶段,他把张琼华请到了北京住上一阵,算是对她一生付出的某种“补偿”。
这一趟北京之行,对张琼华来说,是第一次真正走出四川去看外面的世界。她见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城市,也见到了与自己生命轨迹完全不一样的那群人。
她从未在公众场合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借机大闹或控诉。仍旧是那种谨小慎微的姿态,坐在旁边,静静看着郭沫若接待来客、处理公事。
按一些回忆,她在北京短暂逗留后,又回到四川。终究对这座城市,她只是过客。
张琼华这一生,从未有过子女。家族的香火,由其他支系继承。她的名字,只挂在族谱某一页,身份标注为“郭某某元配”。简单几个字,背后是一段被压缩到极致的寂寞岁月。
更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尽管整整守了一辈子,她在生活上并未得到太多物质保障。为了维持起码的生计,她一向习惯自己想办法,能不麻烦别人就不麻烦别人。

直到年老体衰、走投无路,再也难以靠劳作维持生活,她才鼓起勇气写信到北京,向郭沫若寻求帮助。
在那封信里,她没有大段控诉,只是客客气气地说明现状:“生活有些困难。”字句谨慎,小心翼翼,仿佛开口要钱是一件极其难为情的事。
郭沫若收到信后,开始固定寄钱给她。起初是每月十五元。别小看这十五元,在当时的购买力之下,已经足以解决基本口粮问题。随着物价变化,这个数额后来有所增加。
每次收到钱,张琼华都会认真写一封回信。信里感谢之意写得很重,语气有一点受宠若惊的味道。她反复说“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只算是“借用一下”,有能力时愿意慢慢还。
这种态度,与其说是卑微,不如说是那一代普通妇女骨子里的一种自我克制。哪怕名义上是“妻子”,在现实里,她从不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索取什么。
有人评价,郭沫若终究没有完全忘恩,算是尽到了一点晚年的责任。但若从张琼华的整个人生来看,这些钱更像是一种迟到太久的象征:既无法弥补她青春年华的空白,也无法填满她情感上的缺位,只能保证她在生命最后一段路,不至于饿肚子。
与此同时,于立群和郭沫若在北京的家庭,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两人共同生活的那些年,于立群既是贤内助,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只在厨房打转的女人”。她学会做中餐西餐,招待客人时手脚麻利,菜品味道极好。许多到家里做客的人,对她的厨艺印象深刻。
周恩来曾多次半开玩笑地说:“小于做的饭好吃,小于很能干。”这种评价,既是赞许,也是对她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平衡能力的一种肯定。
考虑到当时郭沫若一家经济并不宽裕,党组织曾于1942年支持于立群创办群益出版社,既为国家文化事业服务,也为家庭增加一份收入来源。后来资金紧张,她把托管幼稚园结余的款项全部挪到出版社,硬是把这个文化阵地撑了下来。
三年后,郭沫若受邀赴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临行前,于立群张罗经费,替他准备行装,接待前来道别的朋友,安排得井井有条。
更重要的是,她并不把自己局限在家庭角色上。学俄语,读政治经济学,写散文、发表文章,参加妇女联谊会等活动——这一系列经历,说明她把“妻子”与“社会人”的身份结合起来,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时代。

从效果看,郭沫若能在政治、学术、文学多条战线上同时发力,背后确实离不开她这样的帮手。这也是后来一些人谈及时,会说“他的成功,有她的一份功劳”的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张琼华从未有机会走到这样的人生舞台上。她的教育背景、成长环境、时代局限,都注定了她只能在深宅大院里,完成长辈期待的那一套生活。
如果从情感角度去看,张琼华、安娜、于立群三位女性,仿佛构成了一种复杂而残酷的对照。
一个被包办婚姻困住,守着本不属于自己的空房;一个为爱情与父母决裂,却最终独自抚养五个孩子;一个在硝烟与变局中,与伴侣并肩前行,成为家庭与事业的双重支柱。
她们没有谁是“完全失败者”或“绝对幸运儿”。只能说,在同一个时代里,面对同一个男人,每个人承担的命运重量与方式不同。
至于郭沫若自己,对原配张琼华心底里是有愧疚的。无论是那次九十度鞠躬,还是晚年坚持每月寄钱,客观上都说明这一点。
但人的一生,有时就是这样:做过的选择,一旦与时代洪流叠加,往往很难回头。能做的,只剩下一点零散补偿与无声叹息。
张琼华在四川的老屋里,静静度过了晚年。身边没有子女,只有一些亲戚邻居偶尔照应。她守了一辈子的“郭家媳妇”身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放下。族谱上,她的名字后面仍然挂着“元配”二字。
这一生,在外人看来波澜不惊,连戏剧性的起伏都不多。但把时间轴拉长来看,那六十八年的独守,实际上承载了整个旧式婚姻制度的残影。
一个人的故事,有时比一本厚书更能说明问题。张琼华的命运,安娜的坚持,于立群的选择,连同郭沫若在不同阶段做下的决定,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一个侧影。
不夸大,不渲染,只把这些事实摆出来,也足够让人回味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