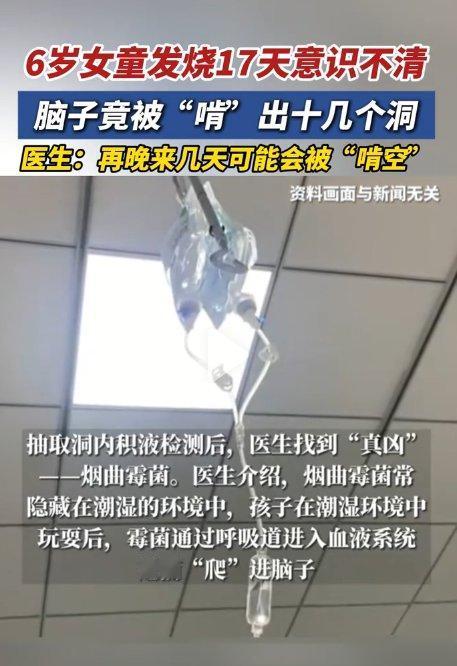昨天我在酒店值班,一个三十多岁的美女来开房。我觉得她有点不对劲,就用备用房卡开了她的房间。发生在我面前的事情真的让我很惊讶。 门推开一条缝,房间里没开大灯,只有床头一盏小灯昏黄地亮着。她没坐在地上哭,也没撕照片,而是端端正正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正拿着钢笔一笔一划地写着什么。台灯的光晕照着她的侧脸,还能看见没干的泪痕,但表情异常平静。听见动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惊讶,也没生气,只是很轻地说:“门没锁严吗?不好意思,我写点东西,很快就好。” 我僵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她反而笑了笑,放下笔,“进来吧,正好,我也需要个见证人。”我鬼使神差地走进去,瞥见笔记本上工整的字迹,抬头写着“离婚协议书(补充条款)”。 她合上本子,从那个名牌包里,不是拿出化妆品,而是掏出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是各种票据、房产证复印件,还有几张银行流水单。“八年婚姻,感情没了,账得算清。”她声音还是有点哑,但条理清晰,“这是共同财产的证据,这是他转移资产的流水……我咨询过律师了。”她指了指笔记本,“刚才在写的,是我对孩子探视权的具体诉求,一周几次,假期怎么分,写得越细越好。” 我愣住了,这和我预想的崩溃场面完全不同。她深吸一口气,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刚才上来那会儿,是真觉得天塌了,想躲起来再也不见人。可坐在房间里,看着结婚时他送的这个包,”她拍了拍手边的包,“突然就觉得没意思。为不爱自己的人毁了自己,太蠢了。” 她站起来,把文件袋和笔记本仔细收好。“谢谢你开门,”她对我点点头,“不然我可能还要自己闷头哭很久。现在不了,我有好多事要做。”她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明早九点,约了律师。今晚得睡好。” 我退出房间,帮她轻轻带上门。走廊地毯很软,听不见任何脚步声。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门,心里那点担忧,慢慢变成了别的什么。 后来她退房时,换了一身利落的西装裤装,眼圈还有点肿,但背挺得笔直。经过前台时,她对我笑了笑,不是客套那种,是真的很轻很亮的一个笑。 那晚之后,我偶尔还会想起她坐在灯下写字的模样。原来人最崩溃的时候,不一定是一地狼藉,也可能是擦干眼泪,开始一笔一划,为自己争取往后的每一分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