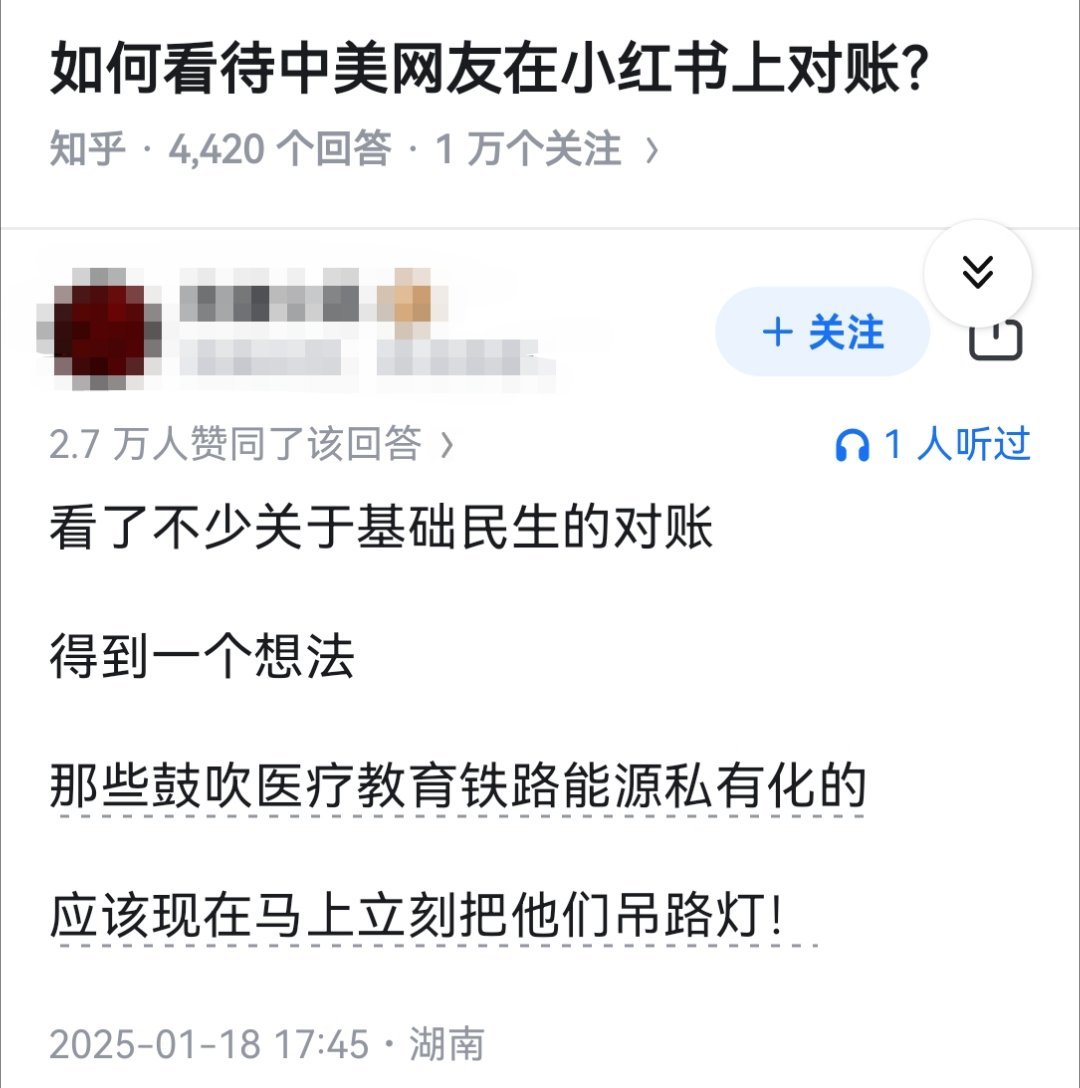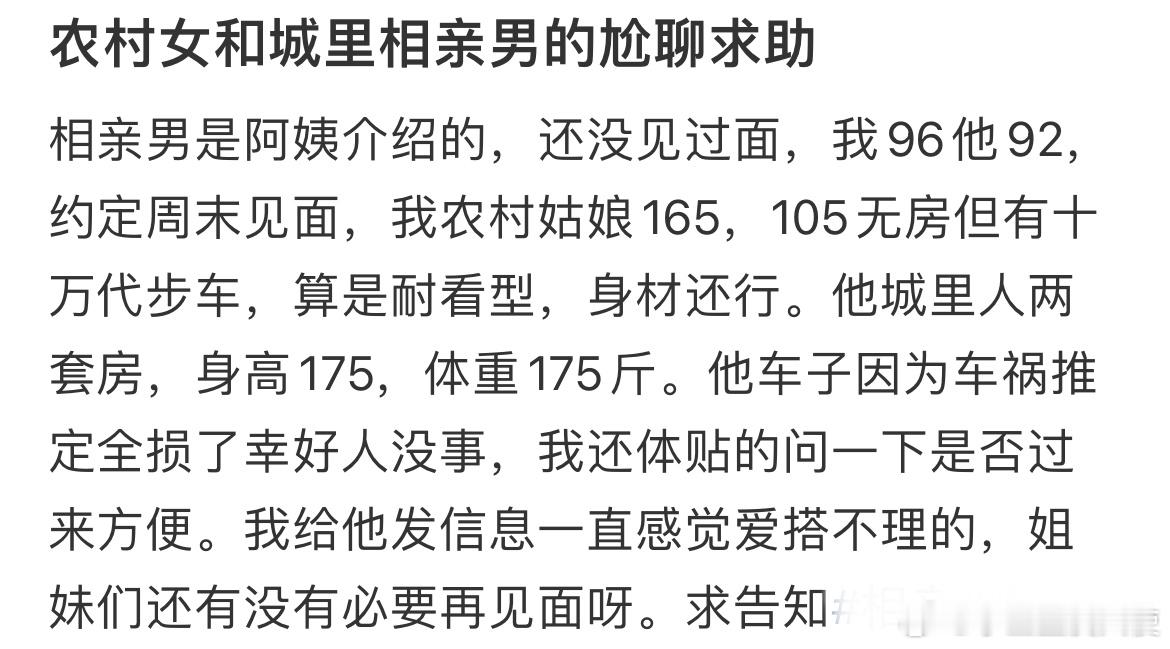1939年延安的那个午后,蜜月未满的余家英正凝视着熟睡的丈夫陈宝琦,掌心还攥着他送的怀表,表壳内侧“等待胜利”四个字温热清晰, 这枚黄铜怀表不是什么名贵物件,表链都磨出了浅痕,却是陈宝琦最珍视的念想——他的父亲是北平城里的爱国教员,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后,因为拒绝给侵略者站台,被宪兵队带走,再也没能回来。临终前,老人把这枚伴随自己教书半生的怀表塞给儿子,只说了一句“莫忘家国”。陈宝琦揣着怀表一路南下,从北平到西安,再徒步穿越封锁线抵达延安,每一步都踩着烽火,每一夜都枕着思念。在抗大的课堂上,他结识了负责文书工作的余家英,这个扎着麻花辫、写字时总皱着眉头的姑娘,把伤员的病历整理得一丝不苟,把宣传标语写得笔力遒劲,让他在颠沛流离中看到了安稳的希望。 他们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红烛,没有喜宴,战友们凑了半袋小米、几双布鞋,在窑洞外的枣树下,由教导员证婚,就算成了亲。新婚之夜,陈宝琦把怀表递给余家英,用小刀在表壳内侧刻下“等待胜利”,指尖划过她的手背:“等把小鬼子赶出去,我带你回北平,看故宫的雪,吃前门的糖葫芦。”余家英当时没说话,只是把怀表贴在胸口,听着表针滴答,像听着两人共同的心跳。她知道,丈夫说的胜利,不只是他们小家庭的团圆,更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安宁——就像延安城里每一盏深夜亮着的油灯,不是为了照亮自己,而是为了刺破黑暗。 陈宝琦是抗大的军事教员,白天给学员们讲战术、练射击,晚上就着煤油灯写教材,常常熬到后半夜。余家英心疼他,每天清晨都会把掺了小米的粥熬得稠稠的,把他磨破的袖口缝了又缝。有一次,陈宝琦带领学员进行野外拉练,遭遇了日军的小股侦察队,双方在山坳里激战了半天。消息传回延安时,余家英正在整理伤员名单,手指突然僵硬,手里的钢笔掉在纸上,晕开一片墨迹。她强忍着眼泪,把名单整理完,才跑到村口的大槐树下等,从日出等到日落,直到看到陈宝琦带着学员们平安归来,军装沾满尘土,胳膊上还缠着绷带,她才扑过去,死死攥着他的手,眼泪再也忍不住。 “哭啥,我这不是好好的?”陈宝琦笑着擦去她的眼泪,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捡来的野果,“给你留的,甜着呢。”余家英咬了一口,酸中带甜,眼泪却流得更凶。她知道,在这个烽火连天的年代,每一次分别都可能是永别,每一次重逢都值得感恩。这枚怀表成了她的精神支柱,丈夫外出执行任务时,她就把怀表放在枕边,听着表针的声音,仿佛丈夫就在身边;遇到困难时,她就摩挲着“等待胜利”四个字,告诉自己不能放弃——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都在为这个目标奋斗,她没有理由退缩。 1939年的延安,物资匮乏,条件艰苦,却处处充满着希望和力量。余家英和陈宝琦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却在烽火岁月中愈发坚定;没有海誓山盟的誓言,却用“等待胜利”的约定,书写着最动人的家国情怀。他们知道,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只有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才有真正的岁月静好。这枚小小的怀表,不仅承载着一对夫妻的思念,更见证着一代中国人在苦难中不屈不挠的抗争,在黑暗中执着追求光明的信念。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