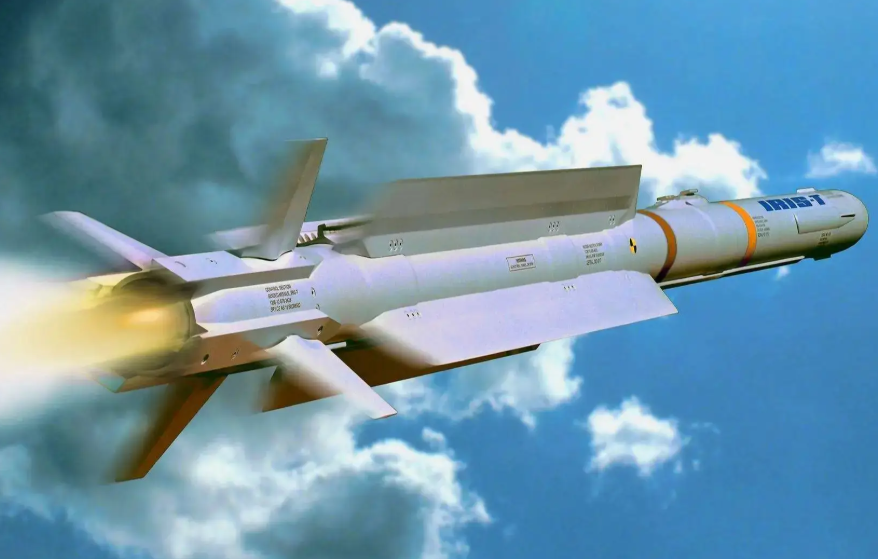色弱、15岁上大学、歼-20总师:杨伟的人生,每一步都在打破“不可能”。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走廊里,挂着一张有些褪色的老照片。1978年的西北工业大学校门口,15岁的杨伟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校服,背着帆布书包,站在“为人民服务”的校牌下,眼神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跟后来他在歼-20首飞现场攥紧拳头时一模一样。 谁能想到,这个差点因为色弱被航空系拒之门外的少年,会在四十多年后,让中国战机在全世界面前抬起头来。说起来,杨伟的航空路走得一点都不顺。 1978年恢复高考,他凭着数理化几乎满分的成绩闯进了顶尖高校的视野,可体检表上“色弱”两个字,让不少招生老师摇了头。 那时候人们觉得,搞航空的连颜色都分不清,还怎么看仪表盘、辨信号旗?就在他快要错失机会时,西工大飞机系主任罗时钧拍了桌子:“我当年也是色弱,照样跟着钱学森搞研究! 开不了飞机,咱们就造能让别人羡慕的飞机!”这位老教授可能没料到,自己这句带着点倔劲儿的话,不仅给中国留住了一个天才,更埋下了打破西方技术垄断的种子。 进了大学的杨伟,成了校园里的“异类”。同班同学里最大的都快三十了,他这个还没长开的少年,每天凌晨就翻墙进教室占座,晚上宿舍熄灯了,就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啃《空气动力学》。 有人打趣说他是“小老头”,他却指着书本上的公式回嘴:“等我搞明白这些,就能让飞机飞得更稳。” 这种近乎轴的认真,让他在研究生阶段就啃下了飞机紊流影响分析的硬骨头,22岁毕业时,手里已经攥着7篇核心期刊论文,其中一篇关于机翼设计的新思路,后来直接用到了歼-10的改进上。 1985年到成飞报到那天,杨伟背着一个装着换洗衣物的纸箱,直接冲进了飞控系统研究室。当时国内战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全靠进口,人家卖设备时还藏着掖着,核心数据根本不给。 有回外国专家来调试设备,故意把参数改乱,看着咱们的工程师急得满头汗,在旁边偷偷笑。 杨伟把这事儿看在眼里,回到办公室就把自己关了三天,出来时手里攥着一叠演算纸:“咱们自己搞,不信比他们差!” 他带着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连台像样计算机都没有的情况下,硬是用算盘加手摇计算器,搭出了国内第一个数字仿真系统。 半年后,当那台被他们叫做“铁鸟台”的模拟设备成功复现战机飞行姿态时,连见多识广的老厂长都红了眼:“这玩意儿,比进口的还灵!” 很多人觉得,杨伟能搞出歼-20,靠的是天赋。可跟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最厉害的不是算得快,而是敢想别人不敢想的。 就说歼-20的鸭翼设计吧,当年国际上都觉得这玩意儿会影响隐身性能,美国的F-22就特意避开了这种布局。 杨伟却带着团队在风洞里吹了上千次,愣是琢磨出“锯齿化处理”的法子,让鸭翼转动时产生的雷达反射信号降了一大半。 后来有外媒测算,歼-20的雷达能探测到的面积,比F-22小了近一半,这就意味着在空战中,咱们能先一步发现对方。 更绝的是内置弹舱,他硬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塞下了6枚导弹,射程比美国同类型号远了快一倍,用他的话说:“打架就得手里家伙够长,不然没等靠近就被人揍了。” 2011年1月11日那天,成都温江机场的天有点阴。当歼-20的验证机像一道黑色闪电冲上天际,做了个漂亮的“眼镜蛇机动”时,指挥塔台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盯着屏幕上的参数。 杨伟站在最前面,手指紧紧抠着栏杆,指节都发白了。直到飞机稳稳落地,试飞员李刚走下来冲他竖大拇指,他才发现自己手心全是汗。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在想啥,他说:“就觉得这二十年的熬,值了。” 这二十年里,他见过团队里的老工程师因为算错一个数据哭红了眼,也经历过关键部件试验失败时的沉默,最难的时候,连食堂大师傅都知道:“那个总加班的杨工,最爱吃加两勺辣椒的担担面。” 其实杨伟最了不起的,不是造出了一款先进战机,而是带活了一整个行业。以前咱们搞飞机设计,图纸画出来后,工人得一点点照着做,稍微改个零件,就得从头再来。 他来了之后,硬是把汽车厂的“流水线”概念搬了过来,搞出了“脉动生产线”。 现在成飞的总装车间里,300米长的生产线上,每隔三天就能下线一架歼-20,零件精度能控制在头发丝的五分之一那么细。 这背后,是他逼着大家搞的全三维数字化设计,以前画一张机翼图纸要三天,现在在电脑上拖拖拽拽,俩小时就能搞定,还能直接传给工厂的机床,一点都不走样。 有回外国同行来参观,摸着刚下线的机身蒙皮感叹:“你们这速度,比我们快了三倍都不止。”这些年,总有人说杨伟是“中国版马斯克”,可他听了总摇头。 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 从当年罗时钧教授力排众议录取他,到成飞老厂长把最硬的骨头交给一个毛头小子,再到团队里年轻人敢跟他拍桌子争论方案,这背后是一代代航空人攒下的底气。




![我可以证明“歼-20”是坠毁了,非常惨!我没拿稳电池都摔出来了[doge]烽火问鼎计](http://image.uczzd.cn/1393191938494143352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