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0年,李文忠交代完后事才去上朝。朱元璋看了他的奏折,怒骂道:“李文忠,你就不怕死吗?”李文忠说:“臣死不足惜,愿陛下多念及江山黎民。”这话一出口,大殿鸦雀无声,朱元璋脖颈青筋暴起。 金銮殿的梁柱仿佛都在这死寂里缩了缩。朱元璋死死盯着阶下那个身着绯红官袍的身影,这人是他亲外甥,是跟着他从濠州泥地里杀出来的开国勋贵,当年鄱阳湖大战,李文忠带着二十亲兵就敢冲陈友谅的中军帐,血浸透铠甲都没皱过眉头。可现在,这双手握过刀枪的手,递上来的奏折里写的全是“罢兵休养”“宽宥功臣”,字字都像软刀子,割着他刚坐稳的龙椅。 “念及江山黎民?”朱元璋突然笑了,笑声在空旷的大殿里撞出回声,听着比怒喝更让人发寒,“朕杀的是结党营私的逆贼,查的是贪赃枉法的蛀虫,这江山是朕一刀一枪拼出来的,难道要朕看着那些人把它蛀空才叫念及?”他把奏折往地上一摔,明黄的绸面在金砖上滑出刺耳的声响,“你李文忠,凭着这层亲戚关系,就敢指着朕的鼻子说教?” 李文忠缓缓跪下,额头抵着冰凉的地砖,声音却没低半分:“陛下忘了龙凤十二年的冬天吗?滁州城外,咱们三天没吃上热饭,是乡农给的半袋红薯才撑过去。那时陛下说,得了天下,要让百姓过安生日子。”他顿了顿,喉结滚了滚,“如今徐达将军在北平戍边,身上还带着九处箭伤;常遇春的儿子才十二岁,就承袭了父爵去守云南。这些人,哪个不是跟着陛下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这话像针,精准刺中了朱元璋最敏感的地方。他猛地一拍龙椅扶手,案上的玉圭都震得跳起来:“放肆!你是说朕杀功臣?胡惟庸结党谋逆,证据确凿,难道留着他颠覆大明?”殿外的日头正好移过窗棂,把朱元璋的影子投在地上,像头蓄势待发的猛虎。 站在班列里的李善长眼皮直跳,他悄悄拽了拽李文忠的袍角,却被对方甩开。李文忠抬起头,脸上溅到了奏折散开的纸屑,眼神亮得惊人:“胡惟庸该杀,但牵连上百官员,连马夫、厨子都没放过,这不是查案,是株连!臣府里的老仆,当年给陛下牵过马,昨天因为他远房表舅在胡府当差,就被锦衣卫拿了去。这样下去,人心惶惶,谁还敢为大明卖命?” 朱元璋的呼吸越来越粗重,手指关节捏得发白。他想起当年郭子兴猜忌自己,是李文忠的母亲,也就是他的亲姐姐,把最后一块干粮塞给了他;想起攻破南京那天,李文忠抱着他的腿哭,说姐姐要是能看到这一天就好了。可现在,这个外甥像变了个人,句句都在指责他治国太狠。 “朕看你是读书读傻了!”朱元璋的声音陡然拔高,“自古人主驭下,就得恩威并施!你当朕愿意杀人?这些功臣手握兵权,个个居功自傲,朕不敲打敲打,将来太子镇得住吗?”他忽然起身,龙袍扫过案几,带倒了一个青瓷笔洗,水溅在明黄的袍角上,像块深色的疤。 “太子仁厚,正需要这些元勋辅佐!”李文忠也急了,膝行两步,“陛下若把能臣都杀了,将来外有强敌,内有变故,谁来为大明披甲上阵?” 这话彻底点燃了朱元璋的怒火。他指着殿门,声音都在发颤:“滚!给朕滚回去!再敢多言,朕就抄了你的曹国公府!” 李文忠却没动,他从怀里掏出一份早就写好的遗表,双手举过头顶:“臣今日上奏,就没打算活着回去。这是臣的遗表,恳请陛下看完再处置臣。”表章上的字力透纸背,开头写着“臣闻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后面洋洋洒洒数千言,全是劝朱元璋止杀戮、重农桑的话。 朱元璋盯着那份遗表,突然觉得一阵疲惫。他想起姐姐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照顾好文忠”,那时这孩子才八岁,怯生生躲在母亲身后。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孩子长成了敢跟他硬碰硬的忠臣,可这忠臣的话,他怎么就听着这么刺耳? 殿外的风卷着落叶飘过丹陛,带来一丝秋凉。朱元璋沉默了许久,终于挥了挥手:“把他……押回府里,看管起来。”声音里没了刚才的暴怒,却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 李文忠被锦衣卫架着往外走时,回头看了一眼龙椅上的舅舅,那人背对着他,肩膀微微耸动。他忽然笑了,笑得眼角有泪——至少,陛下没当场杀他,这就还有希望。 可他没想到,这一禁足就是三个月。期间朱元璋没再召见他,却把那份遗表里提到的几件苛政悄悄改了:减免了江南三府的赋税,释放了被牵连的三百多户百姓。直到那年冬天,李文忠染了风寒,朱元璋夜里悄悄去了趟曹国公府,坐在床边看了他半宿,临走时丢下句话:“好好活着,朕还需要有人给朕提意见。” 只是那时的李文忠已经烧得糊涂,没听见这句话。他去世后,朱元璋罢朝三日,追封他为岐阳王,亲手写了祭文。只是祭文里没提那天金銮殿上的争执,只说“朕有天下,多赖尔力”。 后人读这段历史,总说李文忠是拿命谏言,可细想起来,这场君臣角力里,既有开国皇帝对权力的警惕,也有血浓于水的牵绊。朱元璋终究没杀李文忠,或许不是怕了他的奏折,而是怕午夜梦回,对不起姐姐那句“照顾好文忠”。



![恭喜檀健次新代言官宣啦。[鼓掌]](http://image.uczzd.cn/1614082391423610313.jpg?id=0)
![这个秦代石刻居然是真的[思考]看来传说中的昆仑山就在黄河源头[666]今年6](http://image.uczzd.cn/10570079295685155684.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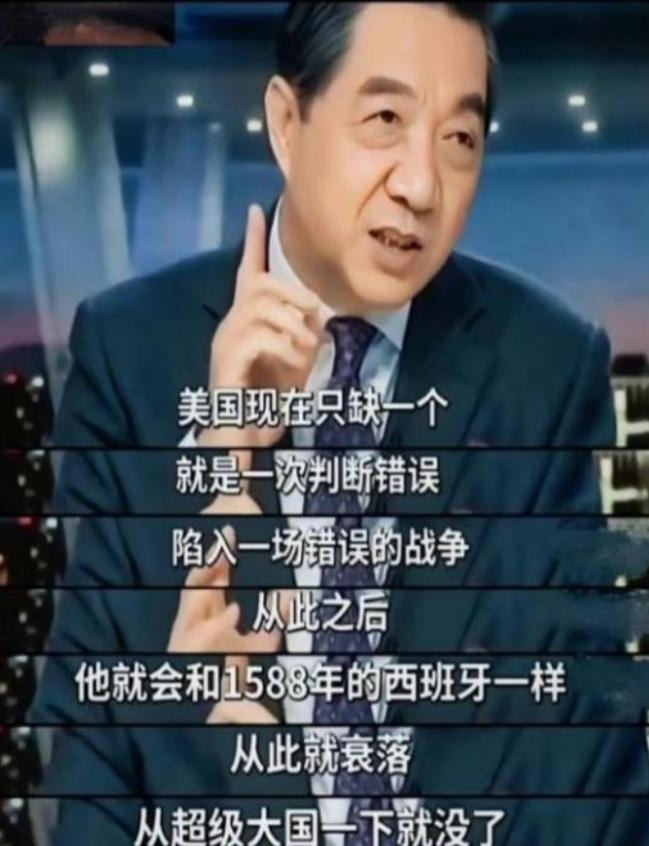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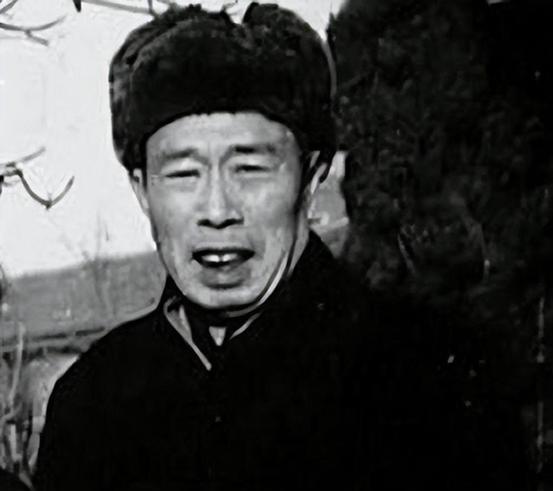

水嘟嘟
造什么谣都没必要瞎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