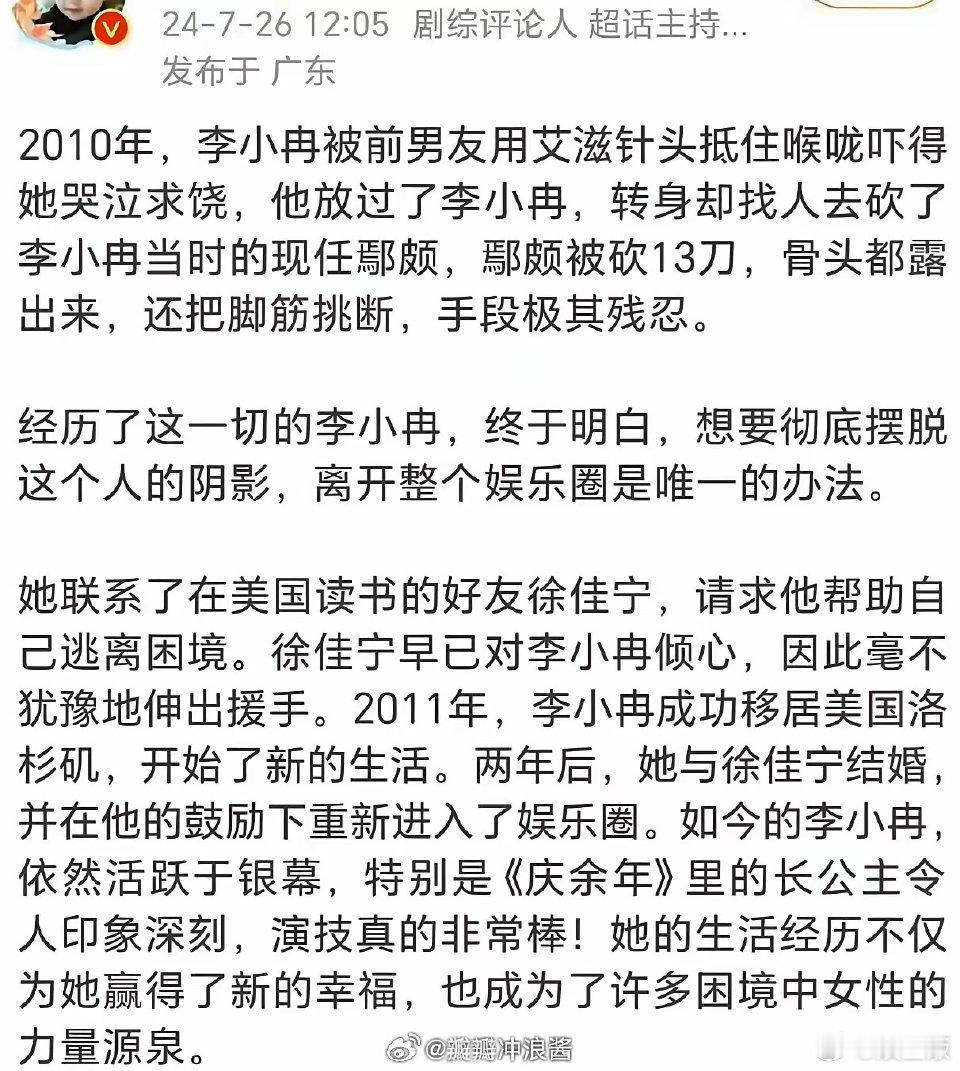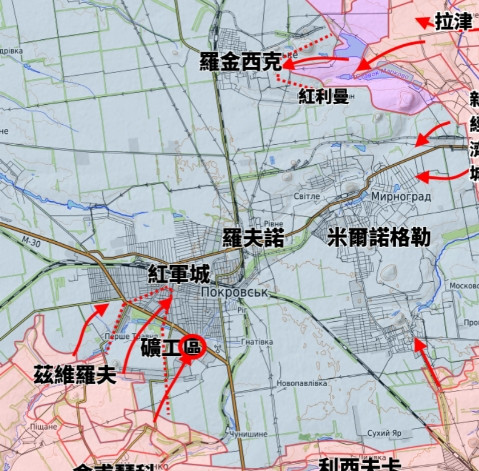1279年,陆秀夫背起8岁的小皇帝,问道:大势已去,陛下可愿与我跳海殉国?来保我大宋名节。小皇帝哭着回答道:朕也不愿苟活在这世上。随后二人便纵身一跃投入了茫茫大海中。 陆秀夫抱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这事儿到底算千古流芳的忠烈,还是把孩子当道具的愚忠?有人说他伟大,保全了汉人最后的风骨;有人骂他残忍,凭什么替一个孩子决定生死? 陆秀夫本来是个文官,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跟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是同年。这种人,天生是待在庙堂之上,喝着茶、写着奏折,讨论国家大事的。可时代没给他这个机会。 蒙古人的铁蹄踏碎临安的繁华,把十五岁的宋恭帝打包北上当了俘虏。一时间,朝廷里头的“精英”们,跑的跑,降的降。张世杰、陆秀夫这帮“头铁”的,硬是护着小皇子赵昰、赵昺,搞起了海上流亡政府。 小皇帝赵昰就是在这种惊恐和颠簸中一病不起,死了。当时所有人都快崩溃了,陆秀夫带头,率领群臣号啕大哭,硬是把心里的那股绝望给压了下去,然后扶立了更小的赵昺。 他不是天生的战士,但时局把他逼成了最后的顶梁柱。 等到退守崖山,其实已经是死局了。崖山,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但也是个绝地。张世杰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把上千艘战船用铁链锁在一起,想搞个“海上堡垒”。听着挺霸气,实际上是自绝后路。元军一来,一把火,加上切断淡水的来源,船上二十万军民(里头能打的也就一半),不攻自破。 当时他们已经没有陆地了,唯一的依靠就是这些船。锁起来,至少能给惶恐的军民一种“我们还在一起”的稳定感。这是一种心理战,可惜,面对绝对的实力差距和战术碾压,心理战脆弱得像张纸。 决战那天,也就是1279年3月19日,元军四面八方围上来。宋军的船阵瞬间被打乱,火光冲天,哭喊声、厮杀声混成一片。败局已定,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大宋最后一口气,要咽下去了。 这时候,镜头给到陆秀夫。 那个广为流传的对话——“陛下可愿与我跳海殉国?”“朕也不愿苟活!”——大概率是后人为了艺术效果加工的。真实的史料《宋史》里只是说,陆秀夫先是呵斥自己的妻子孩子跳海,然后换上朝服,跪拜小皇帝,说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 随后,他把国玺挂在身上,背起八岁的赵昺,纵身跳进了大海。 没有那么多悲壮的台词,只有一种冷静到可怕的决绝。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投降不好吗?至少能活命。元朝对宋朝宗室,表面上还算可以。你看那个被俘虏的宋恭帝,后来在元大都还娶了公主,虽然结局也不好,但至少多活了几十年。 但陆秀夫看到的是另一层。他看到的是襄阳城破后的屠戮,是元军铁蹄下无数百姓的流离失所。他更明白,一旦小皇帝投降,就意味着流亡朝廷的彻底终结。赵氏皇族将成为元朝宣示其“正统”的政治工具,大宋最后一丝精神象征,也将荡然无存。对于把“名节”看得比天还大的古代士大夫来说,那种“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所以,他选择了最惨烈的方式,为这个三百年的王朝,画上了一个血红色的句号。 更让人震撼的,是跟随他一同跳海的十万军民。史书记载,“后宫、诸臣、军民从死者十余万人。”第二天,海上浮尸遍野。 在那个“华夷之辨”深入骨髓的年代,“国”和“家”的存亡,就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 元军主帅张弘范,他也是个汉人。灭了南宋后,他得意洋洋地在崖山的石头上刻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一个汉人,灭了汉人的王朝,还生怕别人不知道。后来,有人悄悄地在这行字前面加了个“宋”字,变成了“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 这几年,随着国学热和历史科普的流行,关于崖山和陆秀夫的讨论,在抖音、B站上又火了一轮。很多年轻人用AI复原当时的场景,用沙盘推演战局,甚至为陆秀夫到底该不该抱着孩子跳海,吵得不可开交。 这恰恰说明,陆秀夫那一跳,跳出了历史,成了一个超越时空的文化符号。 他代表的是什么?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是一种在绝境中,选择用毁灭来捍卫尊严的刚烈。这种精神,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几百年后,明末的史可法坚守扬州,抗战时期的中国军人死守阵地,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陆秀夫的影子。 我们也要承认这种选择的局限性。它过于惨烈,代价巨大,甚至带着一丝对生命的漠视。它不应该被无条件地歌颂,更不能成为绑架他人的道德枷锁。 我们回望崖山,不是为了模仿那种死亡,而是为了理解那种精神。 理解在那个黑暗的时刻,有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守护一些他们认为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文明的延续,比如民族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