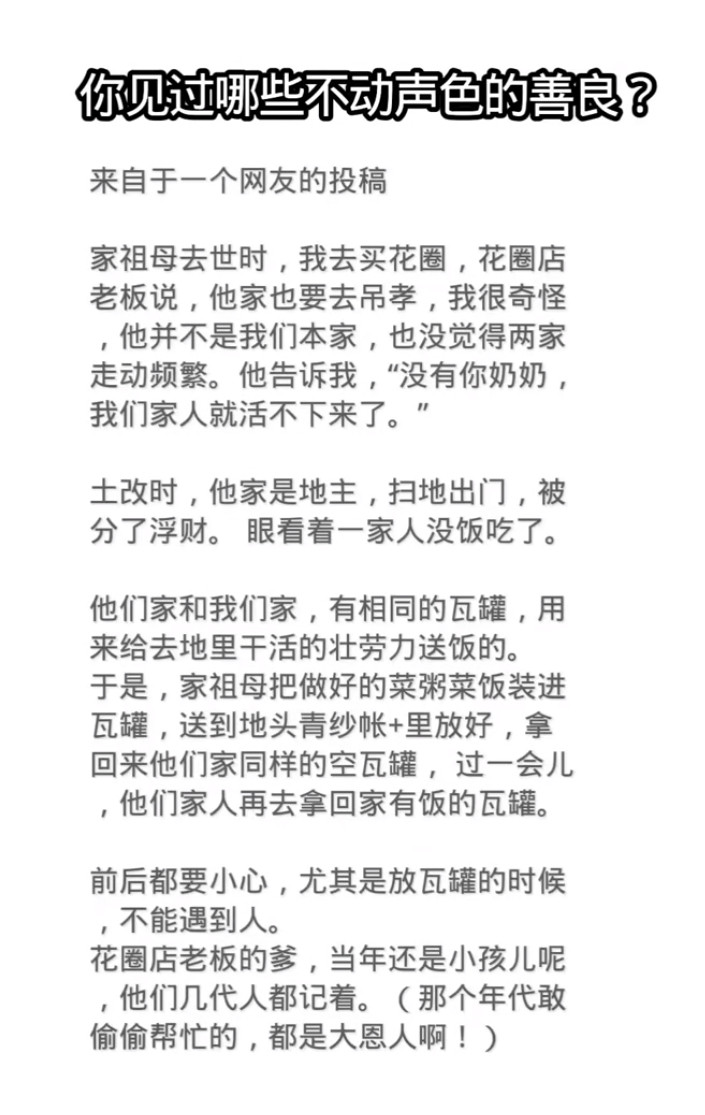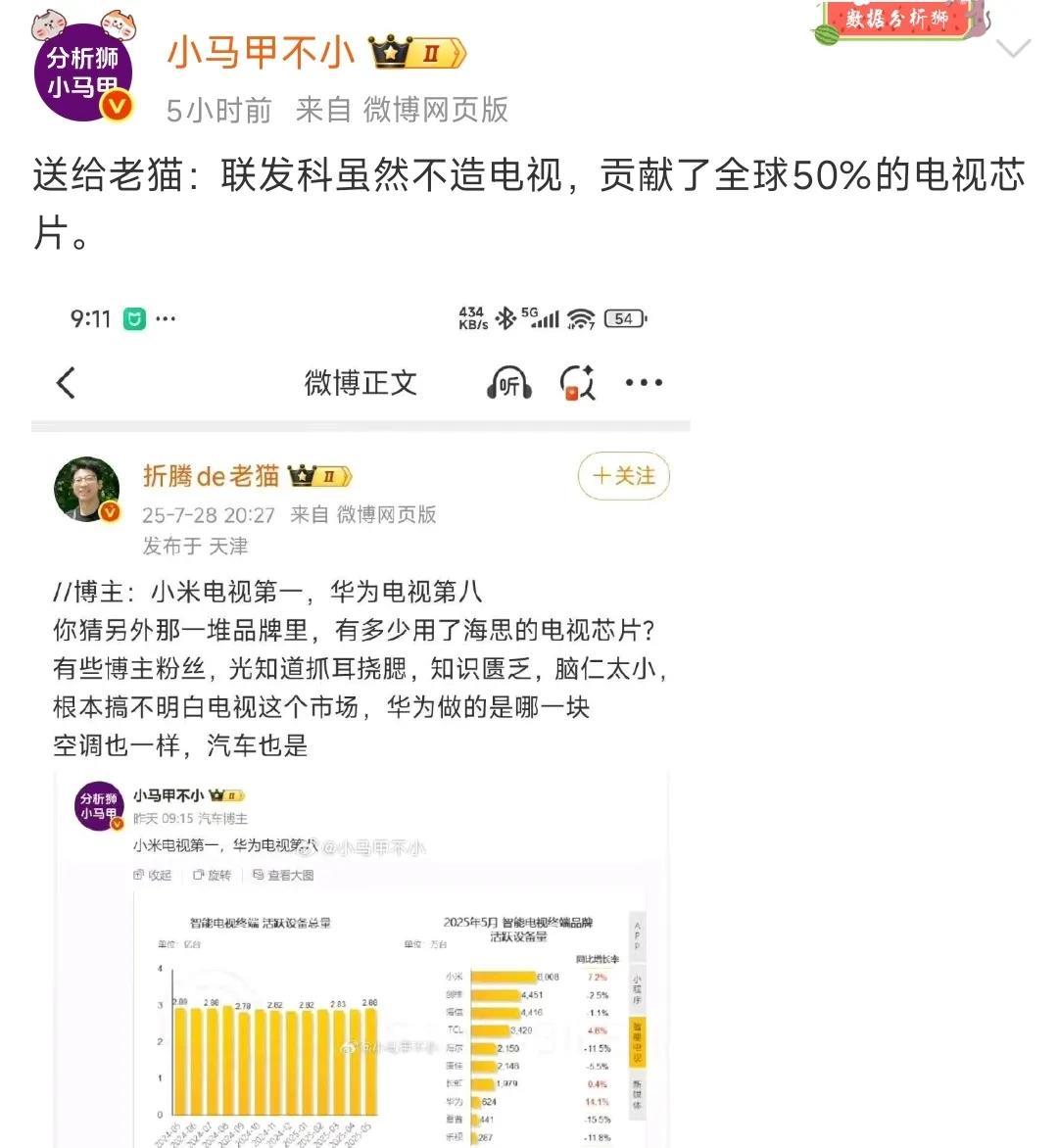1961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
包产到户和承包责任制的政策一经出台,便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随之而来的也有诸多非议。一些人认为,这种政策的关键在于“分而不是包”,他们觉得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将土地分配给个人单干,甚至认为这是倒退回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道路,甚至有人感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夜之间就退回了“解放前”。还有人心有余悸,表示宁愿慢慢发财,也不愿意冒险跌倒。 回顾当时毛主席为何反对包产到户,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深刻原因。包产到户虽然能够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带来了很多潜在的危机和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农业生产中集体化的优势,容易导致土地分散,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可能导致农田的荒废与浪费。毛主席担心,这种做法虽然看似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破坏农村的集体主义基础,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陷入“短期热闹,长期低效”的困境。 然而,进入1980年代,社会的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80年9月27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包产到户和承包责任制政策逐渐获得认可。文件指出,包产到户是为了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 且强调这一政策是在生产队领导下实施的,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并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因此,包产到户的风险已经得到了控制,且这一措施是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的。
1961年的春天,中国农村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关于农村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古老的生产方式上。当时,不少地方的干部群众提出,让农民分到自己的土地,实行包产到户,或许能够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更好的收成。 在这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中,支持包产到户的声音不在少数。他们的理由看似很有说服力:每个农民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样就能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热情。一些地方的实践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个别试点地区在实行包产到户后,确实出现了农业产量的短期提升。 然而,毛泽东主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他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纵观中国历史,包产到户确实由来已久。 追溯到先秦时期,我国就已经存在类似的生产方式。秦汉以后,这种小农经济形态更是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民虽然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贫困的面貌。相反,土地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社会的一大顽疾。 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由于缺乏资金、农具和技术支持,许多农民即使拥有土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更严重的是,这种生产方式往往导致土地不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使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历史上土地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分田到户的做法也并非首次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王莽在公元九年颁布了王田制,将全国土地统一更名为“王田”,明确规定不得买卖,并要求每家八口的农户拥有不超过800亩土地,超过部分需分配给其他农户或宗族。 对于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农民,国家给予补偿,标准为每个家庭100亩土地。这一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土地平均化政策,目的是缓解土地兼并现象和贫富差距,推动社会阶层的平衡。然而,王田制并未如期实现其理想,反而因制度的僵化和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农民反而被束缚在这个“王田”制度中,难以发挥其土地使用的最大效益。此外,贵族与地主的强烈反对,使得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未能在社会中得到广泛支持。 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重新成为重点。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的雄溪乡燎原社开始了生产责任制的试验,成为中国最早的包产到户的实践之一。随着实验的推广,包产到户的做法在一些地区得到了认可。然而,1956年11月,浙江省委出于对中央政策的考量,要求停止这一实验,因为该做法与当时的集体化政策产生了冲突。 1978年,贵州等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农村经济困境加剧,许多农民开始悄悄实行包产到户。贵州的农民在长期贫困与粮食不足的困境中,为了自救,不顾上级禁令,积极采取了这一方式。1979年,贵州省委第二书记池必卿深入农村调研时,发现不少农户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纷纷采取了这一变通方式。 1981年,贵州遭遇了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旱灾,但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农民们凭借更加灵活的生产管理方式,努力抗旱保产,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灾害造成的损失。通过这一事件,许多原本实行其他生产责任制的地区,纷纷转向包产到户。到年底,贵州省98.2%的生产队已经实施了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