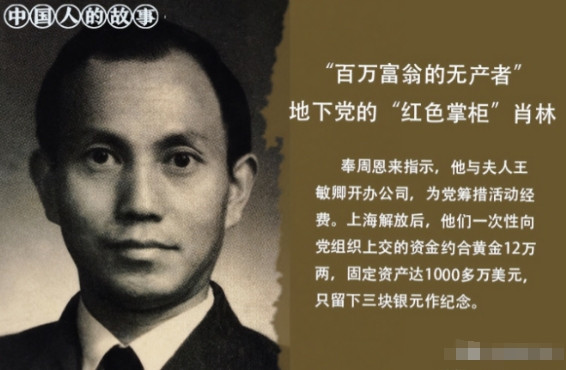1976年徐景贤进去后,在里面一直身体不好,他夫人葛蕴芳写信申述,于是徐景贤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保外就医,又于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权利。 1933年,徐景贤出生于上海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徐宗骏早年参与地下工作,后因不堪政治压力退出,选择在教育系统中安身,家庭氛围中既有对革命的热情,也有对现实的警惕,这种复杂的背景,为徐景贤的成长打下了双重底色,他从小耳濡目染,对政治有着天然的敏感与兴趣,青年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巨变之际,他选择投身学生运动,最终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一条不同于父亲的政治道路。 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后,徐景贤开始展现出出色的写作才华,他的文章常见于校内刊物,语言犀利,思路清晰,这种文笔与政治觉悟的结合,使他在毕业后迅速被分配至华东局机关工作,在那个讲求“笔杆子”的年代,他的能力极具竞争力,1957年反右运动初起,他迅速撰写批判文章,立场坚定,措辞激烈,赢得了上级的注意,这篇文章成为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张春桥由此发现了这个有才干、懂分寸的年轻人,将其调入市委写作小组。 在写作组的日子里,徐景贤如鱼得水,他不仅能准确把握政策精神,还能将其转化为鼓动性极强的宣传文字,他参与撰写的大量内部材料、对外文章,成为当时上海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在那个信息高度集中、舆论控制几乎全覆盖的年代,写作组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一些行政部门,徐景贤逐渐被视为“笔杆子中的骨干”,政治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起初,徐景贤并未贸然行动,而是保持一定的观望与谨慎,他显然意识到,这场运动可能远超以往的政治行动,但他也深知,不表态就意味着边缘化,当时,上海的权力结构剧烈震荡,原市委核心遭受猛烈冲击,徐景贤一度试图在旧体制与新风潮之间保持平衡,但很快他意识到,中立并不能自保,在张春桥的授意下,他选择倒向“造反派”一方,以强硬姿态参与批判陈丕显等人,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政治命运。 随着“一月风暴”的爆发,上海原有的组织架构被彻底打破,新的政治实体——上海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迅速建立,在这一过程中,徐景贤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不仅负责起草大量宣传材料,还参与组织批斗、整顿各级机关,他主持的《文汇报》成为“革命路线”的喉舌,刊载的社论、批判文章频频登上全国舆论高地,他的文风愈发尖锐,常常一篇文章便能改变某个干部的命运。 权力的集中让徐景贤在七十年代初登上上海市委书记之位,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市委书记的权力几乎无边,他住进干部宿舍最好的楼层,日常行程有专车接送,身边聚集着一批唯命是从的工作人员,对外,他是“革命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对内,他是上海宣传系统的总指挥,他在市内主持整风会议、清理队伍、重构组织体系,几乎事无巨细,但这份荣耀的背后,是对四人帮政治理念的全面依赖。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局逆转,令徐景贤措手不及,消息传出那一夜,他正在自家客厅观看新闻,得知张春桥等人被捕的画面时,他明白,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即将终结,几日后,他被带离市委大院,开始接受调查,此后,他被正式羁押,逐步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最终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 监狱生活对徐景贤而言,是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他从原本的权力中心跌入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环境,精神与肉体都遭受重创,狱中条件艰苦,饮食贫乏,医疗条件简陋,他的身体逐年恶化,患上多种慢性疾病,精神上的打击更为沉重,他曾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与抑郁状态,唯一的慰藉来自外界的书信——他的妻子葛蕴芳在多年中坚持不懈地通过信件与他保持联系,不断申请减刑与保外就医,她不为名,不为利,唯一的愿望,是让丈夫活着回来。 1992年6月,徐景贤因病获得保外就医,提前三年离开监狱,当他走出高墙时,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他搬入中山西路一处老旧阁楼,与家人共居三十平米的狭小空间,家中八口人挤在逼仄的屋檐下,生活开销主要靠街道发放的每月三百元生活补助,连基本的医疗费用都需依赖女儿接济,昔日的市委书记,如今成了街道档案中的普通低保户。 1995年,他刑满释放,三年后恢复政治权利,然而,他从未真正复出,也未参与任何公开活动,他的生活逐渐归于平静,每日看看报纸,偶尔在小区中踱步,社区干部回忆,他每季度需提交思想汇报,文字中常见对过往行为的反思,但他从不主动谈及那段历史,他成了弄堂口寂静的背影,邻居多对他报以冷淡态度,很少有人愿意靠近这个“曾经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