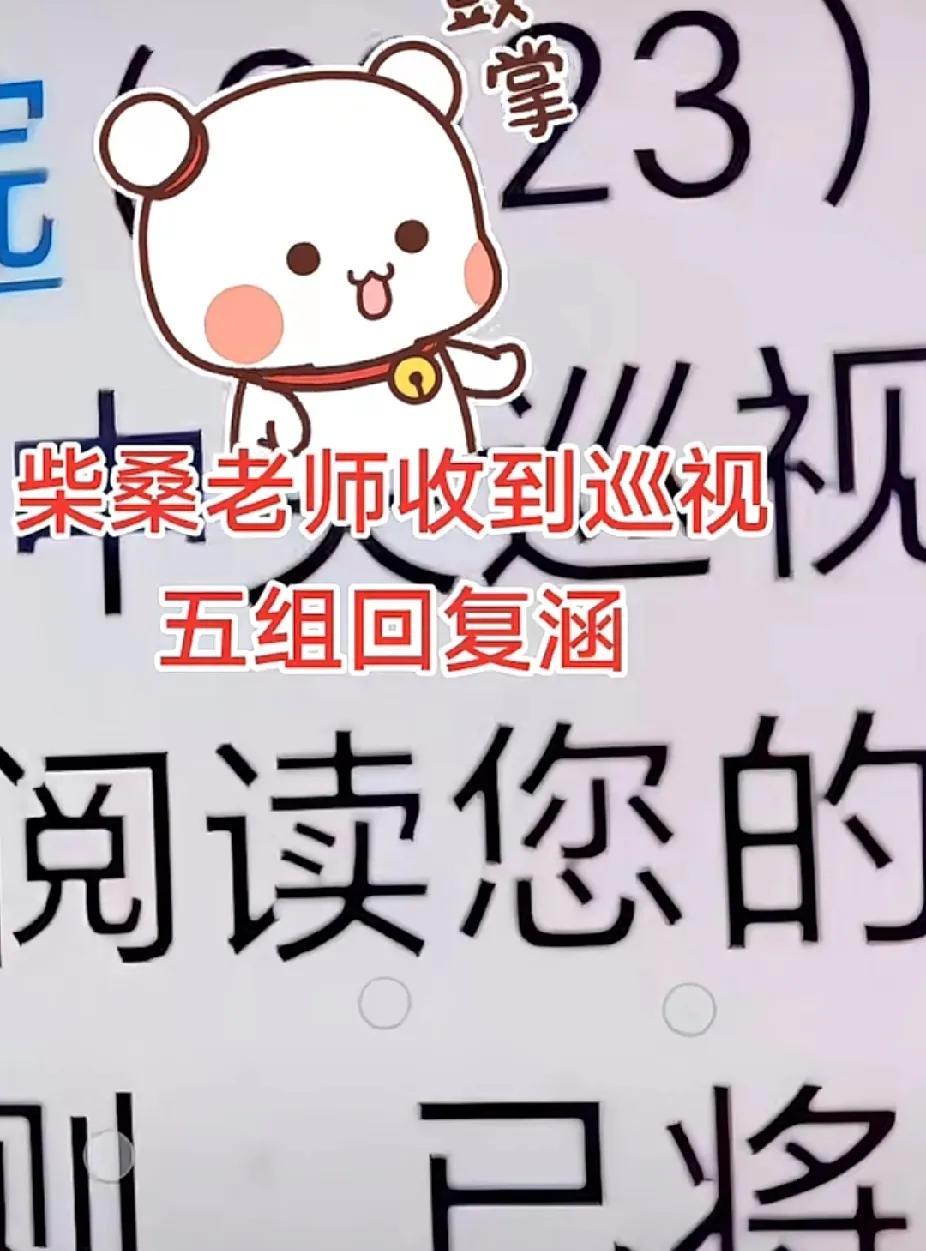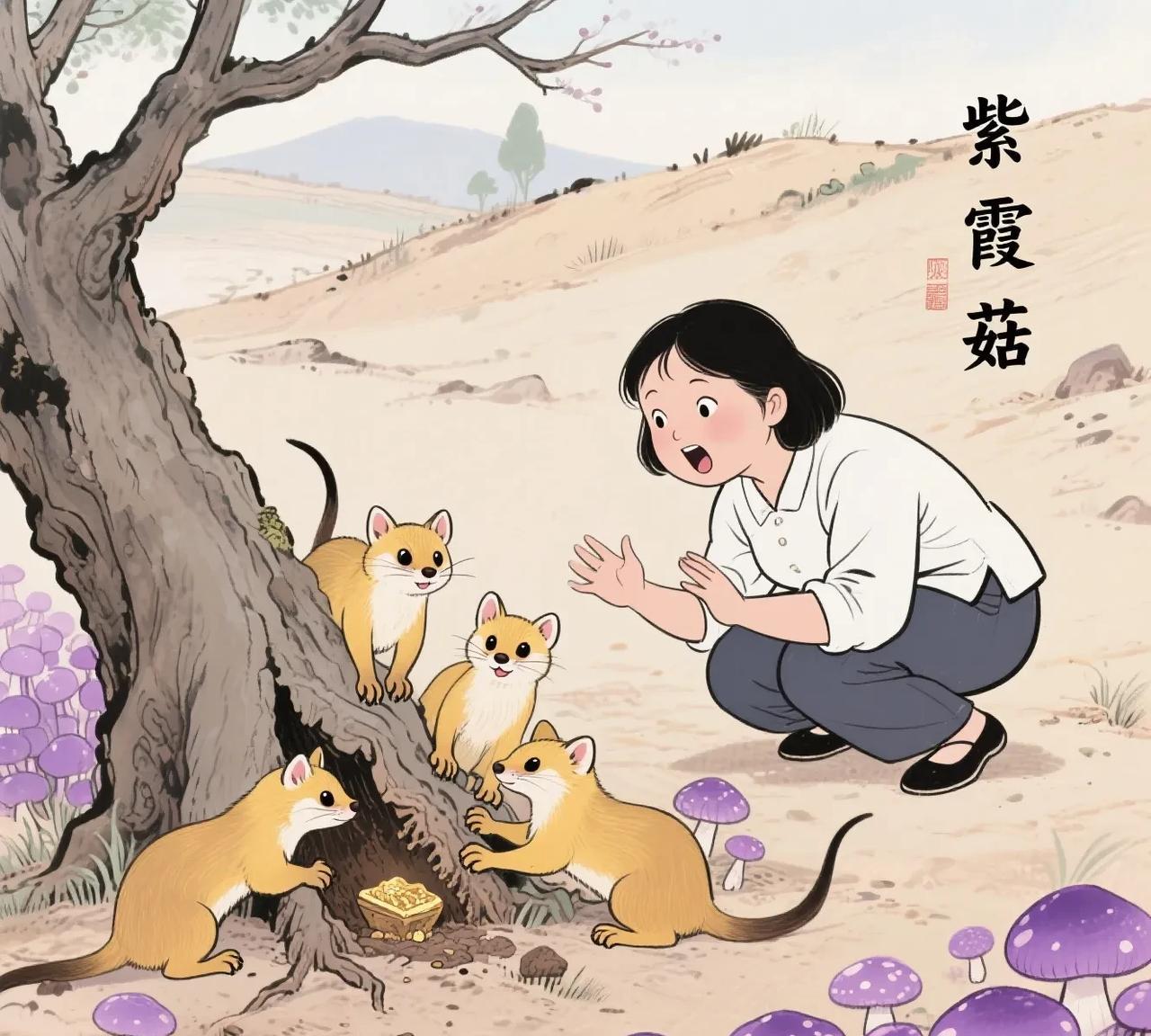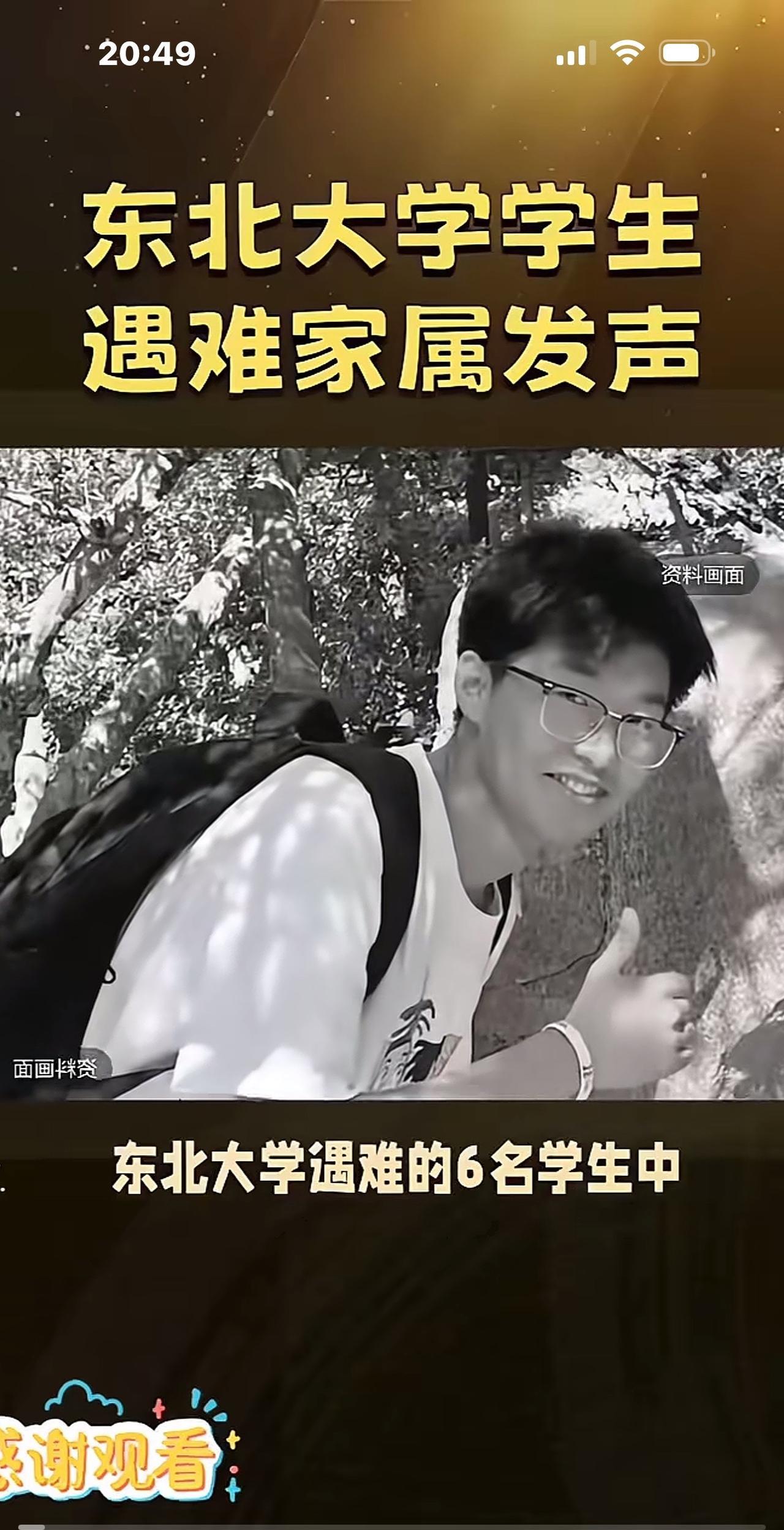明末崇祯十年,福建商人徐之璧在湖湘一带贩药,突遭张献忠之乱,被洗劫一空。他逃进荆南山中,却迷失了方向。 山里的雾气像浸了水的棉絮,把日头遮得严严实实。徐之璧攥着怀里最后半块干硬的麦饼,脚下的碎石子硌得草鞋直打滑。他原本挑着两箱上好的当归和天麻,打算去武昌府换些银子,谁料张献忠的队伍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眨眼间就把商队冲散了。现在别说药材,连贴身带的罗盘都在奔逃时弄丢了,只剩下这身被荆棘划破的粗布短打。 “咕噜噜——”肚子不合时宜地叫起来。徐之璧靠着一棵老樟树坐下,树皮上的青苔蹭得他后背发凉。他想起三年前离开泉州时,妻子把绣着牡丹的荷包塞进他行囊,说“药材是救人的,你走南闯北,也要护好自个儿”。那时江南的稻子刚黄,码头的船工喊着号子装货,哪想到如今会困在这荒山里,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从灌木丛里传来。徐之璧猛地站起身,抄起手边一根粗树枝——这年月,山里的野兽和乱兵一样吓人。可钻出来的不是豺狼,是个背着竹篓的少年,灰头土脸的,手里还攥着株带着泥土的草药。 “你是……”徐之璧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少年往后缩了缩,竹篓里的野果滚出来两个。“俺叫狗剩,家住山那边的清溪村。”他打量着徐之璧,“你是外乡人?” 徐之璧松了口气,把树枝扔在地上。“福建来的,做药材生意,遇上兵祸迷了路。” 狗剩的眼睛亮了亮,指着竹篓里的草药说:“俺认识这个,俺爹是村里的郎中,说这叫石菖蒲,能治头疼。”他蹲下身捡起野果,用衣角擦了擦递过来,“吃吧,山里的八月炸,甜着呢。” 果子的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甜丝丝的,带着股山野的清香。徐之璧咬了一大口,忽然看见少年篓子里有株叶片卷曲的植物,看着眼熟。“这是……”他伸手轻轻拨了拨,“这是七叶一枝花?” 狗剩点点头:“俺爹说这东西金贵,能治蛇咬伤,就是不好找。” 徐之璧的心猛地一跳。他做了十年药商,一眼就看出这株七叶一枝花长了至少五年,根茎粗壮,是难得的上品。他想起刚才路过一片潮湿的山坳,那里的腐殖土最适合这种药材生长。“你爹在哪儿?”他抓住少年的胳膊,声音都有些发颤。 清溪村藏在山坳深处,几十户人家的土坯房围着棵老槐树。狗剩的爹正坐在门槛上给村民包扎伤口,见了徐之璧,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听狗剩说明白来龙去脉,老郎中才叹了口气:“兵荒马乱的,能活着就不易。” 原来村里前两天遭了山匪,好几个壮年汉子被打伤了,存的草药也用得差不多了。徐之璧看着屋檐下晒着的半干草药,忽然想起自己脑子里记的那些药方。他指着墙上挂着的草药图谱,跟老郎中说:“这独活和苍术配伍,治风湿痹痛比单用有效。还有那边晒的艾叶,用酒炒过再敷,跌打损伤好得快。” 老郎中眼睛越睁越大,拉着徐之璧往屋里走。桌上的陶碗里盛着糙米粥,徐之璧却顾不上喝,借着昏黄的油灯,把自己走南闯北记下的药方一一讲出来。哪些草药能在溪边采到,哪种树皮能代替紧缺的杜仲,他说得头头是道,连狗剩都搬着小板凳听得入了迷。 接下来的日子,徐之璧就在村里住了下来。他带着村民去山里认药材,教他们炮制的法子,还把自己防身用的短刀磨利了,帮着村里防备野兽和散兵。有次遇上山洪冲毁了引水渠,他想起家乡泉州的水圳样式,领着大伙在山腰挖了条导流沟,保住了半亩快要成熟的玉米。 秋末的时候,徐之璧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村民们把晒好的药材打包。老郎中把一包用油纸裹好的天麻塞进他手里:“去汉口的路通了,带着这个走吧。村里帮你凑了些盘缠,够你回福建了。” 徐之璧望着远处翻涌的云海,忽然笑了。他把天麻放回桌上,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他用零碎竹片做的药碾子。“俺不走了。”他挠了挠头,“这山里的药材好,村民们心善,俺留着教大伙种药,比走南闯北强。” 狗剩在一旁蹦起来:“俺就知道徐大叔舍不得走!” 后来,荆南山里多了个背着药篓的福建人。他教村民们在向阳的坡地种当归,在背阴的石缝里找黄精,还把泉州的草药嫁接法子传到了山里。有人说他傻,放着安稳的生意不做,偏要在这穷山僻壤耗着。徐之璧只是笑笑,他记得老郎中说过,药材是救人的,在哪儿救不是救呢? 春去秋来,当年被战火蹂躏的土地慢慢长出新绿。清溪村的药材越种越好,连外乡的药商都循着名声找过来。人们说起那个福建来的药商,总会提到他常说的一句话:路走错了不怕,只要心里的方向没错,总能走到亮堂地方去。 (出自民间故事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