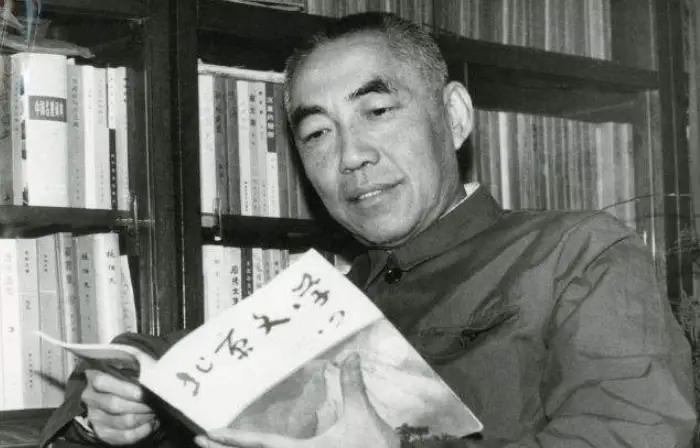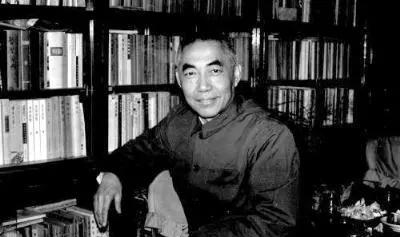面对各种对浩然的批判,雷达教授说:浩然的创作从来不是 "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著作",小说中的 "东山坞" 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村庄,而是浩然用文学想象搭建的精神共同体:马老四捧起黄土的热泪里,既有贫苦农民获得土地的真实情感,也融入了作家对 "翻身" 的价值认同;高大泉的坚韧不拔,既是特定时代对英雄的召唤,也暗藏着浩然对 "穷人主心骨" 的理想化寄托。这种真实,是情感的真实、体验的真实,而非统计学意义上的真实! 莫言笔下的乡土带着原始的生命力与荒诞感,那是他对农耕文明的解构式回望;而浩然笔下的农村,始终跳动着 "集体主义" 的脉搏,那是他亲历的 "新社会" 图景。二者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是不同生命体验催生的不同文学真实 —— 就像不能要求杜甫写出李白的豪放,我们也无法强求浩然突破他的时代视野与生命底色。 浩然对 "党是救星" 的坚信,绝非空洞的表态,而是刻进生命的记忆。幼年父母双亡、与姐姐相依为命的苦难,党和政府提供的救济粮、安稳的工作机会,这些具体的温暖构成了他认知世界的起点。在十四岁那个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革命不仅是抽象的理念,更是让他 "不至于流落街头" 的现实力量。这种经历使他笔下的 "党的形象" 始终带着温度:不是教科书里的概念,而是说书人口中的 "正义英雄",是能为马老四们 "主持公道" 的具体存在。 这种个人体验的投射,让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 "情感真实"。《艳阳天》里萧长春对集体的执着,《金光大道》中高大泉对互助组的坚守,背后都藏着浩然对 "安稳生活" 的珍视 —— 那是从饥饿中走过来的人,对 "不饿肚子" 的集体保障最朴素的赞美。当他描写农民们在打谷场上唱歌的场景时,文字里的热乎气儿,与他少年时在农会大院里感受到的温暖一脉相承。这种真实,或许不符合后世的理性审视,却无比贴近他自身的生命感受。 2008 年浩然的离去,之所以被视作 "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正因为他的作品凝结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基因:从延安文学延续而来的 "深入生活、表现工农" 的创作路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集体主义叙事,以及作家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创作姿态。这种文学范式或许有其局限,但它记录了一代作家对 "新社会" 的真诚想象,也保存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集体情感记忆。 重审浩然小说的真实性,终究要回到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期待文学提供什么?如果期待的是历史的全景式记录,那史书或许更胜任;但如果承认文学的使命包括保存时代的情感温度、记录个体与时代的精神联结,那么浩然的作品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他笔下的 "真实",是一个被时代塑造又真诚拥抱时代的作家,用文字为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价值认同立下的纪念碑 —— 或许不完美,却足够独特,足够成为我们回望一个文学时代的重要坐标 回想1994年夏,京华出版社再版了《金光大道》并一次出齐四卷,这一举措在当时的文坛犹如投入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轩然大波。文学界仿佛一下子被激活了,各方声音此起彼伏,争论不休。 在这场争论中,支持者虽然存在,但他们的声音相对显得较为微弱。更多的人对《金光大道》的再版持有恶感。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部作品的前两部曾受到青睐,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一种文学标识。作品从主题上看,似乎只是在生硬地演绎当时的理念;人物塑造也趋于模式化,成为了时代的代表;情节结构同样是为了迎合某种宣传而构建,缺乏文学作品应有的生动与鲜活。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使得《金光大道》在文学界的处境颇为尴尬。 然而,当我们抛开那些先入为主的评判,以一种纯粹的文学欣赏视角去审视这部作品时,会发现其中不乏闪光点。就像在这样一部被普遍认为是“图解政治”的作品中,竟然有着许多田园诗般的景物描写,这着实让人感到意外。 比如那一段对老槐树和周边景物的描写:“枝杈繁荣的老槐树,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像花生果一样的槐豆豆。成熟了的向日葵,像一根根竹杆子挑起的一顶顶黄色锦缎的帽子,伸出高高的院墙。墙头上,爬着豆秧。紫色的花朵开得正旺盛,垂着玻璃片似的豆荚。那中间,还有小磨盘似的窝瓜,如同涂了朱漆,上了油彩,又好像穿着红兜肚的胖娃娃,仰卧在那儿晒太阳。” 读着这段文字,仿佛眼前真的展开了一幅秋日丰收美景图。作者对色彩的把握非常精妙,槐豆豆的朴实、向日葵的金黄、豆秧花的紫色、窝瓜的红润,各种色彩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而且,比喻的运用更是恰到好处,将槐豆豆比作花生果,把向日葵比作黄色锦缎帽子,窝瓜比作胖娃娃,这些形象的比喻让景物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充满了生机与童趣,让人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美好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