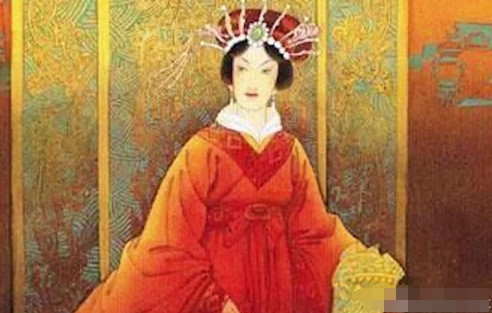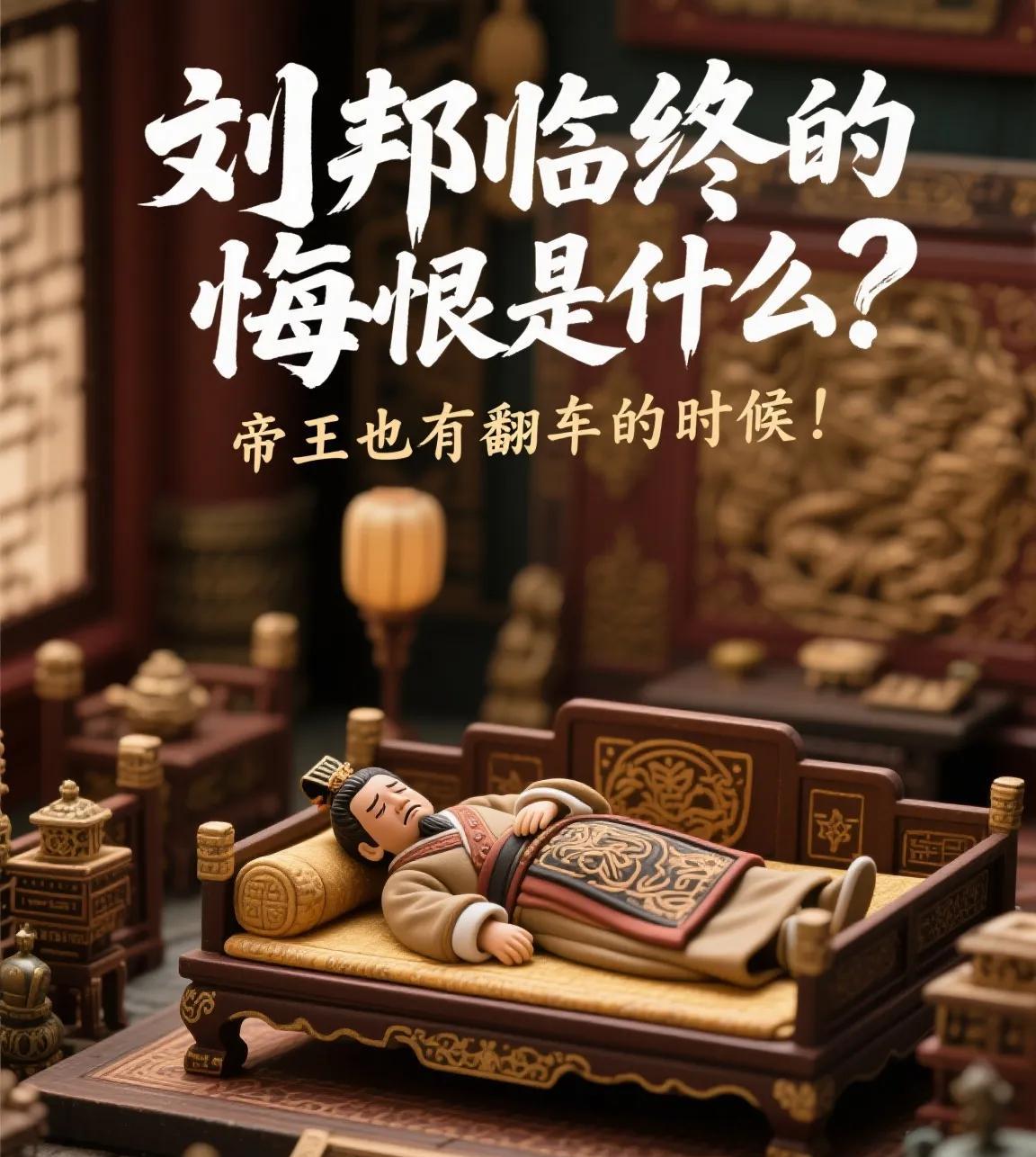公元前472年,勾践赐死文种,文种临死质问:“我帮你灭了吴国,你这就卸磨杀驴?” 鸱夷子皮(也就是范蠡)当年泛舟五湖前,曾托人给文种捎过一封信。信里说得明白,“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劝他早点离开勾践。那会儿文种正捧着越国丞相的印绶,看着朝堂上黑压压一片臣服的脑袋,只当是老友漂泊多年的过虑。他哪里会想到,不过三年光景,那杯盛着鸩酒的玉爵,会由勾践最信任的内侍端到自己面前。 殿外的桂树还是当年他亲手栽下的,如今枝繁叶茂,细碎的花瓣落了一地,像极了吴宫破城那日飘的雪。文种握着爵的手指泛白,抬头时正撞见勾践藏在冕旒后的眼睛。那双眼睛曾在会稽山的石室里闪烁着隐忍的光,也在姑苏台的庆功宴上漾着得意的笑,可此刻只剩下一片深不见底的冷。 “灭吴?”勾践忽然笑了,笑声撞在青铜编钟上,碎成一片刺耳的响,“先生怕是忘了,寡人当年在石室里尝夫差粪便的时候,先生正在越国清点粮草。”这话像淬了毒的匕首,精准地剜在文种最在意的地方。他确实没陪勾践去吴国为质,不是不敢,是勾践临行前攥着他的手说,越国的根基不能塌,你得留下。 文种想反驳,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他想起夫差赐死伍子胥时,那个白发老人也是这样睁着眼睛,直到最后一刻都不肯闭上。当时他还在心里冷笑,说伍子胥刚烈过甚,不懂为臣之道。如今才明白,有些时候,不是懂不懂的问题,是容不容的问题。 内侍在旁边低声催促,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不耐烦。文种看着眼前这张年轻的脸,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勾践还是个毛躁的少年,跟着他读《孙子兵法》,会因为解不出阵法而急得摔竹简。那时候的少年眼里有光,会喊他“文先生”,会在打赢一场小仗后,偷偷塞给他一块烤熟的鹿肉。 “大王可知,”文种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像风中残烛,“臣有七策灭吴,只用了三策,剩下的四策……” “不必说了。”勾践打断他的话,指尖在案几上轻轻敲击着,节奏与当年在吴宫为夫差牵马时的步伐重合,“先生的智谋,寡人领教过了。可这天下,容不下两个能颠覆乾坤的人。” 玉爵最终还是碰到了唇边,苦涩的液体滑入喉咙时,文种忽然笑了。他想起范蠡临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勾践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以前总觉得是老友看不透帝王心,现在才懂,不是看不透,是看得太透,才舍得转身。 殿门在身后缓缓关上,文种倒在冰凉的地砖上,视线渐渐模糊。他最后看到的,是窗外那棵桂树的影子,像极了他初见勾践时,少年人插在发髻上的那支桂枝。 参考书籍:《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吴越春秋》《左传·哀公二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