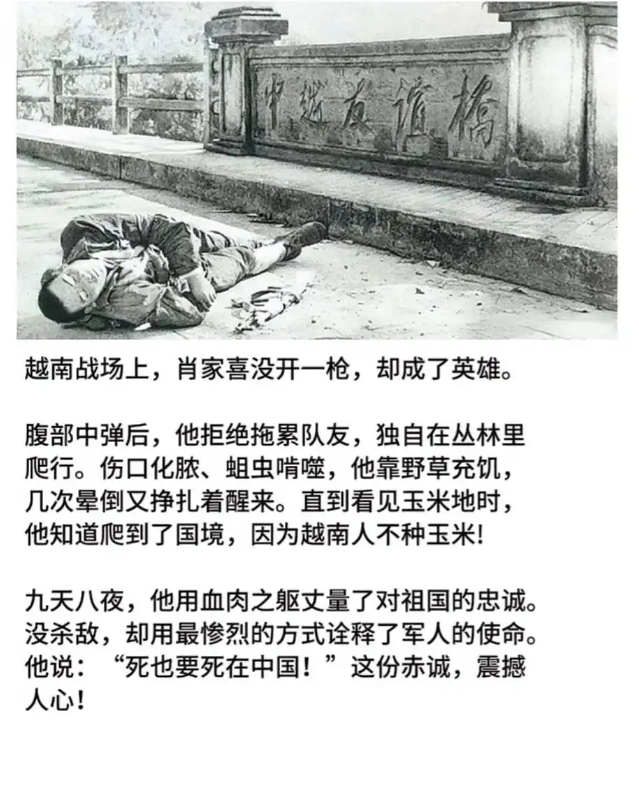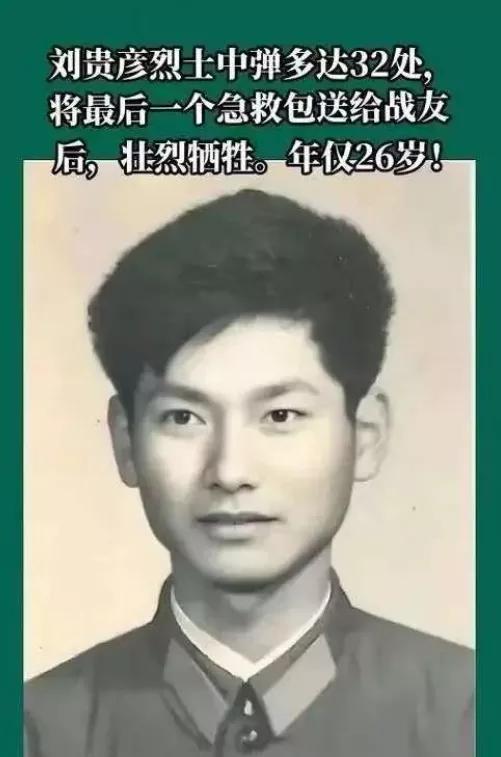1985年,老山战场上,20岁小战士身受重伤,为保住阵地,他独自坚守战位11个小时,在敌军即将攻上哨位时,他利用报话机高呼:“向我开炮!” 1985年7月19日,边境的无名高地上,太阳刚露头,敌军的炮弹就铺天盖地砸过来,碎石子混着滚烫的气浪往脖子里钻。 韦昌进缩在6号哨位的猫耳洞里,这是全排最关键的位置,丢了它,敌人就能顺着山沟撕开我军的防线。 那时候六连还没什么名气,在团里就是个“小字辈”,上战场前,领导本来没打算把他们放在一线,可全连战士不答应。 训练场上,大家比着劲儿地练匍匐、练瞄准,晚上就着煤油灯写请战书,最后全连三十多号人咬破手指,在红布上摁满血手印,上面就八个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韦昌进把这八个字抄在日记本上,申请守最险的6号哨位时,他跟连长说:“我爷爷讲,共产党给了咱们好日子,现在该咱们拼命了。” 敌军上来的架势真吓人,两个营带着一个连,黑压压的一片往山上涌,机枪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炮弹炸起的土块把人埋了半截。 韦昌进眯着眼数,一次、两次……敌人像疯了似的往上冲,突然一阵剧痛,他感觉左脸像是被烙铁烫了一下,伸手一摸,黏糊糊的,居然是自己的眼球掉出来了。 他咬着牙把眼球塞回眼眶,用急救包往头上一缠,血顺着下巴滴在报话机上。 这时候身边的苗挺龙倒下了,胸口一个血窟窿;旁边的战友想爬过去拖他,刚探身就被打中了肩膀。 哨位上能喘气的越来越少,韦昌进捂着右胸的伤口,感觉力气正从身体里往外跑,他抓起报话机,对着麦克风喊:“向我开炮!为了祖国,向我开炮!” 声音嘶哑得不像他自己,他知道炮兵需要坐标,现在自己就是最好的坐标,只要能把敌人打下去,炸到自己也值。 炮群呼啸而来的时候,他趴在地上数着炸点,一轮齐射,前沿的敌人倒下一片;又一轮,后续的进攻梯队被拦在半山腰。 他就这么喊一阵,歇一阵,直到第八次反扑被打下去,阵地上总算安静了些,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裤腿都被血浸透了,浑身能动的地方没几处,意识像被水浸泡的纸,慢慢沉下去。 后来听战友说,是几个幸存的战友轮流把他背下来的,20多公里的山路,全是石头子,背着他的战士换了一个又一个,每个人的军装都被他的血染红了。 团领导在电话里吼:“就是抬,也要把韦昌进抬到医院!”从团救护所到师医院,再转到军医院,他像在梦里飘了好久,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天花板上的输液瓶。 同病房的战友递过来一张纸,是连队党支部的批复,同意他入党,韦昌进这才想起,昏迷前他拉着排长的手说:“要是我不行了,就追我当党员吧。” 没想到支部当天就研究了,还把批复加急送到了医院,他让战友扶着坐起来,用没受伤的右手在入党志愿书上签字,笔尖抖得厉害,每个笔画都像刻在石头上。 养伤的时候,几个幸存的战友来看他,有人提议:“咱们把7月19日当成共同的生日吧,那天咱们都是从阎王爷手里逃回来的。” 韦昌进点点头,他还有个藏在心里的生日,爷爷说他刚出生时,母亲难产,公社医院治不了,是镇江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冒着零下好几度的严寒,背着保温箱跑了几十里路赶来。 他在保温箱里待了七天,医生说再晚一步就没救了。“党给了你两次命,”爷爷总跟他讲,“这辈子都得记着。” 后来他去北京领奖,站在人民大会堂里,胸前的一等功奖章沉甸甸的,可他总想起6号哨位上那些永远不会说话的战友。 吴东梅牺牲时才19岁,口袋里还揣着给家里写了一半的信;张泽群是机枪手,最后时刻抱着机枪滚向敌人,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 “我凭什么活着戴奖章?”他在日记里写,“这些荣誉是替牺牲的战友领的,往后得活出两个人的分量。” 从那以后,“坚守”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当排长时,他带的兵军事考核全团第一;做政委时,他跑遍了辖区所有哨所,给战士们讲6号哨位的故事。 现在他左眼装了义眼,看东西得偏着头,但只要说起当年的事,眼神亮得吓人。 四十多年过去了,6号哨位上的弹坑早被雨水冲平,长出了青草,但韦昌进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冲不掉。 就像爷爷说的那份恩情,就像战友们用命换来的安宁,就像刻在骨子里的那句“向我开炮”,这些东西,比军功章更重,比生命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