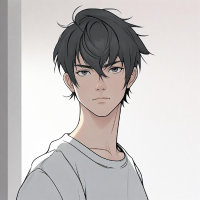1956年,傅作义几次请求毛主席释放陈长捷,也几次去功德林探望他,然而陈长捷每次见了傅作义都是怒目而视,“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初,天津城破,陈长捷被俘,傅作义和平起义的消息随后传来,从那一刻起,陈长捷便认定自己上了当,在他心里,这不仅是一场军事失败,更是一段长久信任的崩塌,从保定军校同窗,到并肩作战的上下级,再到天各一方的战犯与部长,他们之间的关系,因这场战役彻底改变。 陈长捷原是傅作义一手提拔上来的,1947年底,傅作义力荐他出任天津警备司令,那时的天津,是华北防线的重镇,战略地位极高,陈长捷接任后,投入极大精力整顿防御工事,调兵遣将,誓要守住这座城市,他的努力得到认可,连蒋介石视察后都大加赞赏,称若各地守将皆如陈长捷,局势未必不可挽回,从战术部署到士兵训练,他事事亲力亲为,城防体系也日趋完善,天津,在当时看来,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然而,战局的发展远比预料迅猛,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完成对天津的合围,胜势如潮,他们试图通过劝降信促成和平解放,但遭到陈长捷拒绝,他曾坚定表示,军人不能轻易放下武器,他始终认为,守土是职责,投降是耻辱,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傅作义身上,希望能得到明确的战略支持。 陈长捷多次向傅作义通报天津局势,希望得到具体指示,傅作义的回复始终没有实质内容,只是模糊地表示“坚守便有办法”,在陈长捷看来,这是承诺,是有后援的信号,可他并不知道,傅作义此时正秘密与中共谈判北平的和平起义事宜,因为谈判尚未公开,傅作义无法也不敢提前透露实情,他担心一旦走漏风声,北平的和平方案便会前功尽弃,也因此,他对陈长捷的回信没有正面回应,更没有明确下令其撤退或投降。 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动总攻,炮火倾城,持续近三十小时,陈长捷躲在地下指挥部中,调度兵力,试图稳住阵脚,然而面对数倍于己的兵力和密集炮火,天津防线很快失守,指挥部被攻破,陈长捷被俘,他没有想到,自己拼尽全力守城的同时,傅作义已经准备将北平无条件交出,几天后,和平起义的消息传来,他愈发觉得自己成了牺牲品。 从那以后,陈长捷被关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改造生活,每日学习、写思想汇报、下地劳动,生活枯燥但不松懈,他原本是个文质彬彬的将军,战时英勇,作风正派,被称为抗战常胜将军,可在功德林,他只是一名需要接受改造的战犯,身处高墙之内,他常常陷入对往事的反思,而其中最让他耿耿于怀的,始终是天津一战,以及傅作义在关键时刻的沉默。 相比之下,傅作义的处境要好得多,北平和平起义后,他在新政府中担任水利部长,频繁出席会议,规划治理河流项目,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一员,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老部下,在得知陈长捷的近况后,他曾多次向中央请求宽大处理,甚至在政协会议上,用“恳求”这样的词语表达希望特赦表现良好的战犯,他的言辞恳切,态度真诚,而这一切,陈长捷并不知情。 傅作义也曾亲自去功德林探望陈长捷,每次去,他都带着点心和水果,想缓和紧张的气氛,但陈长捷总是冷眼相待,有时甚至故意转过身不与他交谈,他的沉默中透着愤怒,他无法释怀,也不愿接受解释,在他看来,傅作义的成功,是用天津守军的失败换来的,他失去了军衔、尊严,甚至自由,而傅作义却成了和平名将,这种强烈的落差让他难以接受。 在功德林的生活并非全无变化,随着时间推移,改造的氛围逐渐深入,陈长捷开始读书学习,接触到了《资本论》等理论书籍,虽然起初吃力,但他并未退缩,他和其他战犯一起参与农场劳动,哪怕年纪大了,体力不济,也坚持完成任务,有一次,他和杜聿明被编在一组,一起抬粪下地,因步伐不齐而引人发笑,昔日统军上万的将军,如今在田间劳作,场面虽有戏剧感,却也道尽了时代的变迁。 1956年,傅作义再次上书中央,表达对陈长捷等人的关注,中央也开始逐步考虑对战犯的处理政策,终于到了1959年,特赦名单公布,陈长捷位列其中,在功德林待了整整十年,他终于获得自由,出狱那天,傅作义在北京鸿宾楼设宴接风,陈长捷虽姗姗来迟,态度依旧冷淡,但终究还是赴了约。 宴席上,傅作义详细讲述了当年北平和平谈判的全过程,他解释为何无法事先通知陈长捷,坦言自己也曾备受煎熬,这些话,陈长捷听在心里,脸上的神情逐渐缓和,他没有回应太多,也未再责怪,只是沉默良久,最终伸手与傅作义握了一下,这一握,既是对过往的释怀,也是对现实的接受。 信息来源:《李宗仁回忆录》自我毁灭的西南保护战 1370页-1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