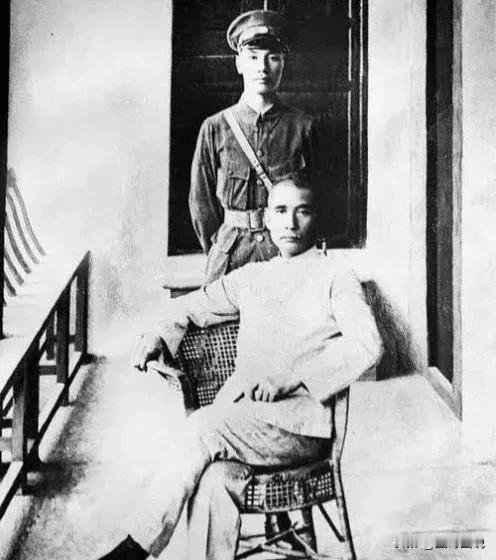在清洗龙武功臣的前后,唐玄宗对中枢又作了调整,萧嵩替代了源乾曜,宇文融、裴光庭替代了李元纮、杜暹。 庸相的仕途 萧嵩长着好胡髯,潇洒,威风,庄重,给人以信任感。 瞧瞧萧嵩,史书白纸黑字记着,他最大的优势是啥?一把好胡子!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往那一站,自带“靠谱”光环。玄宗一看,嗯,有派头,像个能镇场子的宰相。可翻开他的政绩簿,除了奉命监修国史这类事务性工作,实在乏善可陈。处理政务?能力平平。推荐人才?眼光更差。他推荐的王丘、严挺之,后来证明都非栋梁之材。说白了,萧嵩就是个政治花瓶,靠着出色的“形象管理”和玄宗对他外表的偏爱,坐稳了相位。盛世宰相,选了个“门面担当”,这开局就透着玄机。 萧嵩之后,宇文融登场。这位爷的“名气”,可就更“硬核”了。他是靠“搞钱”出名的。玄宗后期,花钱如流水,宫廷开销、赏赐功臣、四处封禅,国库再厚也经不起折腾。宇文融瞅准了皇帝的心思,化身“财政魔术师”,他的绝招是“括户”——大规模清查逃亡户口和隐匿田产。听着像整顿吏治、增加税收的正经事吧?可实际操作起来,完全变了味。为了追求速度和政绩,宇文融的手下官吏如狼似虎,手段粗暴至极。管你实际有没有逃税,先按“潜逃户”的帽子扣上,严刑拷打,逼着认缴巨额赋税和罚款。一时间,民间怨声载道,鸡飞狗跳。宇文融靠着这种近乎掠夺的方式,确实在短期内给玄宗搞来了大把银子,解了燃眉之急。玄宗龙颜大悦,宇文融自然平步青云。这种饮鸩止渴的“理财能手”,名声能不大吗?不过是恶名罢了。他满足了皇帝对金钱的渴望,却透支了民心,给盛世的根基悄悄凿开了裂缝。 裴光庭接棒,他的“出名”方式又换了个赛道——搞制度创新。他推出了一个叫“循资格”的选官制度。核心思想简单粗暴:当官升迁,不看才能,只看资历!排队,论资排辈,年头熬到了,位置自然就是你的。这玩意儿一出,整个官场都懵了。有才华的年轻人?对不起,后面排队去!庸碌无能的老油条?恭喜,您资历深,该您上了!裴光庭这套制度,简直就是给官僚体系打了一针强力麻醉剂。它彻底扼杀了官员的进取心和创造力,把大唐的官场变成了按部就班、死气沉沉的养老院。效率?活力?不存在的。要的就是一个“稳”字,一个“不出事”就好。裴光庭用制度化的平庸,换取了表面的秩序稳定,玄宗居然也接受了。这种制度遗毒深远,让整个官僚系统加速僵化,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那么问题来了,唐玄宗,一代英主,早年励精图治,慧眼识珠,晚年怎么就迷了心窍,把这帮“庸人”一个个扶上高位,还让他们“名垂青史”(虽然是恶名)?深挖下去,答案让人脊背发凉。 首先是玄宗心态的巨变。开元盛世的光环太耀眼,他飘了。早年那种虚怀若谷、求贤若渴的劲头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好大喜功、贪图享乐和刚愎自用。他需要的不再是能匡正得失、直言进谏的诤臣,而是能让他舒服、顺心,能无条件执行他意志(哪怕是荒唐意志)的“工具人”。萧嵩的“稳重”(实为平庸),宇文融的“搞钱能力”(实为盘剥),裴光庭的“制度稳定”(实为僵化),李林甫的“办事得力”(实为专权逢迎),恰恰都戳中了晚年玄宗那点隐秘的心思——别给我添堵,让我好好享受这盛世繁华。 其次是权力结构的异化。清洗功臣集团后,玄宗需要巩固皇权,防范新的权力中心崛起。这些“庸相”们,要么能力有限构不成威胁(如萧嵩),要么根基浅薄只能依附皇权(如宇文融),要么用制度固化阶层削弱潜在对手(如裴光庭),要么干脆自己就是皇权最忠实的看门狗(如李林甫)。他们在不同层面上,都成了玄宗强化个人独裁的棋子。用庸人,有时候比用能臣更“安全”,因为他们离不开皇帝的恩宠。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