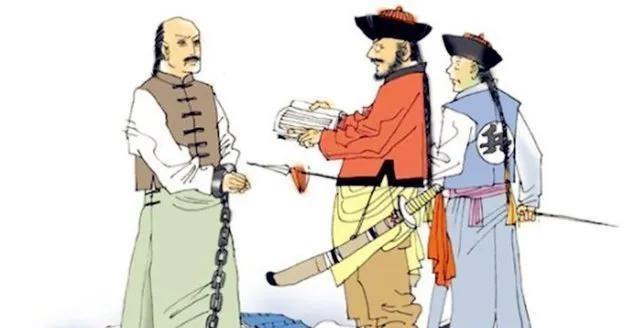1726年,年羹尧死后一周,雍正下令处死汪景祺,并将首级悬挂在菜市口,这一挂就是十年。 汪景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兄长汪见祺官至礼部主事,这样的家庭背景本应赋予他顺遂的仕途起点。 然而,汪景祺的科举之路却异常坎坷,直至康熙五十三年才勉强考中举人,此时他已年过四十,与同期进士相比,仕途前景已然黯淡。 科场的失意塑造了汪景祺乖张不羁的性格,他 “性豪迈,喜纵谈天下事”,却因 “恃才放旷,屡犯忌讳” 而得罪乡邻。 在浙江家乡时,汪景祺曾在酒肆当众讥讽杭州知府 “鼠目寸光,只知盘剥百姓”,被地方官记恨在心,最终被列入 “劣绅” 名册。 雍正元年(1723),汪景祺在京城参加会试期间,又因在客栈墙壁上题诗嘲讽主考官 “眼盲心浊”,被逐出考场,断绝了正途仕进的可能。 康熙末年,年羹尧凭借平定西藏、青海的军功成为西北重臣,权势日隆。 汪景祺敏锐地嗅到了机遇,于雍正二年(1724)千里迢迢前往西安,以投奔年羹尧的幕僚钱名世为契机,最终成为年府的食客。 为博取年羹尧的青睐,汪景祺精心撰写了《读书堂西征随笔》,书中不仅收录了为年羹尧歌功颂德的文章,还特意附上自己绘制的《西征图》,图中年羹尧身着蟒袍立于雪山之巅,周围将帅环伺,气势恢宏。 汪景祺在序言中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甚至将其比作 “周武之吕望,汉高之韩信”。年羹尧见此书时颇为得意,曾将其悬挂于府中 “西征堂”,每逢宾客来访便炫耀一番。 雍正三年,年羹尧被解除川陕总督职务,调任杭州将军,其势力开始瓦解。同年十二月,雍正以 “九十二条大罪” 将年羹尧革职下狱,次年赐其自尽。 在查抄年羹尧府邸时,浙江巡抚福敏发现了汪景祺所著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其中的 “悖逆言论” 引起雍正的雷霆之怒。 细究汪景祺的罪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对康熙皇帝的不当评价。书中《历代年号论》一文称 “康熙” 年号 “于义为非”,认为 “圣祖仁皇帝” 的 “康” 字暗含 “糠粃” 之意,这种牵强附会的解读被视为 “大不敬”。 雍正看到此处时怒不可遏,在奏折上朱批:“此等狂吠之语,实为千古所未有!” 其二,嘲讽雍正朝的政治举措。汪景祺在文中批评新政 “繁苛扰民”,尤其对 “摊丁入亩” 政策多有微词,他写道:“丁银摊入田亩,看似利民,实则官吏借丈量土地之机肆意盘剥,百姓苦不堪言。” 这番言论直接触及了雍正帝的改革底线。 其三,依附年羹尧的野心暴露。书中不仅记录了年羹尧的军功与权势,还隐晦提及 “功臣不可为” 的观点,暗示年羹尧可能遭受鸟尽弓藏的命运,这被雍正解读为 “离间君臣”。 从本质上看,汪景祺的文字并非单纯的学术探讨,而是卷入了皇权与军功集团的权力斗争。雍正继位初期,面临着 “九子夺嫡” 的余波,年羹尧、隆科多等权臣的存在始终威胁着皇权的集中。 汪景祺作为年羹尧的幕僚,其文字自然被视为 “逆论” 。 在查抄年府的过程中,福敏还发现了汪景祺与年羹尧的往来书信,其中一封写道:“将军手握重兵,西北半壁江山尽在掌握,当为长久计。” 这句话被曲解为汪景祺怂恿年羹尧拥兵自重,进一步坐实了其 “谋逆” 的罪名。 雍正四年(1726)正月,在年羹尧死后一周,雍正下达了处置汪景祺的谕旨:“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枭首示众,其妻子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俱革职,发往宁古塔。” 这道谕旨不仅判罚严厉,更体现了雍正 “杀鸡儆猴” 的意图。 从判决到执行,整个过程仅用了三天时间,显示出雍正的急切心态。 汪景祺临刑前曾写下绝命诗,但监刑官以 “悖逆之人不配言忠” 为由,将其诗稿焚毁。 行刑当日,菜市口挤满了围观百姓,汪景祺却神色自若,对着人群高声喊道:“吾今日之死,非因文字,实因卷入权斗耳!” 这话让监斩官大惊失色,立即命人堵住他的嘴。 雍正杀了汪景祺后,尤不解恨,下令将其首级长期悬挂。菜市口作为清代北京的刑场,是平民百姓聚集之地,当时此处有一家名为 “王记茶馆” 的店铺,正好对着悬挂首级的木杆,茶馆老板为免客人不适,特意在窗前挂起竹帘,却被官府以 “遮挡圣谕” 为由强行拆除。 直到乾隆元年(1736),左都御史孙国玺在奏折中写道:“菜市口乃商贾云集之地,悬首十年,恐伤天和。” 乾隆在批复中称 “景祺罪虽当诛,悬首已久,可着即掩埋”。 年羹尧死后,其党羽多被牵连,但汪景祺作为 “文人 的代表,其处置方式更为残酷。据《雍正朝起居注》记载,雍正在处理完汪景祺案后,曾对大臣们说:“武人叛乱,不过祸及一时;文人乱心,足以动摇国本。” 这句话道破了汪景祺之死的背后隐情。 参考资料:《清世宗实录》《啸亭杂录》《雍正朝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