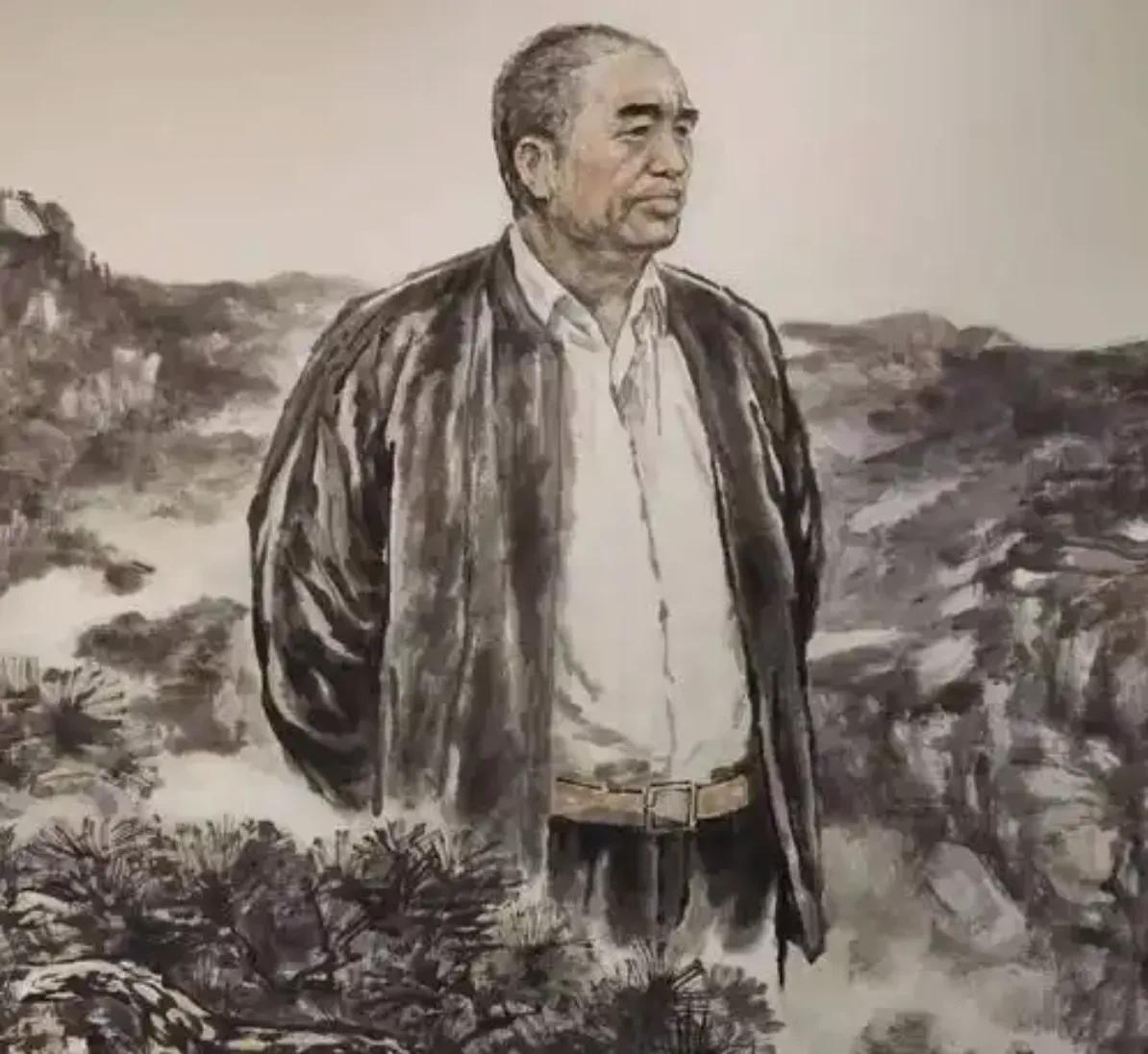战国时魏国邺城三老勾结巫婆,年年以“河伯娶妇”为名敛财。今年他们又选中了贫家少女阿桑,新上任的西门豹只用一招就解决了这帮骗子。 漳水汤汤,浊浪拍打着邺城残破的河岸。七月的风带着水腥和焚香的浓烈气味,盘旋在临时搭起的祭台四周。台上,三老和廷掾们锦袍肃立,脸上是多年练就的庄重,眼底却藏不住一丝即将得手的贪婪。台下,百姓如沉默的蚁群,衣衫褴褛,目光死死盯着祭台中央——那里站着瑟瑟发抖的阿桑,粗麻衣难掩清秀,泪痕已干涸在绝望的脸上。她的父母被挤在人群最前面,老父的拳头攥得死白,母亲无声地抽噎,肩膀抖得像风中的枯叶。这是今年献给河伯的新妇,又一个被“河伯娶妇”吞噬的贫家女儿。 “时辰到!”大巫婆的声音尖利如枭鸟,满头乱糟糟的花白头发随动作颤动。她披着五彩法衣,手持桃木剑,围着阿桑念念有词,眼中精光闪烁,扫过台下,也扫过台上那些穿着华服的身影。三老微微颔首,廷掾捋须而笑——又是一年百万钱的进项,稳稳落入囊中。百姓的头颅垂得更低,那沉默里,只有漳水在呜咽咆哮。 就在巫婆即将把阿桑推向那象征深渊的河岸时,一个低沉威严的声音穿透了压抑的鼓乐:“且慢!”人群如被利刃劈开,裂开一道缝隙。西门豹身着县令官服,在两名甲士的护卫下,缓步而来。新任邺令的目光平静无波,却让台上的三老廷掾心头猛地一坠。 西门豹径直走到祭台中央,审视着脸色惨白、抖若筛糠的阿桑。他转向大巫婆,声音不高,却清晰得让每个人都听得真切:“此女不美,恐难入河伯之眼。”他微微一顿,目光转向那浑浊翻滚的漳水,语调竟带上几分商量的意味,“烦请大巫辛苦一趟,入水为吾等详细禀告河伯,待寻得真正佳人,再行奉上,如何?” 大巫婆脸上的皱纹骤然扭曲,像是听到了世间最荒诞的鬼话:“你……”话音未落,西门豹身后两名如铁塔般的甲士已如鹰隼般扑上,铁钳般的手牢牢扣住她的臂膀。老巫婆那身五彩法衣在挣扎中凌乱不堪,刺耳的尖叫划破凝滞的空气:“饶命!大人饶命啊!河伯……” “噗通!” 尖叫被浑浊的浪花粗暴地掐断。巫婆像一块破布被狠狠掼入湍急的漳水,溅起一人多高的水柱。那翻涌的浊流只剧烈地冒了几个气泡,便迅速恢复了它无情的奔流,水面除了一圈圈扩散的涟漪,再无他物。祭台上下,死一般寂静。风似乎停了,连呜咽的漳水也屏住了呼吸。百姓们张大了嘴,眼珠几乎要瞪出眼眶,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吞噬了巫婆的河面。台上,三老和廷掾们面无人色,豆大的汗珠从额角滚落,浸湿了华丽的衣领。 西门豹却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他肃立岸边,官袍的衣角在风中纹丝不动,目光依旧沉静地注视着那幽深的水面,仿佛在等待一个回音。时间在令人窒息的死寂中艰难爬行。一息,两息……水面除了漩涡,再无动静。 西门豹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声在绝对的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冰冷的遗憾。他缓缓转过身,目光扫过台上那群面如死灰、抖如秋风落叶的豪强,声音不高,却字字如冰珠砸落:“大巫久去不归,恐是年老力衰,耽搁了河伯的要事。”他略作停顿,目光精准地落在大巫婆身后那几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抱作一团的女弟子身上,“尔等弟子,速去一人,助尔师一臂之力,催请回音。” “大人开恩!大人开恩啊!” 如同被无形的重锤狠狠砸碎了脊梁,台上的三老廷掾们再也支撑不住那身华服所代表的体面。扑通!扑通!膝盖砸在坚硬的祭台木板上,声音沉闷而惊心。锦袍沾满了尘土也浑然不顾,平日里高高扬起的头颅此刻卑微地抵在冰冷的木板上,撞得砰砰作响,额头上顷刻间便见了刺目的猩红。涕泪与鲜血混在一起,顺着他们惊恐扭曲的面颊流淌下来,糊满了华贵的衣襟。“吾等有罪!有眼无珠!大人饶命!饶命啊!” 西门豹负手而立,目光越过脚下这群抖成一滩烂泥的权贵,投向远处那沉默如海的百姓。他微微抬手,制止了甲士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