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军统特务毛森抓到了一个交际花小姐,在审讯期间,毛森扒下她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肤,“你到底说不说!”见美人还不开口,毛森直接将点燃的烟头按在她身上。
1949年深秋的厦门笼罩在阴云之下,审讯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年仅二十五岁的刘惜芬被反绑在木椅上,胸前的衣裳被刀刃划开道道裂口。
叼着雪茄的审讯官凑近她耳边威胁,烟灰簌簌落在她渗血的伤口上。
这个从护士变成地下党员的姑娘始终挺直脊梁,嘴角竟泛起若有若无的弧度。
在敌人眼里这是挑衅,在战友心中这是永不熄灭的火种。
时间倒回1924年的厦门码头,咸湿的海风里传来婴孩啼哭。
刘家新添的女婴尚不知命运多舛,六岁丧母的打击让姐妹俩早早就懂事了。
她们跟着做手工活的父亲艰难度日,破屋漏雨时就挤在墙角数瓦片,米缸见底时就分食半个地瓜。
1938年日军铁蹄踏碎鹭岛平静,十五岁的刘惜芬被迫辍学,背着竹筐穿梭在炮火未熄的街巷卖油条,油锅烫出的水泡和空袭警报声成了她最深的童年记忆。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博爱医院招护士那年。
白天她在诊室给伤员换药,夜里蹲在走廊就着月光啃医书。
那些趾高气昂的日本医生把中国病人扔在阴暗的一楼,她却总偷偷把消炎药片塞进同胞手里。
有次她撞见地下党员被追捕,二话不说把人藏进药品柜,等搜查的宪兵走远才发现自己后背全湿透了。
正是这次冒险,让革命的火种真正在她心里扎了根。
1945年抗战胜利的爆竹声未落,厦门又陷入白色恐怖。
刘惜芬在中山路开了间小诊所,挂着"专治头疼脑热"的布帘,实则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常来借书的胡大姐总说:"惜芬啊,你给穷人看病时眼里的光,跟咱们红旗上的五角星一个样。"
这话在她心里滚了四年,直到1949年春天,她在鲜红党旗下举起右手,听见自己心跳声和解放军的炮声渐渐重合。
那年夏天的厦门格外闷热。
杀人如麻的毛森坐镇警备司令部,城门口天天挂着新的人头。
刘惜芬和战友们偏要往虎口里闯。
他们在午夜把"迎接解放"的标语贴满思明南路,用浆糊刷子在骑楼柱子上画五角星。
气得暴跳如雷的敌人全城搜捕,却没想到最危险的情报员,正踩着高跟鞋出入他们常去的百乐门舞厅。
化着浓妆的刘惜芬在舞池里旋转,耳垂上的假珍珠随着探戈节奏晃动。
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军官最爱搂着她说机密,有次某位参谋长炫耀刚制定的清剿计划,她故意把红酒洒在他崭新军装上,趁着手忙脚乱擦拭时记下了所有细节。
等回到诊所阁楼,她就着煤油灯把情报编成暗码,藏在给"病人"的中药包里。
危险终究在秋雨绵绵的夜晚降临。
三个便衣踹开诊所木门时,刘惜芬正把最后一份名单塞进墙缝。
特务把诊所翻得底朝天,却没想到他们要抓的"舞场红玫瑰",此刻素面朝天穿着护士服,口袋里还装着没发完的退烧药。
在警备司令部的刑房里,烧红的烙铁烫焦了她的锁骨,竹签扎进指甲缝又拔出来,可她始终重复着:"我是护士,只管救人。"
10月15日解放军总攻的炮声震得牢房铁窗哗哗作响。
满脸血污的刘惜芬挣扎着爬到墙边,把耳朵贴在冰凉的水泥墙上。
当听到远处传来熟悉的冲锋号时,她干裂的嘴唇终于扬起笑容。
丧心病狂的敌人在撤退前,用麻绳结束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她倒下的地方,离厦门解放只差三天。
五年后的深秋,一队解放军护送着黑檀木骨灰盒回到鹭岛。
沿途百姓默默摘掉斗笠,卖油条的老阿婆颤巍巍往灵车上抛白菊。
如今鸿山脚下立着块花岗岩纪念碑,上面既没刻官职也没写事迹,只简单留着"刘惜芬"三个字。
常有晨练的老人指着石碑对孙子说:"瞧见没?当年就是这样的硬骨头,才换来咱们能在海边安心遛弯啊。"
从卖油条的小姑娘到穿梭敌营的红色特工,这个厦门女儿用二十五载光阴诠释了何为忠诚。
她没等到亲眼看见红旗插上日光岩的那天,但鼓浪屿的涛声里永远回响着她的名字。
那些在舞厅套取的情报、在诊所传递的密信、在刑房坚守的秘密,最终都化作鹭江两岸的万家灯火,照亮着后来人脚下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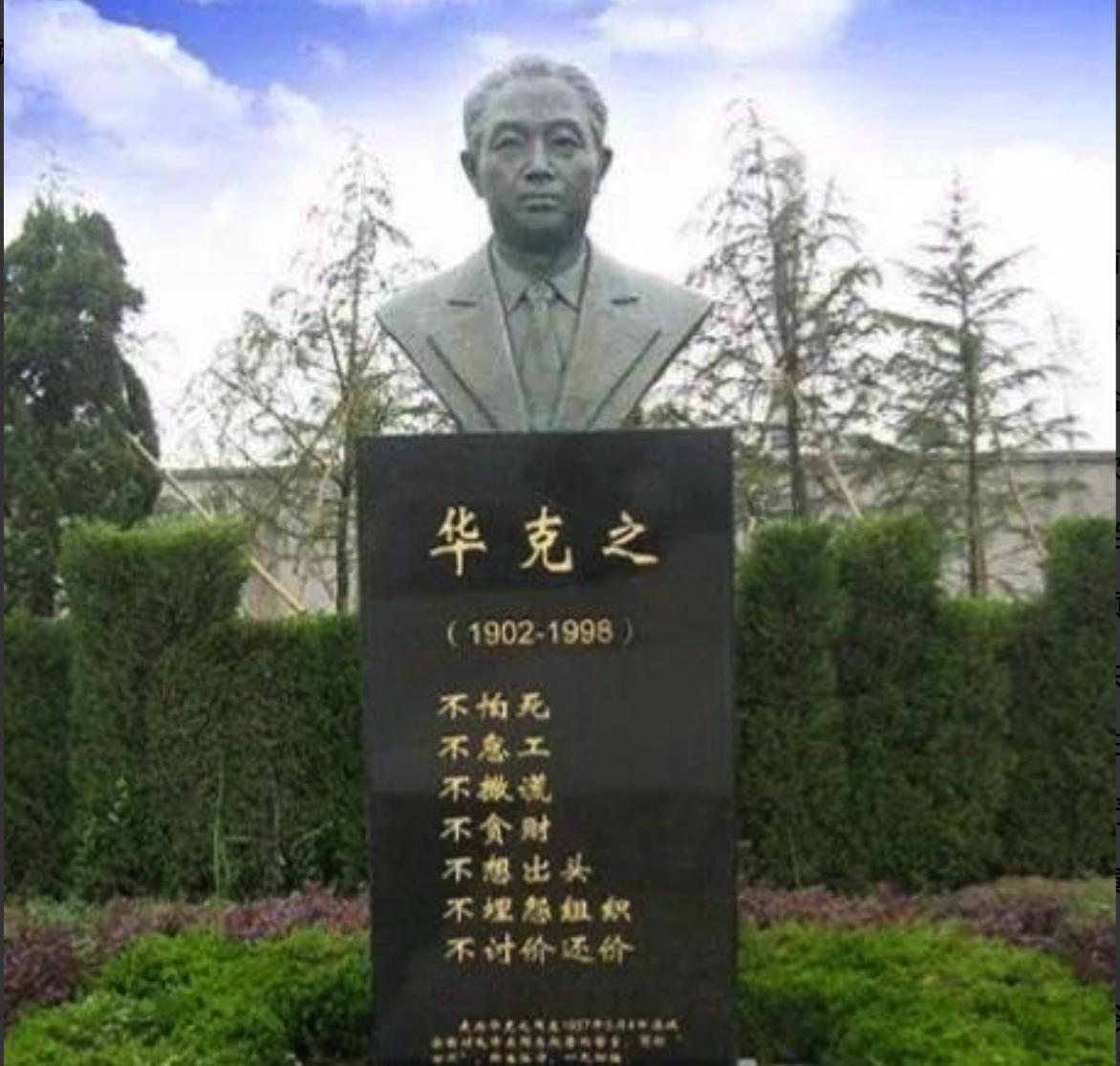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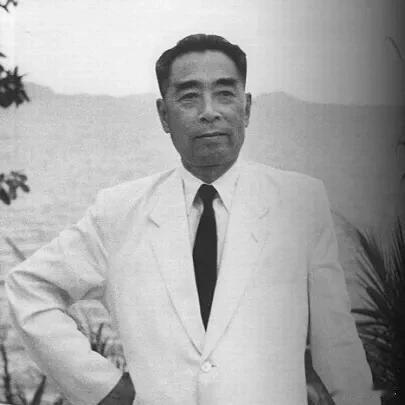


思想决定贫穷观念改变生活
[玫瑰]
西伯克鲁斯
她成为别人的垫脚石,老爸和我常说想混得好,大家一起冲的时候你就跑后面,大家商量问题的时候你是声音最大的,如保证不掉链子紧紧跟随什么走。(不要说冲在最前面),随时为了什么什么牺牲(别人信就行,自己可不能做)。
用户10xxx03 回复 07-01 20:51
就只有大滑头和小滑头两个在怎么办?是不是小滑头想等着大滑头先“闭关”,而大滑头却想等着小滑头先“闭关”?结果是不是应该两个都“黄“了!
天高云淡
英雄的事迹感人,作者的文笔也很好。
林炳
英雄!人们永远怀念您!
用户39xxx78
英雄值得永远追忆
水山
毛森,军统特务头子。白色恐怖者杀人太多,人称毛骨森森
用户10xxx22
致敬人民英雄
雷達
[爱心][爱心][爱心]
00323
再看看现在的女人
用户10xxx11 回复 07-29 12:12
FM收音机,额CC筏板,0
创意
英雄!人民永远怀念您!
用户10xxx30
牢记血泪仇,不忘先烈志
用户64xxx20
可惜了没能坚持到解放
zhangxuyun
[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