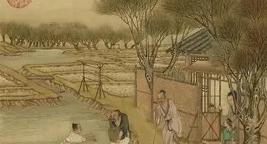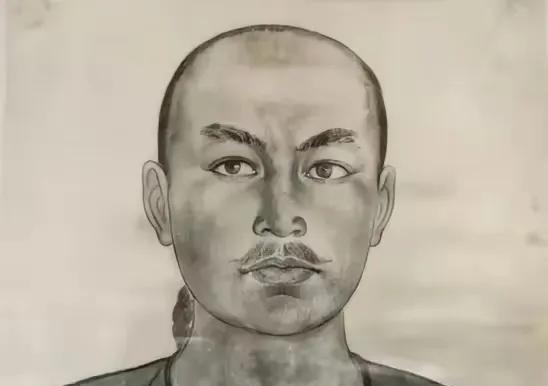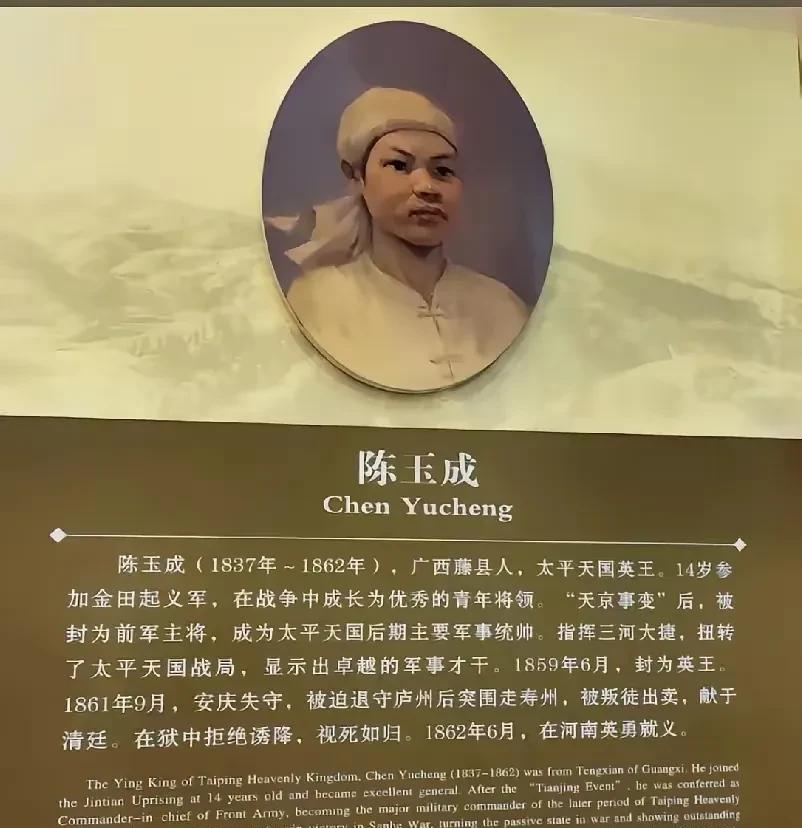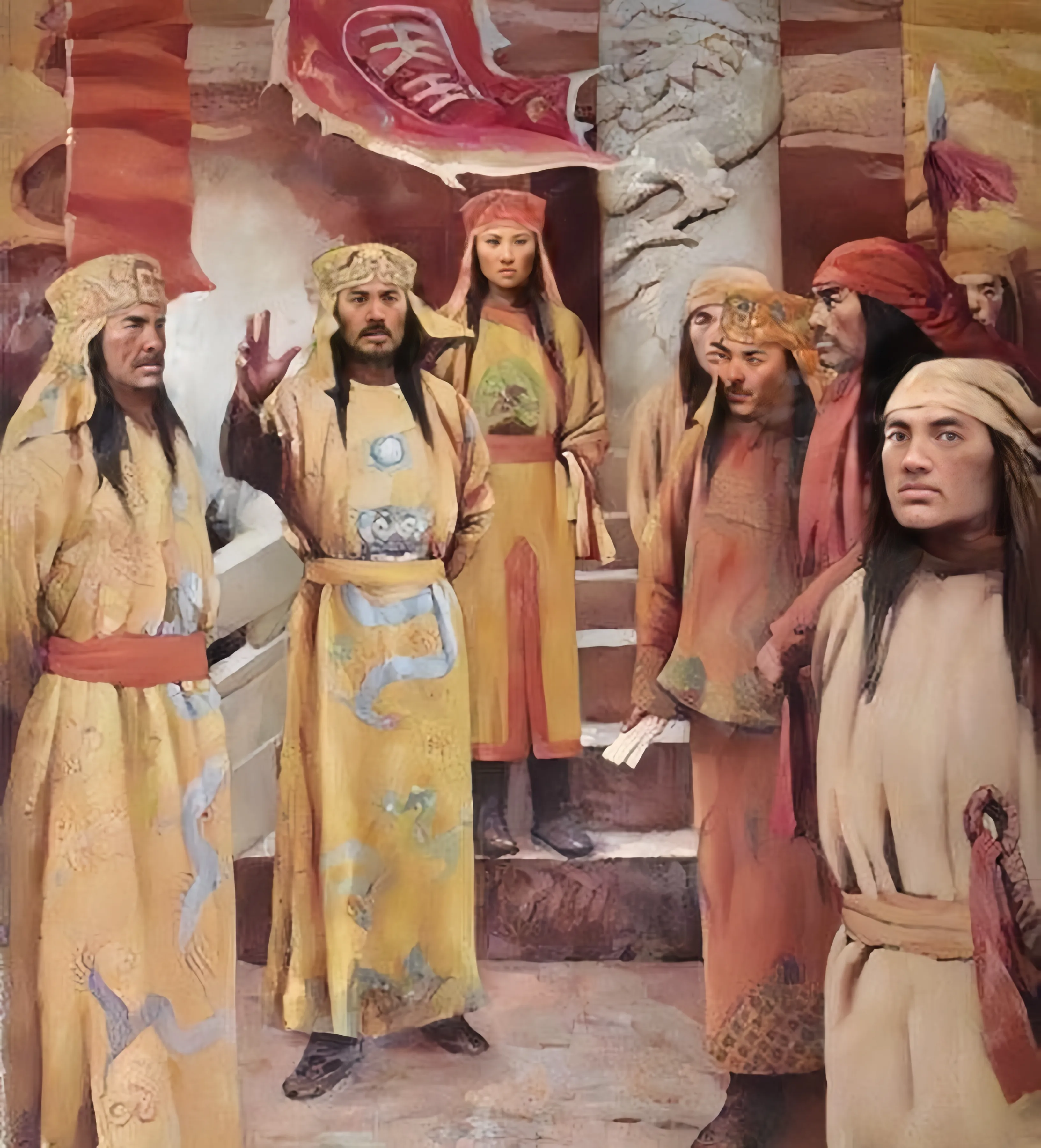古代地多人少,农民为何却宁可被地主剥削,也不愿意去开垦荒地? 我在禄丰县的小村子里出生长大,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那年夏天,天空久久不肯施舍一滴雨水,庄稼在烈日下渐渐枯萎。我每天清晨都会望着天空,期待着乌云的出现,却始终只看到一片刺眼的蓝。 父亲站在龟裂的田地边,长叹一声:"又是一年灾荒,老天爷是要我们活不成了。"我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庞,看着他因长期弯腰劳作而变得佝偻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 1943年,我们禄丰县的灾难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早在前一年,黑鸟瘟疫就已经摧残了大片树苗,紧接着又是一场台风,将许多未成熟的水稻变成了白穗。父亲当时就预感到不妙,可谁能想到,1943年的春天,一场持续数月的干旱彻底断送了我们生存的希望。 随着存粮一天天减少,村里的人开始想方设法延长食物的寿命。最初,大家都将本就不多的大米煮成极稀的米汤,希望能撑得更久一些。后来米也没了,一家五口一天只能共同分享一个饼,然后灌下大量的水,企图骗过饥饿的肚子。 我曾经问过父亲:"四周荒地那么多,为什么我们不去开垦些新田?"父亲将手里的烟袋重重地放在桌上,脸上的表情既愤怒又无奈:"你以为那些地是无主的吗?别说是荒地,就是山上那些寸草不生的石头地,也早就被皇帝或者大户人家划为己有了。" 原来,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从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到夏商周的井田制,再到秦以后的私有制主导模式的变迁。看似无人问津的荒地,实际上都有明确的归属。《诗经》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虚言,天下土地要么归皇帝所有,要么被赐予贵族地主,我们这些底层农民若擅自占用,轻则罚款,重则入狱。 随着粮食的耗尽,村里人开始寻找其他可以果腹的东西。先是树叶,然后是草根,再后来是树皮。村边那棵大槐树,百年树龄,遮天蔽日,如今树皮被剥得光秃秃的,露出苍白的树干,像一个被剥光衣服的老人,无助地站在村口。 更令人绝望的是,连续的干旱使得附近的小河都干涸了,河床上露出一道道裂痕,像是大地的伤口。那些曾经在河里游弋的鱼虾,要么早已死去,要么被污染,成为了传染病的源头。即使有些地方还残存着水源,但那些鱼虾也早已被官府征用或者被私藏起来。 《中国灾荒史》记载,明朝期间,仅河南一地就发生了611次自然灾害,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这些频繁的天灾,加上人为的制度压迫,让我们这些农民始终在生存的边缘挣扎。 那年干旱结束后,我开始思考父亲说的话。村里的李大伯有个远方亲戚,曾经一时冲动去山边的荒地开垦了一小块地,结果被官府发现,不仅被重罚,还被迫服徭役三年。从此他家妻离子散,老母无人照料,在病痛中离世。这样的教训深深刻在每个村民心中。 我曾以为开垦荒地只是法律上的阻碍,直到我随父亲去帮村东头的王财主开荒时,才明白其中的艰辛。那天,我们带着简陋的农具,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王财主站在阴凉处,指挥着十几个佃农翻动坚硬的土地。 "这块地看起来不错,但土质太硬了。"父亲用手捻着一把土,对我低声说道,"就算开出来,没有好的水源,种出来的粮食也寥寥无几。" 开垦荒地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需要判断土质是否适合农作物生长。古人有"看土色、闻土味、捏土感"的方法,但这需要多年经验。错误的判断会导致一整年的劳作付诸东流。更不用说,荒地往往地形复杂,缺乏稳定的水源,这在农业生产中是致命的。 除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开垦荒地还需要大量劳力和工具。最关键的是役牛,它们可以大大减轻人力负担。但在古代,一头健壮的耕牛价格昂贵,动辄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数年的收入。记得村里张三曾经攒了十年钱才买了一头瘦弱的老牛,结果第二年牛就病死了,他负债累累,最终卖掉了自己的女儿换取口粮。 即使克服了这些困难,开垦荒地到收获的周期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在此期间,农民不仅要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还要应对朝廷的赋税征收。明代的一条法律规定,新开垦的土地在三年内也要缴纳田赋,尽管数量有所减免。但对于已经一贫如洗的农民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相比之下,成为地主的佃农虽然被剥削,但至少有一份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我们村的许多人都给王财主家做长工,尽管每年要上交七成的收成,但剩下的三成足以让一家人勉强度日。更重要的是,在灾年,地主有时会提供一些救济,毕竟死了的佃农对他们也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