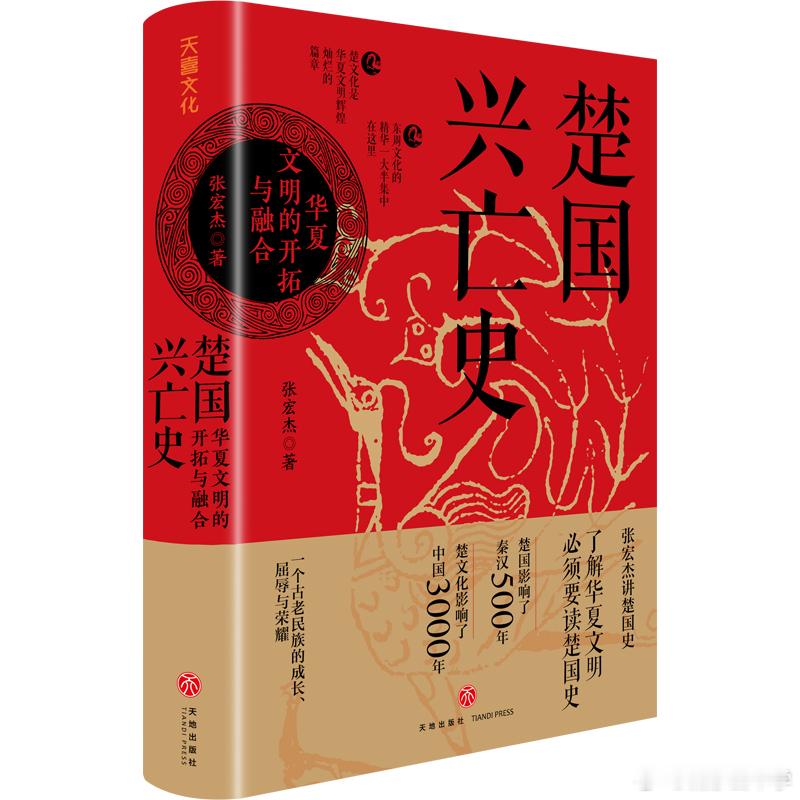张宏杰论秦楚文化气质之不同及楚国拒绝法家路线,野蛮终于战胜文明。
月盈而亏,盛极而衰,是中国历史自古以来不变的规律。即使是以象征生生不息的凤凰为图腾的楚国也不能例外。
楚国衰落的伏笔,其实早在它达到极盛前就已经埋下:吴起那次著名的变法未能彻底,就已经注定了楚国将在国际竞争中落后。
秦国实力本来一直弱于楚国,它一直是追随于楚国后面的忠实盟国。然而,两次结果不同的变法,决定了秦国迅速超越楚国,并且最终吞并楚国,统一天下。
当楚国在中国南方“以启山林”时,秦人则在西北“逐水草而居”,“杂戎翟之俗”。两国都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顽强进取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楚国一样,边疆小国秦国也一直得不到中原文明的承认:“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
两国的区别只是秦国比楚国还要落后,蛮夷化的程度还要深。
秦国的地理环境远不如楚国。它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人民生活贫困。《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秦国的立国和发展一直落后于楚国。楚国在西周初年就立国了,秦国直到东周时代才被封为诸侯国。西周秦人墓葬中的随葬品远少于楚人,而且大多数都是陶器,这反映出秦国早期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楚国。如果比较历史之悠久,物质之繁盛,文化之发达,秦国不能望楚人之项背。
但是,在改革大潮中,秦国却能顺应时代,迅速成功。商鞅变法,使秦国发生了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变化,由此迅速崛起。那么,为什么是落后的秦国在列国变法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领先的楚国却失败了呢?
和楚国竭尽全力中原化不同,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一直不那么热衷。楚国的强大,是因为它背靠蛮夷,却不断向中原汲取文化力量。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的过程。秦人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了浓烈的蛮夷气质。
穆公时代开始伐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后汉书·西羌传》说,生活在秦地的少数民族,“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他禁令。……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秦霸西戎后,戎族在秦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甚至在局部地区占有主导地位。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军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
四塞之地的秦国很少受到外部文化的冲击和刺激,所以秦人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本土很难产生杰出人才,也明显缺乏楚文化的创造性。秦国的著名宰相,几乎都是从其他国家聘来的。这个国家不可能产生屈原那样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巨匠和《楚辞》那样的鸿篇巨制,也无法产生像庄子那样洒脱飘逸、老子那样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正在中原国家渐渐改变殉人的野蛮风俗的时候,秦国却变本加厉。考古发现,秦武公死时,殉死者66人;穆公死时,殉死者多达177人。陕西凤翔雍城发掘出土的秦公1号墓,墓主秦景公,是秦穆公的四世孙,墓中被殉葬者竟有186人之多。被杀殉之人主要放置于墓室四周。一类是箱殉,共72具;一类是匣殉,共94具。箱殉是将殉葬者以绳索捆绑成蜷曲的形状,装入箱内;匣殉者被装入长2米、宽0.7米左右的薄棺材之内。另外,在墓室的填土中还发现20具人牲。
《诗经》中那首著名的诗歌《黄鸟》说:“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大意是说,黄雀鸟啾啾鸣叫声凄凉,飞来停落在枣棘上。让谁陪着穆公去殉葬?子车家老大名奄息。就是奄息这个百里挑一的勇士豪杰,今天面对白骨森森的殉葬坑,仍然恐惧得颤抖心悲凉。那高高在上的苍天啊,我们的良人被无辜地杀害了!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也是最功利的。西北少数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司马迁评价秦国文化说:“今秦杂戎翟(狄)之俗,先暴戾,后仁义。”(《史记·六国年表》)
事实证明,后发优势是秦国统一天下的主要原因。历史短,文化浅,礼治传统不完备,反而成了秦国发展壮大的优势。因为文化包袱轻,所以秦国在列国之中改革精神最强烈。那些老牌强国深受西周宗法制度的束缚,用人凭血缘,看门第。只有秦国君主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别国嘲笑,四处招揽人才。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著名宰相,几乎都是从其他国家聘来的。正是这些外来的人才大幅度改革了秦国的内政外交,让这个落后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秦国的简单、质朴、野蛮、残酷和功利主义气质,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
学者胡克森说,法家文化有着深厚的草原文化基因。诞生于半草原半农业区域的法家文化,具有其他中原文化所没有的残酷、简单、直接的特点。法家学派的思考,完全是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核心,而丝毫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法家学派认为百姓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连夫妻、父子都不可相互信赖。因此民智不足用,民心不足虑。他们建议统治者从人的劣根性出发,严刑峻法,把人当成动物一样管理,只要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加上严刑峻法,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就可以调动民众,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法家不相信感情,只相信利益;不相信文化,只相信刀剑。因此法家改革者所制定的法律,都异常严苛残酷。
应该说,在春秋战国各思想流派中,法家文化是最不人道、最反人性的。如同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一样,法家不追求公平正义,只追求现实功利。不过,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西方诸思想流派中始终居于末流,而在中国,百家争鸣的结果却是法家思想最后胜出。
吴起变法在楚国的失败,在某一侧面,说明了功利主义文化在楚国的失败。因为楚国文化的气质与功利主义反差极大。
如前所述,楚文化的特点是开放性、兼容性和创造性。和秦国不同,楚国从立国之初,对少数民族就并非只有“压服”和“杀戮”之策,而是更多采取怀柔政策,所以“甚得江汉间民和”。
楚人热衷扩张,却并不致力于掠人为奴。他们明智地尊重各地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表现出强烈的人道精神。比如在大冶铜绿山的考古中,人们并没有发现在春秋战国多年的开采中,有矿难及虐待而亡的现象。
因此,楚文化远比秦文化更人道、更宽容,“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黄瑞云:《楚国论》)。而且“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容的”(张正明:《楚文化史》)。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上,开创了一个发达的楚文明。孔子周游列国,“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孔子欣然前往楚地,但是他却西不入秦。显然,秦国在孔子眼中,是一个蛮夷之地,不可能实行王道。
而秦国的功利主义气质与法家文化却一拍即合。关于商鞅变法,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商鞅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像对中原国家君主那样说“以王道”,而秦孝公昏昏欲睡。于是,下一次见到秦孝公,他“说公以霸道”,孝公大悦。这个故事说明,商鞅变法的主导思想,是放弃中原王道政治文化,而改行赤裸裸的霸道。
商鞅的思路,是根据秦人物质贫乏、文化落后、不尚礼仪、只图实利的国民性格,进一步禁学愚民,实行严刑峻法,限制工商业发展而奖励耕战。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思路明显是反文明、反文化的。商鞅变法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极大地激发了人的私欲。正如《淮南子·要略》所说:“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在战国时代,文明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护身符,野蛮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欧洲历史也有相似的规律:
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
…………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力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所努力达到并已经达到的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适宜。(《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
在战国变法中,商鞅变法是最彻底的一次大改革。商鞅全面吸取了前几次变法,包括吴起变法的经验教训。秦国通过改革,成功地提高了资源汲取能力和军事作战能力,取得了惊人的成效,不久就使秦国“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新序》)。原本长期落后于楚国的秦国,迅速与楚国比肩。
作者简介
张宏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