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奴隶制的特点,大量的华夏族人民沦为国家罪隶,数量惊人,待遇残酷。】
奴婢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但数量之庞大,待遇之残酷,没有超过秦代的,连商、周和元代的情况都没有这么严重。秦代有名目繁多的罪隶,而且大部分是由国家层面占有的。仅仅是修建骊山陵墓的罪隶就有几十万人,这和其他朝代的情况是不同的。
罪隶在商周时期就存在,是有罪被罚做奴隶的人,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贾公彦疏《周礼·秋官·序官》:“古者身有大罪,身既从戮,男女缘坐,男子入於罪隶,女子入於舂稾。”《周礼·秋官·司隶》:“司隶,掌五隶之法。” 郑玄注:“五隶,谓罪隶、四翟之隶也。”罪隶位列第一。四翟之隶,就是四夷之隶,即蛮隶、闽隶、夷隶、貉隶,是商周王朝从南蛮、闽越、东夷和东北俘虏的少数民族充作奴隶。
秦代的奴隶,却大部分都是罪隶,也就是把统治下的华夏族人民大量沦为奴隶,当时又称为刑徒、居赀、斩黥城旦舂、黥劓城旦舂、斩城旦舂、黥城旦舂、完城旦舂、系城旦舂、刑鬼薪白粲、鬼薪白粲、耐司寇、刑隶臣妾、耐隶臣妾、隶臣妾等等,花样百出,名目极为繁多。
《商君书·去强》:“重罚轻赏,则上爱民…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秦代实行法家路线,严刑峻法,轻罪重判,刑九赏一,连弃灰于道都是重罪,“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李斯《行督责书》)”,所以“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秦代统治下的人民,因此大量沦为罪隶。还有很多,其实是因为拖欠了秦朝政府的赋税和各种罚款,或者是延误了劳役,被秦朝政府罚做罪隶。这里面甚至包括很多有爵位的身经百战的秦军,他们因为常年在外作战,所有的装备、兵器、衣服都要自备,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又因为家里缺乏劳动力或者是贫病等各种原因,欠下了国家的债,被秦朝政府罚做罪隶,同样受到残酷的虐待。在秦始皇陵附近的赵背户、瑶池头刑徒墓地中就发现了有爵位的秦军被罚在这里做苦役,尸骨上的残瓦写着他们的籍贯和爵位,如“东武居赀上造庆忌”、“东武东间居赀不更 ”、“[杨]民居赀公士富”、“阑陵居赀便里不更牙”、“博昌居赀用里不更余”、“杨民居赀武德公士契必”等,其中很多人还是被虐杀的,这就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墓志(《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刑徒墓》《文物》1982年3期)。
《史记·陈涉世家》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会天大雨,道不通……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也必然要被罚为罪隶,最终还是要被虐待致死。里耶秦简7-304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一个总编户人口才两千人左右的小小迁陵县(在今湖南省龙山县),奴隶、居赀就死了一百八十九人,一百五十一个隶、臣、妾当年就死了二十八人。死亡率如此之高,可见生前所受之残酷虐待。秦代的罪隶是男女老少都有的,现在发现年龄最小的仅五岁,这些婴幼儿也全部要“衣傅城旦舂具”,穿奴隶衣服和佩戴刑具做苦役(《岳麓秦简1003+0998+C10-4-13》)。
为了防止奴隶的大量逃亡,秦王朝专门制定了残酷的《亡律》来进行惩治。岳麓书院藏秦简2088记载,匿藏逃亡者的,与逃亡者同罪。简2009记载逃走的城旦舂被抓回来,脸上刺字,哪怕自己回来自首,也要鞭笞一百。怀孕的女舂,则用大铁刑具束缚。简1997记载,牧马的城旦逃走被抓回,要砍掉左腿,继续当城旦。男女百姓逃亡,其家人要被判处迁徙,基层干部里典、里老不报告也要被罚出甲和盾,这是非常巨大的开支,交不起罚款就要被罚做罪隶。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所说的“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
中国在蒙元统治时期,也存在大量的奴婢,他们往往被称为驱口,是蒙古人在灭西夏、灭金、灭宋、灭大理和西征过程中掳掠贩卖的各民族人口,这里面还包括来自东欧的斯拉夫人和少数来自非洲的黑人。元代驱口的数量,据有关专家估计,最多的时候可能达到一千万,占中国当时总人口的1/10,后来元朝政府下令释放过几次,仍保持有几百万的规模。但元代的驱口,大部分是被蒙古、色目权贵和汉族地主阶级所占有的,属于民间所拥有的奴婢,不是国家层面所占有的奴隶,在生活待遇上比秦代的罪隶要高。秦国自孝公变法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兼并战争,杀死了中国人口的2/3,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讲过这个情况,南宋史学大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户口考》中也讲过这个情况。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全国人口大概还剩下两千万,沦为罪隶的人数是不止1/10的。修骊山陵墓的有73万,其中除了少部分是有技术的工匠而外,大部分都是这些罪隶,当时称为刑徒。骊山陵墓完工以后,他们中不少人是被活埋了的,有些生前还遭到残忍杀害,肢体残缺不全。修长城的有40万,还有在全国修驰道的、修阿房宫的,到东海捕鲸的,到南方伐木的,数量极为惊人。一些刑徒甚至不得不集体逃亡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汉书·匈奴列传》颜师古注:“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史记索隐》引东汉应奉上奏汉桓帝书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后汉书·东夷列传》载:“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
过去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讲过秦代实行的是奴隶制度的问题,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后来负责出土秦简整理研究和定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先生在《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中又指出:“我们知道,由于秦人烧灭故籍,司马迁著《史记》时许多方面只能依据《秦记》,所以以往的学者总以为对秦的认识比较准确深入。近年有关秦的考古发现,却提出了很多全新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奴隶制方面的,使我们感到必须重新描绘晚周到秦社会阶级结构的图景。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发现和研究,展示了相当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景象。秦人的奴隶,大别之有官方的隶臣妾之类和私人的臣妾……隶臣妾之类刑徒,恐怕不能用汉代以下对刑徒的概念来理解……而且刑徒的身份如不经赎免,不能到一定年限解除,甚至株连到家属和后裔。这和汉律的隶臣妾等等有根本的差别。在秦简发现以前,学者已经从秦兵器的铭文里察觉大量刑徒的存在。与此作为对比,在东方六国的兵器铭文中则很难找到身分类似的人名。古书的情况也是一样,关于六国只能找出一些私人的臣妾,而少见官有的刑徒。这种现象恐怕只能解释为六国不像秦那样大规模地使用刑徒劳动力。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统一全国后的十几年间还曾暂时把这种(奴隶制生产)关系推广到六国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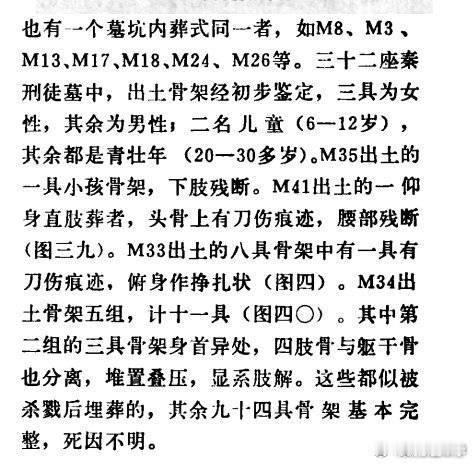

thc2202
秦朝的奴隶是较为低地位的人民,就连奴隶也可以分配到五十亩地,也不是农牧。清朝一个地主有五亩地就能叫地主,但是和秦朝的奴隶比起来差的远。罪犯刑徒也是可以拥有五十亩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