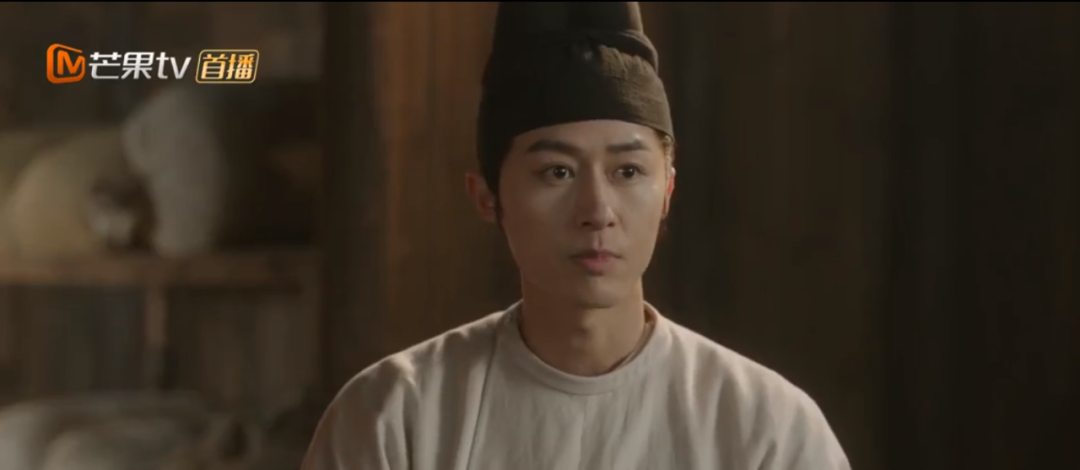
01
烧尾宴上,皇上和蒋长扬隐忍谋划了十来年,准备擒拿宁王,张谦的致命背叛,致使皇上、蒋长扬功亏一篑,宁王掌握主动权,大批忠臣学子惨死。
张谦的背叛,出乎意外。
宁王为谋反拉拢世家大族,从科举着手,打击寒门,把机会倾斜给世家子弟。

而这一次是蒋长扬想尽办法,给了寒门与世族公平一竞的机会。
按理说,这么难得的机会,张谦应该好好珍惜,他并没有。
是皇上、蒋长扬这一派的人对他不好吗?当然不是。
帝师徐祭酒一直很欣赏他,夸他才学深厚,定能高中。
刚科考完,马侍郎就急着向皇上讨张谦,说他心思细腻,才华横溢,想给他个好职位。
张谦连皇上、蒋长扬扳倒宁王的计划都清清楚楚,能说没把他当心腹?
这妥妥地走进了核心圈层,前途无量啊。
可刘畅告诉他,投靠宁王可以一步登天,张谦眼皮子浅,既然有这好事,何必舍近求远?

当利益足够大时,人性是经不起检验的,背叛起来是分分钟的事儿。
突然想起马侍郎想让张谦做自己的得力助手时,蒋长扬说的这番话:学子们涉世不深,精通的都是书上的圣贤之言,还需入仕打磨个几年,才可委以重任。
就连皇上都说:让张谦去州府历练两年,只要他心性不移,待调回京,我定将他留给你。
都说好事多磨,不经历考验,怎么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和底线?
就去基层打磨两年,张谦都等不及,那步步高升后,权力、金钱哪一样不是炙手可热,张谦是不是分分钟可以放弃底线呢?
人心难测,不要轻易相信一个没有经过考验的人,你看这次教训多深刻:皇帝差点成了傀儡;蒋长扬差点死去;那么多忠臣、新科进士都惨死于宁王屠刀下;于昶大将军及部下全部牺牲……
真的不要轻易挑战人性,后果你不一定承受得起。
02
宁王和刘畅在烧尾宴上大获全胜,张谦以为他的好日子来了,拍了拍马屁,顺带递上去一篇治国之策。
张谦口口声声不负刘畅与宁王的看中和提拔,刘畅直接给了他一杯毒酒。
与其说刘畅讨厌张谦,不如说刘畅讨厌自己。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投射效应”,指的是我们会无意识的把自己情绪、价值观等投射到他人身上。刘畅看不起张谦不忠,说一次不忠,终身不用,其实是刘畅骨子里讨厌自己不忠诚,他内心不能接受自己的这个缺点。
青春年少时,刘畅也是个上进青年,刻苦读书,希望通过自己的真才实学为朝廷效力。
刘畅和县主两情相悦时,宁王棒打鸳鸯,拆散了他们。
刘父官场亏空时,逼着他娶了何惟芳,他很抵触。
县主丧夫后做局逼着他结婚,他不愿意。

宁王打断他的腿逼着他入赘,他直接黑化了。
父母、县主、宁王都在逼着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他一步步背叛了曾经的自己,做了权势的傀儡。
刘畅恨那个不得不向权势低头的自己,当他看到张谦临阵倒戈,向宁王低头时,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把对自己的一腔愤怒发泄到了张谦身上,毕竟人都是要面子的嘛,不能骂自己,那骂张谦是可以的,惩罚也是行的。
张谦献上去的治国之策被扔在了水里。
当年,刘畅研究各地水系,用心拟了一份策论,想让宁王过目,宁王也是看也没看,就吩咐下人拿去烧了。
相似的情景,刘畅估计有一种报仇的爽感吧。
当年在宁王那受得气,在张谦这找补回来了。
也许有人会说,谁给你气受,你找谁去啊,没办法,刘畅内核弱啊,那个时候的宁王权势滔天,他不敢硬碰硬啊,他只能朝更弱小者下手,以发泄内心的扭曲和不满。
当然,战场上,当皇上和蒋长扬这边的势力大大超过宁王时,刘畅毫不犹豫就背叛了宁王。
背叛这种事儿,第一次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刘畅抵抗过、绝食过,甚至想过自杀,可父母、县主、宁王都没有放过他。
再次背叛,简直轻车熟路,毫无心理负担,刘畅甚至有一种报复宁王的快感,还说宁王的种种罪行,他都有证据,愿全力配合,彻查此案。这时的宁王不再是岳父,而是反贼,是奸佞之臣,要铲除殆尽。
宁王曾说过: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棋子,哪怕他对你不忠。只要利益足够大,任何时候都会有人为你所用。宁王还是自信过了头,当他不再是大势了,那个善于审时度势的刘畅一次不忠,就换来了他瞬间成为阶下囚。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没有人愿意被人当棋子用,更没有人能够容忍自己的自尊被人碾碎了按在地上摩擦,只要有机会,背叛起来让你猝不及防。

刘畅说他这一生都活在悔恨中,从未顺心如意过,听起来不免让人唏嘘不已。世俗中的权势、金钱、社会地位他都曾有过,但都是以背离他的初心为代价,都不是他想要的。
都说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这一生,那就守好初心,会少很多意难平。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