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纯属虚构,戏说三国,博大家一乐)
曹丕接过魏王玺绶的那一刻,余光不自觉地扫过殿内群臣。
他在寻找一个身影,不是那位以七步诗闻名的弟弟曹植,而是另一个看似低调的兄弟:曹彰。
世人皆知曹植才华横溢,深得曹操生前喜爱,却少有人注意到,曹丕真正寝食难安的,是那位手握重兵、战功赫赫的黄须儿曹彰。
建安二十五年,洛阳的冬天格外寒冷。
曹操病重之时,紧急召见的不是曹丕,而是镇守长安的鄢陵侯曹彰。
这个消息让时任五官中郎将的曹丕如坐针毡。

他太了解这个弟弟了,曹彰自幼好武,能徒手与猛兽搏斗,曾率兵平定代郡乌桓叛乱,麾下精锐之师堪称曹家最锋利的剑。
“父亲召子文前来,莫非是要改立世子?”曹丕在书房中来回踱步,这句不敢说出口的疑问像毒蛇般缠绕着他的心脏。
曹彰快马加鞭,昼夜兼程,可惜抵达洛阳时,曹操已然病逝。
据《魏略》记载,曹彰径直闯入灵堂,不是先跪拜亡父,而是抓住主簿贾逵厉声质问:“先王玺绶安在?”
这一问,暴露了曹彰的野心,也印证了曹丕长久以来的担忧。
曹丕不会忘记,几年前曹彰大破乌桓归来,曹操在邺城门口亲自迎接。
曹彰铠甲未解,战袍沾血,大步走到曹操面前,不无得意地说:“孩儿幸不辱命!”
那一刻,曹操拍着曹彰的肩膀大笑:“我黄须儿竟如此英勇!”
曹丕站在一旁,清楚地看见曹彰那双锐利的眼睛扫过自己,那目光中闪烁的不仅是胜利的喜悦,还有某种不容忽视的野心。
与文采斐然的曹植不同,曹彰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他不仅手握兵权,更在军中威望极高。
将领们对这位能带领他们打胜仗的王子心悦诚服。
乱世之中,刀剑往往比笔墨更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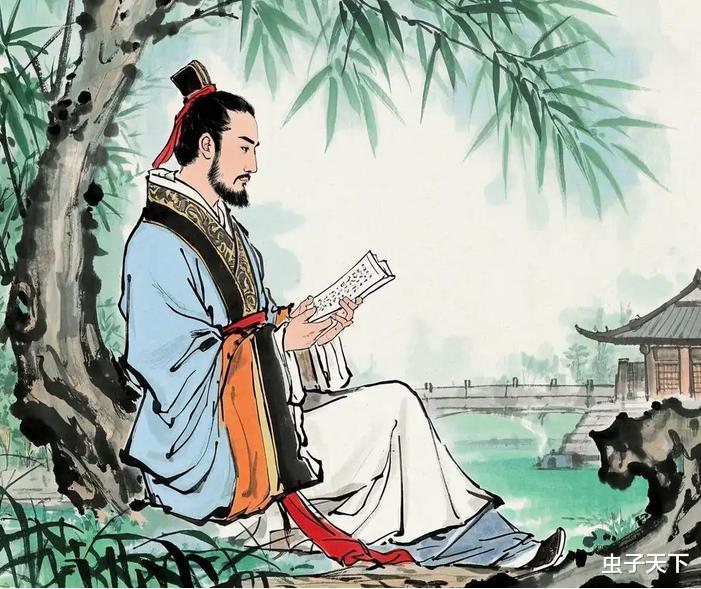
曹丕即位后,对曹彰的防范可谓费尽心机。
他采纳贾诩之计,逐步削夺曹彰的兵权,将他从长安调至宛城,远离边防重镇。
表面上,他加封曹彰为任城王,赏赐丰厚;暗地里,却在其府中安插眼线,严密监视一举一动。
黄初二年,诸王归国。
曹彰被迫交出兵符,带着寥寥数百亲兵前往封地。
临行前,曹丕特意设宴饯行。
席间,曹彰闷闷不乐,酒过三巡,他突然问道:“陛下可还记得当年围猎时,我为你驱赶猛虎之事?”
曹丕手中酒杯微微一颤,随即笑道:“怎会忘记,子文勇武,天下无双。”
这段对话表面是兄弟叙旧,实则暗藏机锋。
曹彰在提醒兄长,自己曾是他的保护者;而曹丕的回应,则暗含了对这种武力的忌惮。
曹丕对曹植,更多是文人相轻的嫉妒与打压;而对曹彰,则是实实在在的恐惧。
诗词歌赋杀不了人,但曹彰麾下的千军万马可以。
曹植的《白马篇》写得再豪迈,也不过是纸上谈兵;而曹彰的铁骑,却真能踏破江山。
曹丕曾私下对心腹司马懿说:“植之文才,不过锦上添花;彰之武略,实为心腹之患。”
这句话道破了天机。
黄初四年,曹彰奉诏入朝,暴毙于府中,年仅三十五岁。
《世说新语》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卞太后得知曹彰死讯,哭着对曹丕说:“你已杀我任城,不可复害我东阿。”
这段记载虽未必完全可信,却折射出时人对曹彰之死的猜测。
曹彰死后,曹丕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他不用担心某天醒来,发现城外驻扎着弟弟的精兵;不用忧虑哪位将领突然倒戈,拥护战功赫赫的任城王登基。
历史往往被诗意的光环所笼罩,曹植的七步诗成了兄弟相残的象征。
但当我们拨开文学的面纱,会发现政治斗争的真相更加残酷。
曹丕真正惧怕的,从来不是能作诗的曹植,而是能征善战的曹彰。
在权力面前,笔墨终归要让位于刀剑,这才是铜雀台下最真实的暗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