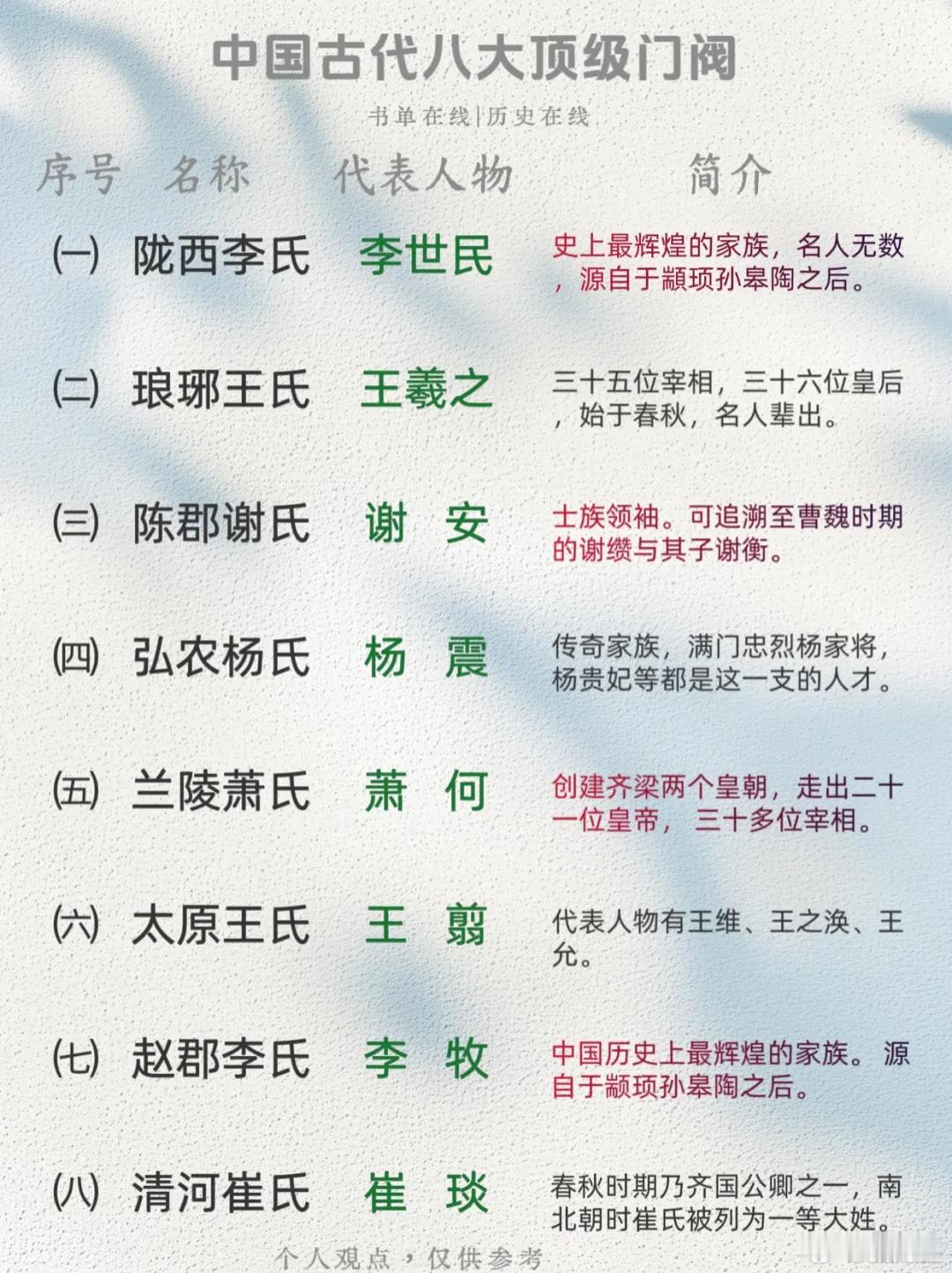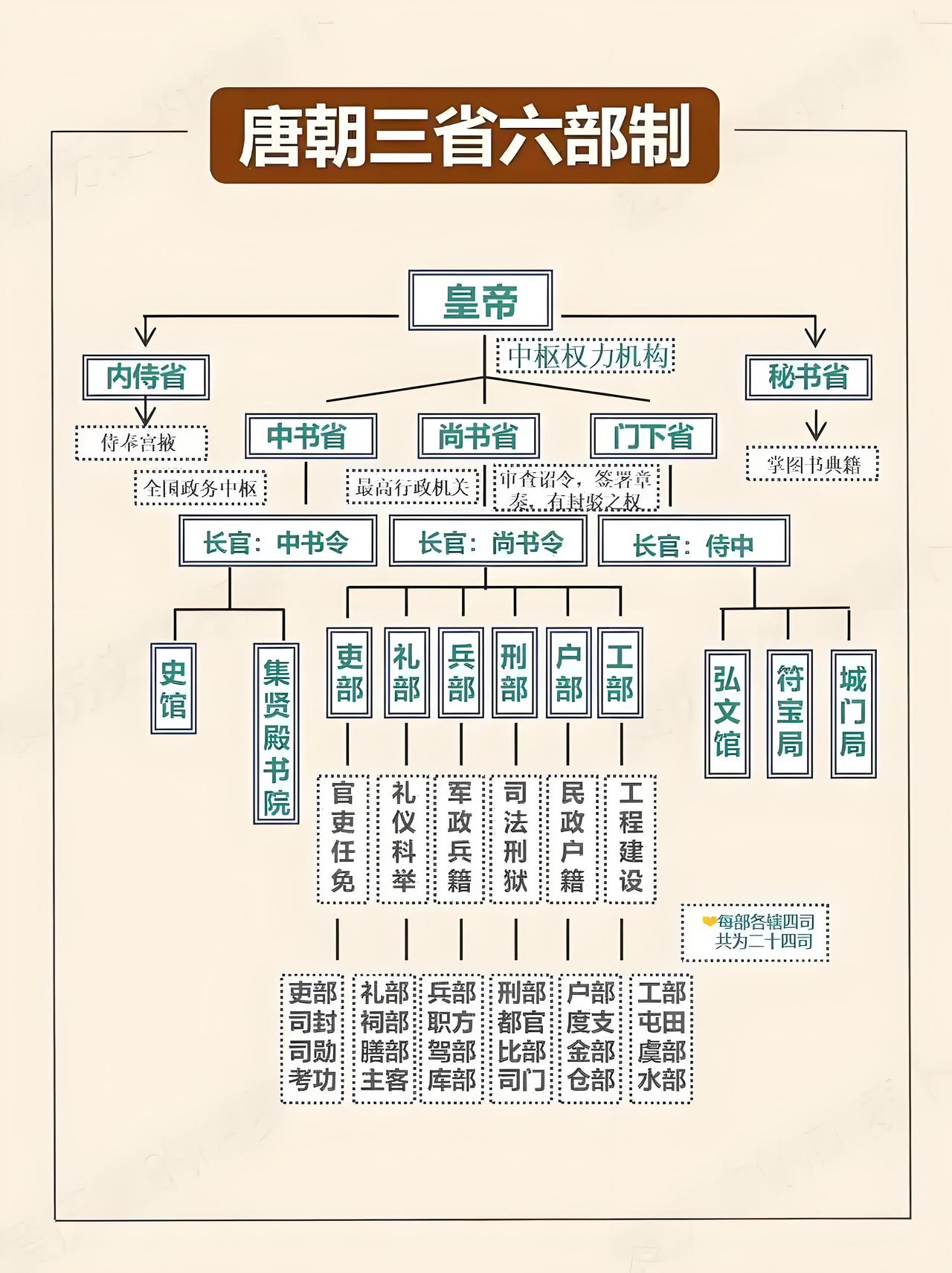中国自古有“衣冠上国”之称。在古代政治文化体系中,官员服饰不仅是标识其身份的物质载体,而且包含着文明秩序的核心隐喻,服饰的形制、色彩与纹饰共同构成一套精微的文化符号系统。那么,官服上都有怎样的图案与花纹?如何从官服判断一个官员的职位等级?一起来看看吧!
01
以色辨等——形制色彩中的等级秩序
中国古代官员服饰花样繁复、等级森严,其中蕴涵着古人对宇宙规律和人间秩序的反思,构成一套独特的政治文化符号系统。据《周礼·考工记》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周人率先将青、赤、黄、白、黑五色与东、南、中、西、北五方相对应,此后又发展出绿、红、碧、紫、骝黄五间色,与五行相对应,共同构成传统中华色彩体系,并进一步将色彩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元素相联结,形成包含视觉审美、社会等级、文化隐喻的传统色彩观。战国末年的“五德终始说”以色彩为媒介,结合阴阳五行以解释王朝更迭,将色彩上升为国家政治符号,后来被秦始皇所采纳。
自秦汉以降,历代王朝初立之时皆“改正朔,易服色”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确立官服制度,构成规训官员的符号权力。帝王通过修改服色制度进行权力结构的调整,既是审美趣味的变更,又是等级秩序的“符号重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秦尚黑并为汉所承继,其时自帝王至官吏皆着黑衣,上下服色无差。官员品秩的高低则依靠印绶区分,所谓“怀金垂紫”指的就是高级官员所佩戴的金印紫绶。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元年始定服色之制,“自天子逮于胥吏,章服皆有等差。始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朱紫”遂成为达官贵人的代指。唐代品色衣制度,表面看是行政等级的视觉区分,实则每种色彩都被赋予特定的政治意涵。唐太宗贞观四年,昭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以上绿,八品、九品以上青”,至此,官员品色衣制度基本形成,此后历代官服只是在紫、绯、绿、青四色基础上细化调整。自唐以来,色彩成为古代官员等级制度最为直观的物质载体,其通过色彩符号、配饰体系以及形制规定共同构建起“以色辨等”的官僚身份识别系统。
在传统官服系统中,服饰形制与色彩的设计,不仅是等级制度的物质外化,而且是伦理秩序的具象表达。在这里,抽象的伦理观念通过服饰形制完成对身体的规训,如宋代官服的“方心曲领”,其形制上圆下方,隐含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服饰色彩则始终遵循“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礼治原则进行等级化配置。作为贯穿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符号,官员服色制度的等差演变既折射出强化等级秩序的治理需求,又反映出传统礼制对社会生活的深度渗透。
02
以纹喻德——纹饰符号中的文化隐喻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道德”的文化,官员服饰毫不例外地体现着中华文明的道德功能。官员服饰作为标识官员身份等级的物质载体,其具象呈现是多要素协同的结果,在主体服色之外,还使用各种纹饰图案强化视觉区分度,形成与服色并行的补充标识系统。官服纹样构建出一套精密的视觉符号语言,通过服饰纹样严格的等级区分与文化隐喻,实现“以纹喻德”的道德规训。这一符号语言最早可追溯至《尚书·益稷》所载的“十二章纹”,它将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意象转化为身份地位的视觉明证,其中“山”纹象征着庄严和镇静,“火”纹昭示光明,“黼”纹象征做事果断,隐含对帝王及官员品行的道德要求。唐武德元年“高祖诏其诸卫将军,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袄子,织成紫瑞兽袄子。左右武卫将军服豹文袄子,左右翊卫将军服瑞鹰文袄子。其七品已上陪位散员官等皆服绿无文绫袄子”,以配合服色显示官秩的高低,而纹饰道德符号体系的完善,则体现于明清两代文武官员服饰的“补子”上。
明代补服制度将符号文化学运用到极致,文官绣禽、武官绣兽的设计,隐含着对官员道德品性的要求。明代官服的前胸后背均饰有金线彩丝绣成的“补子”,以标识官品。明洪武二十六年定百官常服:“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二品仙鹤、锦鸡,三品、四品孔雀、云雁,五品白鹇,六品、七品用鹭鸶、㶉鶒,八品、九品用黄鹂、鹌鹑、练鹊,风宪官用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马。”文官用禽鸟,武官用猛兽,这便是“衣冠禽兽”的最初来源。“衣冠禽兽”的文化符号实则包含着严密的道德隐喻:白鹇因其“行止闲雅”被用于五品文官补子,暗喻贞静清正;鹭鸶取“鹭行有序”之意配置给六品官,强调官场秩序;即便是武官系统的犀牛补子,也借犀牛“强悍耿直”的特性传递忠厚威严的寓意。在继承明代补服制度基础上,清代官服进一步精细化,清人在官服冠饰中增加“花翎”,通过羽毛眼数区别身份,这种视觉符号的量化处理,将官僚系统的等级秩序转化为更加直观的纹饰语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官服纹饰除正向的道德隐喻,也常采用“负向警示”的设计策略,最具代表性的是汉代司法官员的獬豸冠和明代风宪官的獬豸补服。《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法冠,一曰柱后……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将獬豸形象应用于服饰中,是取法传说中这种神兽能辨曲直的特性,以其独角的特殊造型,形成对贪腐及不公的潜在威慑。在符号学视野下,官服纹饰实现了三重维度的语码转换,即生物特征转化为道德规训(如以白鹇洁羽喻清正)、动物行为引申为日常准则(如以鹭行有序彰显官场纪律)、神话意象演绎为监察权威(如以獬豸辨奸对应御史职能)。最终将官服纹饰变成“穿在身上的监督”,将警示符号嵌入日常生活。
03
以制束行——礼仪制度中的实践规范
礼仪制度是华夏制度文明的核心,官员服饰则是礼仪制度的具象呈现,其形制、颜色、纹饰、质料的区别不仅是一种政治文化符号,而且是对官员等级、德行的制度约束。在礼法同构的传统社会中,官员服饰制度在法律编撰中属于礼令的范畴,一般包含在法典中的礼令章节之内。这一制度通过严密的符号体系及穿着规范,建构出一套“以制束行”的政治文化实践机制,将作为官员日常物质载体的服饰转化为规训官员行为、强化政治秩序的重要治理工具。这一制度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从荀子提出的“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到管仲提出的“度爵而制服”,已具备用服饰区分爵秩之雏形。据《汉书》记载:丞相、太尉和太傅、太师、太保,皆金印紫绶,掌副丞相、御史大夫则银印青绶,通过印绶颜色差异区分官阶,汉代将身份标识转化为官员随身佩饰,使等级规训贯穿于日常。
唐代正式确立“品色服”制度,将官员服饰的制度约束推向新的高度。通过颜色区分,在视觉上塑造出“满朝朱紫贵”的政治景观,更通过“借服”制度允许低品级官员在特定场合穿着高阶服色,形成激励官员进取的符号动力机制。《宋史·舆服志》载:“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宋承唐制,在继承唐代官员服色制度的基础上扩大鱼袋这一配饰的功能,使其在标识身份之外更添优抚之意,将制度的监督性柔化处理。明清时期的补服制度更把“以制束行”的理念发挥到极致,通过文化隐喻及礼仪规定,使服饰与政务、礼仪场景相对应,这些仪式化场景通过服饰的标准化,塑造官员的身体记忆和行为范式,从而借助服饰管理把官员仪表变为制度规训的直接载体。
在法律层面,历代对官员着装违制的惩处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咸亨五年五月十日,唐高宗颁发敕令:“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于袍衫之内,著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蠧彝伦;自今以后,衣服下上,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严加禁断。”《大明律》规定:“凡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若违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此外,当官员受到惩罚时,其服饰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明代对于降级违法的官员会褫夺其冠服,清代则直接“革去顶戴花翎”以示惩戒,这种“去符号化”的惩罚手段,把服饰制度与官员政治生命紧密绑定。站在现代行政学之视域,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官员服饰制度的管理充满智慧。一是传统官服将抽象的社会伦理、政治制度转化为具象的穿着要求,使官员日常着装行为变成制度内化的实践过程;二是利用服饰的可视性与标志性,建构起全天候的权力监督网络;三是古代官服制度借助纹饰符号的文化隐喻,形成非强制性的行为引导机制。
04
以服明道——传统官服中的礼乐教化
中国古代官服制度跨越千年,其形成、发展与演变历程绵延不绝,蕴含着深厚的政治智慧与精妙的符号艺术。该制度不仅是礼乐文明的载体,而且是儒家教化思想的具象呈现。儒家提倡的礼乐教化,实则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即借助礼乐文化的浸润与规范,以涵养德性、整饬秩序、化育百姓。从哲学维度审视,礼乐教化通过引导个体精神意识与行为模式从特殊性向普遍性转化,最终实现人类存在本质的普遍性跃升。因此,它既是高远的政治智慧,又是深刻的实践智慧。
从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政治寓言,到“以色辨等”的唐宋服色制度,再到“以纹喻德”的明清补服制度,这套将体制运行、道德教化与服饰制度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展现出儒家礼乐制度独特的教化功能。“品色服”制度通过等级可视化提高治理效率,以色谱管理替代繁琐的身份验证,这种将等级标识转化为日常视觉符号的理念贯穿于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官员服饰;补服制度的文化隐喻性规训,比抽象的道德说教更具渗透性,而“借服”制度则将官员政绩考核具象化。此外,古代官服制度颇具创造性地将法律约束转化为服饰语言,从而形成一套“服饰—身份—惩罚”的闭环管理系统。
从传播学视角观察,古代官员服饰作为“行走的政治标语”,其宣传效果远胜于静态的文字书写。例如,獬豸因其“触邪辨奸”的象征意义,被广泛应用于古代司法监察人员的服饰中,以时刻提醒他们“辨忠奸、明法理”;补服纹样所承载的道德隐喻,通过日复一日的穿戴,潜移默化地教化官员保持清正廉洁。古人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治理想,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服饰制度,通过对抽象制度的物化,增强其治理效力。这一传统秉承“衣冠明道”的理念,通过将礼乐教化的精神内核与服饰符号的物质形态有机融合,构建起官员服饰体系作为职业伦理载体的象征系统,进而实现人格完善、秩序规范与化民成俗的多重功能。这种制度设计既彰显传统政治哲学对现实治理的深刻关切,又以物质文化实践的方式确证儒家礼乐文明的主体性地位,生动诠释中华文化在礼制建构中一以贯之的文化自觉与历史主动精神。
◎本文原载于《人民论坛》(作者:和溪),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