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此日客边过,旧事重寻奈老何。
万里乡心随去雁,三更清梦逐惊波。
月临浅水涵秋影,云带斜阳下碧萝。
莫问金樽斟酒处,西风吹泪入悲歌。

这首诗以“年年此日”的客边漂泊为时间轴,通过去雁、惊波、浅水、斜阳等意象,构建出一幅充满乡愁与沧桑的秋日画卷。
全诗语言凝练,意境凄清,既有“万里乡心”的绵长思念,又有“西风吹泪”的悲怆宣泄,最终在金樽空对、悲歌自吟中,完成对游子命运的深刻叩问。

首联“年年此日客边过,旧事重寻奈老何”以时间循环开篇,将“此日”的漂泊定格为年复一年的生命仪式。
“客边过”三字平淡却沉重,道出游子身份的永恒性;“旧事重寻”则揭示记忆的反噬——越是试图回望,越被岁月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
“奈老何”的诘问,如秋叶飘落时的叹息,将个体衰老与时间无情并置,奠定全诗的苍凉基调。

颔联“万里乡心随去雁,三更清梦逐惊波”转入空间与梦境的双重维度。
“万里乡心”以距离量化思念的深度,“随去雁”将无形的情感具象化为候鸟的迁徙轨迹,暗含“归不得”的绝望;“三更清梦”则通过时间切割,将白日的克制与夜晚的脆弱暴露无遗,“逐惊波”的梦境意象,既指海上风浪的实体,更喻记忆中故国的残影如波涛般破碎重组。
这两句如对仗工整的楹联,上联写现实中的空间阻隔,下联写梦境中的时间撕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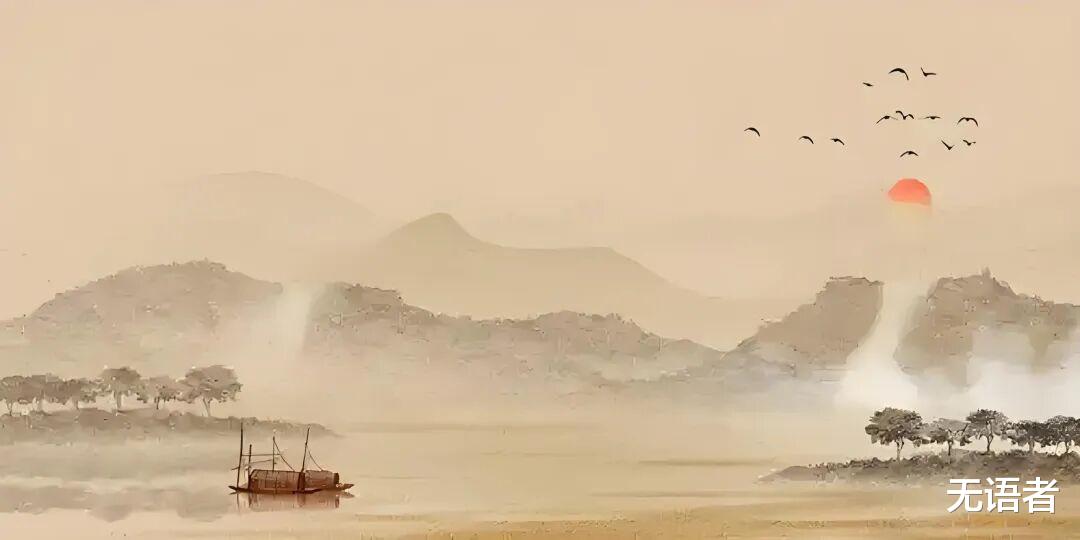
颈联“月临浅水涵秋影,云带斜阳下碧萝”将视角从内心世界转向外部自然,通过月、水、云、萝等意象构建出清冷的秋日图景。
“月临浅水”以倒影技法,将天空的皎洁与水面的幽暗交织,暗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涵秋影”的“涵”字如镜头聚焦,定格秋意在水中沉淀的瞬间;“云带斜阳”则以动态笔法,描绘云霞裹挟着残阳坠入藤蔓的壮丽与凄美,“下碧萝”的“下”字赋予自然以主动的告别姿态,暗示白昼的终结与黑夜的降临。
这两句如山水画中的留白与着色,以物象传递情绪,无需直白言说。

尾联“莫问金樽斟酒处,西风吹泪入悲歌”以动作收束全篇,完成从景物到情感的终极爆发。
“莫问”二字如决绝的盾牌,拒绝所有慰藉的试探——金樽空对,酒无处可斟,恰似乡愁无处可寄;“西风吹泪”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情感载体,风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内心悲怆的外化;“入悲歌”则以声音终结画面,泪与歌的交融,使私人化的痛苦升华为人类共通的生存悲鸣。
这种“以声证痛”的结尾,与首联的“奈老何”形成闭环,构成完整的生命哀歌。

全诗如一曲秋日变奏曲,从“年年此日”的时间循环起笔,经由“万里乡心”的空间跋涉、“月临浅水”的景物凝视,最终在“西风吹泪”的声音爆发中达到高潮。

它没有沉溺于自怜式的哀叹,而是通过“去雁”“惊波”“斜阳”等意象,将个体命运置于自然与时间的宏大叙事中审视——所有的漂泊都是季节的必然,所有的悲伤都是生命的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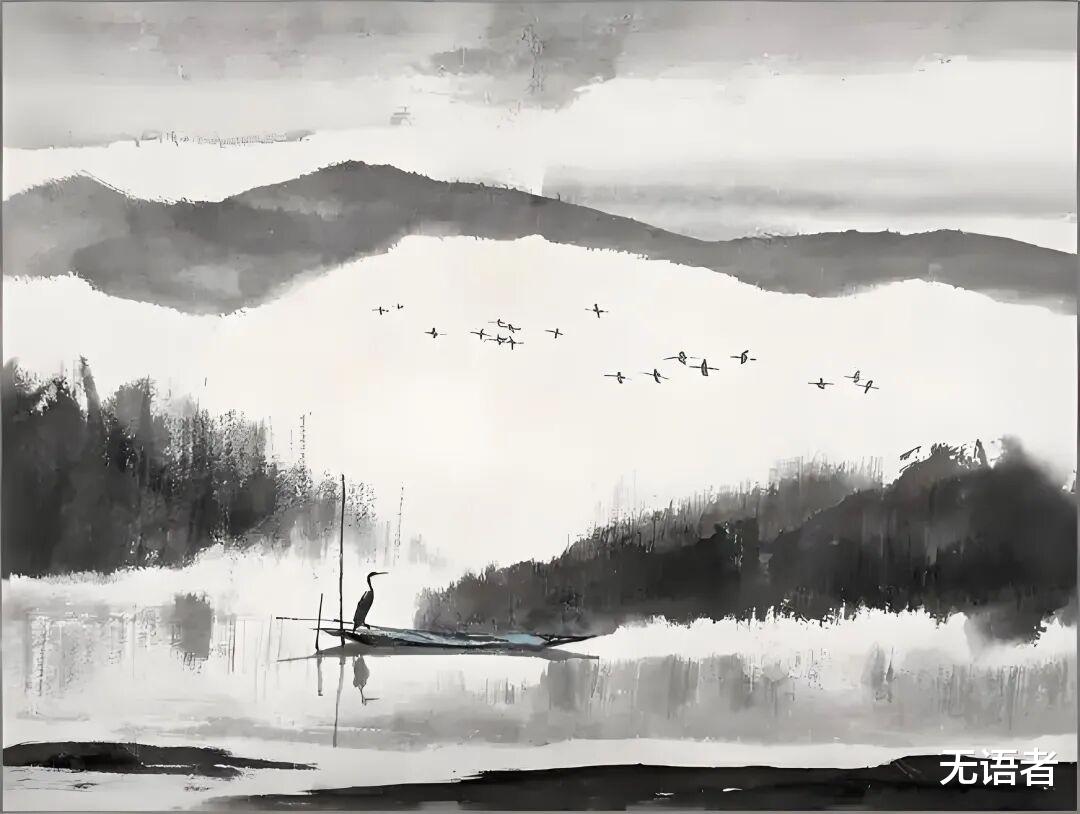
这种“小我”与“大化”的对话,恰似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的现代回响,最终在金樽空置、悲歌自吟的姿态中,找到对存在荒诞性的诗意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