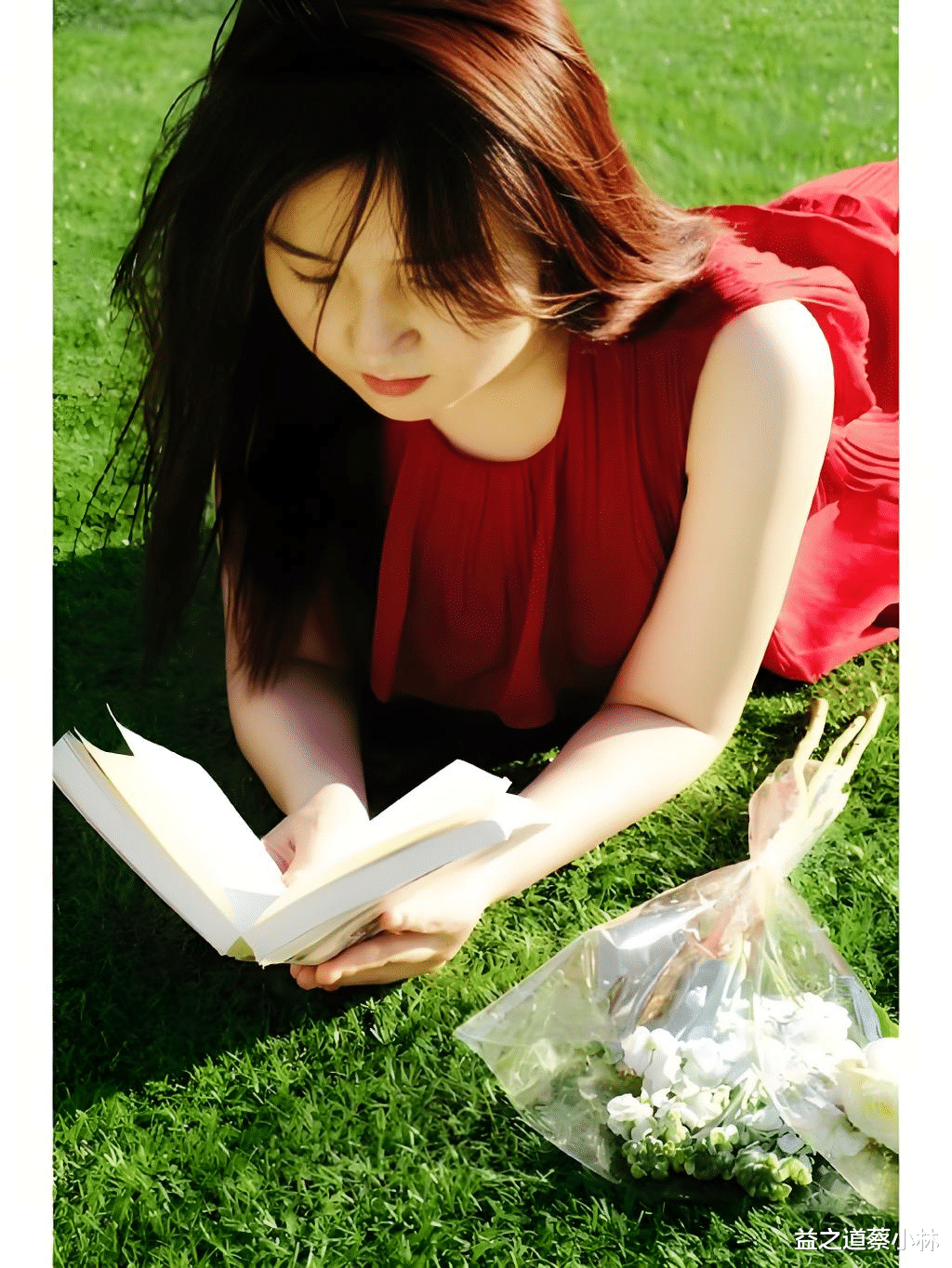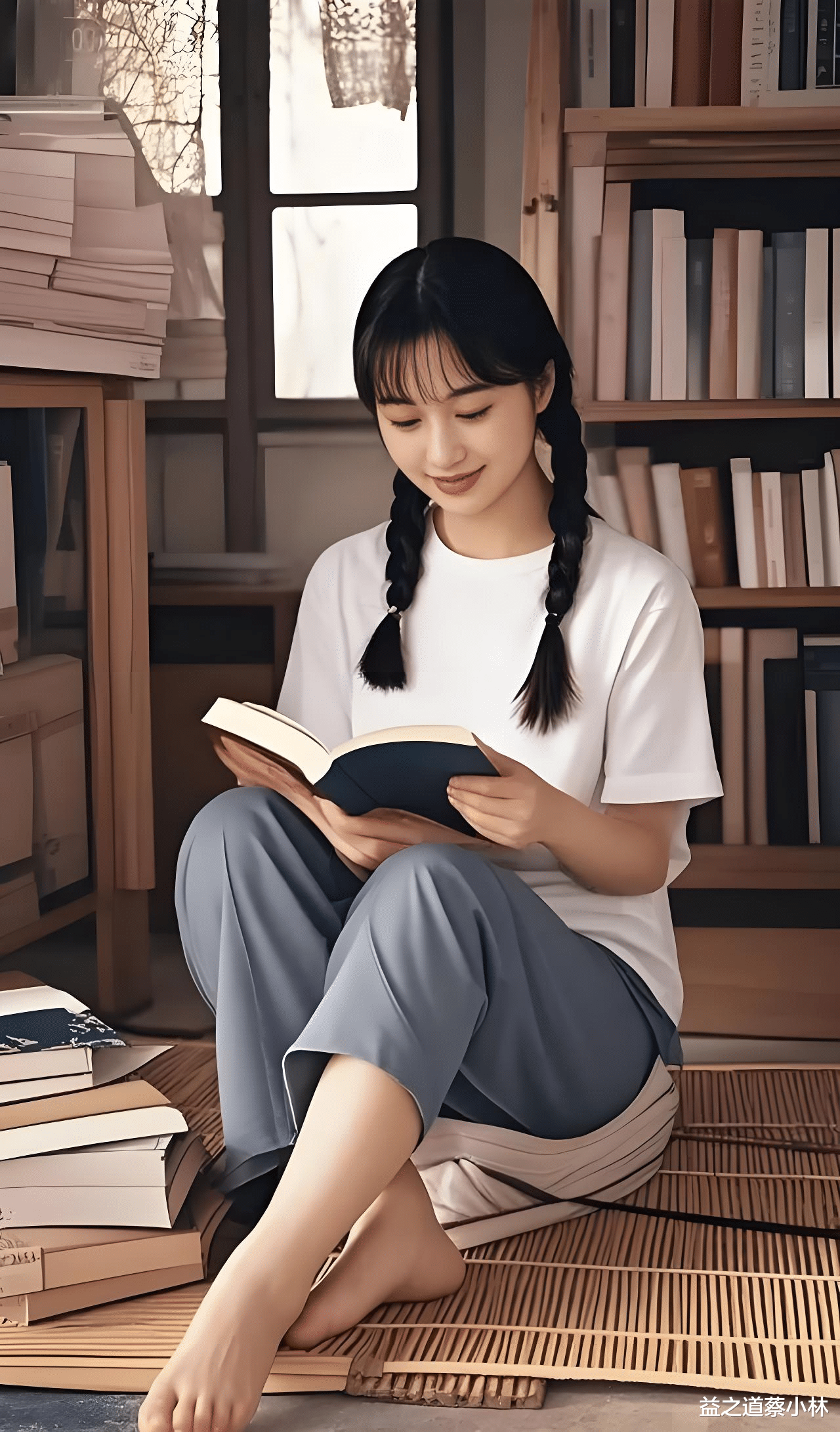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编物权,第三分编用益物权,第十章一般规定,第三百二十六条:“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
本条是关于用益物权人的权利行使的规定。
一、本条的历史由来《物权法》第一百二十条:“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本条在《物权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基础上增补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这一改动是《民法典(草案)》2020年5月提交给全国人大代表审议之后完成的。
二、制定本条规范目的或功能传统的物权法并不调整自然资源,也不调整自然资源以外的其他资源。自然资源的归属和利用是由公法和特别法调整的。但现代社会,不仅各种传统的自然资源如土地、水流、石油、矿产等因日益稀缺而凸显出更大的战略意义,而且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提高,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资源越来越受到物权法的调整。
如何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并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成为直接调整、规范物的归属和利用的物权法的重要使命。除新增的居住权外,《民法典》物权编所规定的典型用益物权,其客体都是土地,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另外,《民法典》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三百二十九条涉及的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以及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和捕捞的权利,也都属于为了调整自然资源利用关系而设置的权利。可以说,除居住权外,我国《民法典》物权编中现有的各项用益物权,都是围绕着自然资源的利用而设计的,在扩张物权法调整范围的同时,更为物权法保护环境和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奠定了基础。
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因此,应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根据本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应当遵守法律规定,禁止滥用民事权利。《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一原则被称为“绿色原则”。本条把“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用益物权合法行使的基本要求,为权利行使设定了绿色底线。这是“文明”、“和谐”价值观入法的体现,是“绿色原则”的具体呈现。通过一般规定加具体规则的方式,《民法典》将绿色发展、环境保护纳入制度体系,是对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破坏、环境危机、资源紧张,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回应。
从民法的角度看,自然资源是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物权法律制度的发展进程中,其经历了从重视物的归属到更重视物的利用的转变。尤其在当代,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增长,人们在对物的利用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的利用上的紧张关系有增无减。如何合理地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在更好地满足当代人对资源的需求的同时,满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物权立法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条关于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是《民法典》绿色原则在用益物权制度中的具体体现。
三、本条规范的具体内容(一)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自然资源用益物权是针对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设立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以及针对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权利。用益物权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等资源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如何使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是当前所面临的严峻问题。
自然资源具有不同于一般财产的特殊属性,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属公共物品,是环境要素的一部分,兼具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传统物权多注重对物的直接支配性和绝对保护性,其价值取向在于维护私人对物的支配和利用。而自然资源的公共物品和生态属性,决定资源物权制度设计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实现私人或者团体的利益,而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增进公共利益与公众福祉,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资源的稀缺性、耗竭性和不可再生性等特性决定了资源开发利用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资源利用中的冲突的加剧,使得物权法必须承担起合理和有序地利用资源的责任,“以使互不相侵而保障物质之安全利用”。
我国过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历了“先开发后治理”模式和“严格的环境限制下的资源开发”模式。前者虽然快速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由此造成环境破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后者虽然有效地保护了环境,但是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重要基础,需要大力寻找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源支撑。但是生态环境必然会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遭到破坏,保护环境必然会使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限制,两者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因此,除了需要提高当前的技术水平之外,更需要转变人们的发展理念。即转变传统意义上的以单纯消耗自然资源、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和高耗能为特点的开发利用方式,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真正实现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与所有权相比,用益物权的行使可能对环境保护有着更多的不利影响。主要原因是:
第一,从人的本性看,既然用益物权是权利人对他人所有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是利用他人所有的财产取得收益,一般不可能像对自己的财产那样从内心里珍惜爱护。
第二,从经济动因看。我国实行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主要涉及用益物权制度。由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有偿的,用益物权人作为一个“经济人”,在资源利用过程中会千方百计获取利润,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用益物权人往往会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从事生产开发,从而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加之资源的有偿使用一般均有期限的限制,会促使用益物权人在权利期间内拼资源攫取最大利润,这是加剧生态破坏的又一个原因。因此,《民法典》在设定用益物权的同时,要求“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以保证用益物权的依法正确行使。
对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以及保护生态环境,我国相关法律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比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国家鼓励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培肥地力,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承包方有义务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未经依法批准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承包方、土地经营权人违法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承包方给承包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发包方有权制止,并有权要求承包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矿产资源法》规定,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采取合理的开采顺序、开采方法和选矿工艺。矿山企业的开采回采率、采矿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应当达到设计要求。在开采主要矿产的同时,对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和伴生矿产应当统一规划,综合开采,综合利用,防止浪费;对暂时不能综合开采或者必须同时采出而暂时还不能综合利用的矿产以及含有有用组分的尾矿,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防止损失破坏。开采矿产资源,应当节约用地。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矿山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者其他利用措施。

(二)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
用益物权人对其依法使用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享有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用益物权虽由所有权派生,但它是一种独立的物权,用益物权人的权利具有排他性,不仅可以对抗一般人,而且构成对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限制。同时,用益物权人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受到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的限制,如土地使用权人要受到保护耕地及土地整体规划等方面的限制。
用益物权是对所有权的一种限制,具有优先于所有权的效力。主要体现在:(1)在用益物权依法成立后,所有人不能随意取消之。只有在具备法定事由时,所有人才能终止用益物权。(2)所有人行使所有权时,不得妨碍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3)所有人不能随意变更用益物权人对所有权的义务内容。(4)用益物权具有优先于所有权的效力。本条关于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的规定,即为用益物权优先效力的体现。
用益物权人可以依法直接行使权利,不受第三人的侵害和所有权人的干涉。比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其承包的土地有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发包方应当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需要适当调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的,应当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办理。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传统民法中,他物权作为所有权的附属性权利而存在,立法及其保护的重点在于保障所有权人的占有和处分权,在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上强调所有权优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上为促进物的充分利用,将立法重心转移到使用和收益权能上来,在保证所有人的所有权不受侵犯这一基本原则下,为平衡资源的私人占有和资源配置社会化之间的关系,他物权制度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当代,各国物权法都强调效益原则,促使物权法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由物的“归属”转向物的“利用”,以物的“利用”为中心发展并取代了以物的“所有”为中心。
可以说,用益物权已从最初附属于所有权的地位过渡成为现代民法中一项重要完整的独立的民事法律制度,成为物权法的核心制度,并具有调节“所有”“利用”关系,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价值,以及使物的利用关系物权化,巩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得以对抗第三人等诸多价值功能。应该说,用益物权在其权利范围内优先于所有人对该物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所有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系题中之意。
本条以明文规定的方式予以申明强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践中,在某些地方,侵害用益物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况还时有发生。例如,不尊重和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违反基本农田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在推行规模化经营等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一些农户的承包土地被违法收回或者调整。《民法典》在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利的用益物权属性的同时,强调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十分必要。
还应注意的是,《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的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四次审议稿和第五次审议稿都曾规定:“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不得损害所有人的权益。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其中,“不得损害所有权人的权益”这句话,后来被删除了。但并不意味着用益物权作为优先于所有权的物权,可以肆意行使。如果用益物权人不正当地行使权利,损害所有权人的权益,所有权人可以根据物权保护的相关规定维护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