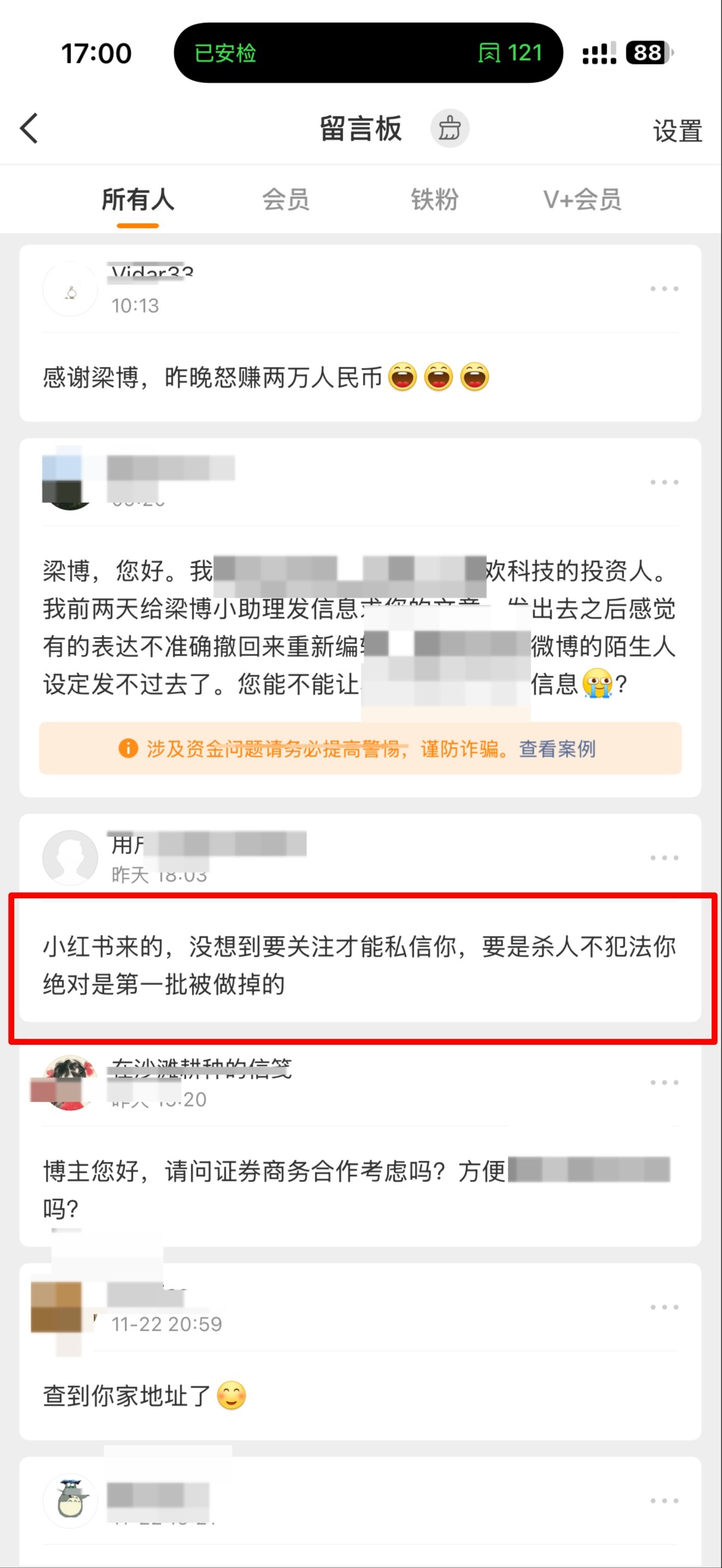高中班花骂我“乡巴佬,你配?”二十年后我营级转业,在县医院撞见拖地的她
......
「王建国,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配得上我吗?」
刘晓芳尖着嗓子念我写给她的信。
整个教室的人都轰的一下笑开了。
我感觉自己像是大冬天被人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浑身都僵了。
二十多年了,这事儿就像心口上扎了根刺,一想起来,还钻心地疼。
谁能想到呢,老天爷就这么能安排人。
我带我妈上医院看病,竟能在走廊上跟她撞个正着。
她一抬头,我俩眼对眼,时间好像一下子就停了。
过去那些事,乱糟糟地全涌了上来,我俩都傻在那儿了。
01
那年是1979年的春天,我高三。
刘晓芳是我们班的「一枝花」。
学习好,家里条件也好,她爸是县供销社的主任。
我呢,叫王建国,乡下泥腿子一个。
身上的褂子洗得快看不出本色了,裤子膝盖上还打着补丁。
眼看要高考了,我鼓起勇气写了封信。
趁下课时塞进了她的书本。
信里没说啥肉麻话,就说想跟她做朋友,考完试请她看场电影。
那晚我一宿没睡着。
第二天开班会,班主任刚说了两句,刘晓芳「噌」地一下就站起来了。
「老师,我这儿有个事,得当着大家伙儿的面说说!」
她嗓门又脆又亮,手里捏着的,正是我那封信。
她脸上带着笑,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毛:
「我收到一封信,有人不好好学习,净想些歪门邪道,我觉得这股歪风必须得刹住!」
说着,她就把信里的内容一句一句往外念。
全班同学先是愣,接着就「哄」地笑成了一片。
刘晓芳念完,眼光一下子就定在我身上:
「王建国,是你写的吧?」
教室里立马又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所有人都扭过头来看我。
「王建国,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配得上我吗?」
她把信「刺啦」一下揉成个纸团,狠狠地摔在我脚底下。
「你瞅瞅你那穷酸样,裤子上还打着补丁,一个乡巴佬,你凭啥觉得我能看上你?」
教室里的笑声更大了,有人还指着我的裤子吹起了口哨。
班主任脸都气青了,拍着桌子喊:
「安静!都给我安静!」
可话已经说出去了,伤人的刀子已经扎进心里了。
班会一完,我头都不敢抬,跟逃命似的冲出了教室。
一口气跑到学校后头的小树林里。
我背靠着一棵老杨树,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地往下掉。
可我没让它流多久,就用袖子狠狠地擦干了。
我咬着牙,在心里头发了个毒誓:
我王建国这辈子要是不混出个人样来,我就不姓王!我非得让你们这些看不起我的人,将来都高攀不起!
从那天起,我整个人都变了。
上课下课,除了看书就是做题,再也没抬头看过刘晓芳一眼。
02
高考前那一个月,我跟个活死人差不多。
脑子里除了做题就是背书,一天三件事:学习、吃饭、睡觉。
等真坐进考场,心里反而静下来了。
脑子也从来没那么清楚过。
考完最后一门,别的同学都嗷嗷叫着把书往天上扔。
我没跟着起哄,就是长长地吐了口气。
感觉压在心口的大石头总算搬开了一块。
离校那天,班里搞啥散伙饭,我压根没去。
自个儿卷着铺盖就回了乡下。
查分那天,我蹬着我爹那辆二八大杠,骑了十几里地到镇上。
手心攥着汗给学校打电话。
当老师报出我的分数,说上重点大学都绰绰有余时。
我捏着电话筒的手抖得跟筛糠似的,半天说不出话。
我爹听了信儿,那老茧扒拉的手一个劲儿拍我肩膀,眼圈都红了。
我娘更是直接捂着脸就哭了。
报志愿的时候,我眼睛都没眨一下,直接填了军校。
一头是不用家里再掏一分钱,另一头,我是真想去部队那大熔炉里炼炼,把自己炼成一块钢!
录取通知书寄到村里那天,我家那小土屋的门槛都快被踩平了。
我爹一辈子舍不得花钱,那天也破天荒地买了瓶好酒,请乡亲们热闹了一场。
走的时候,我娘一边给我缝被子,一边絮叨个没完。
我爹啥也没说,就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塞给我二百块钱。
那钱,都是他一分一毛从土里刨出来的。
军校的日子,比我想的还苦。
天不亮就得起,半夜才能睡,跟上了发条的陀螺似的。
新兵训练那会儿,好多城里来的同学都吐了。
就我一个人咬着牙,别人跑五公里,我就跑六公里。
可能是从小干农活底子好,也可能就是心里那股气撑着。
没多久我就成了队里的尖子兵。
大学四年,我一次家都没回过。
不是不想家,是怕一回家,心里那股劲就松了。
毕业后,我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边防部队,当了个排长。
在部队,我把兵当成亲兄弟,训练起来又像个黑脸阎王。
没过几年,我就从排长干到了连长。
每次立功受奖,我头一件事就是给我爹妈写信报喜。
有一回搞大演习,我带着我们连,硬是在山里潜伏了三天三夜。
最后出其不意地端了「敌人」的指挥部,立了个大功。
我们连队,在我手上连续三年都是「先进连队」。
我胸口的奖章也挂了一排。
眼瞅着前途一片亮堂,老天爷却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一次夜里搞演练,有个新兵蛋子脚下一滑,眼看要掉下山崖。
我飞身扑过去把他推开了,自己却滚了下去。
右腿当场就折了。
在医院躺了半年,命是保住了,腿却落下了病根。
走路一瘸一拐的,再也没法带兵训练了。
部队领导看我贡献大,又成了残疾,就特批我转业。
还破格给我保留了营级待遇。
我回了老家的县城,分到农业局上班。
离开部队那天,全连的兵都来送我,一个个哭得跟泪人儿似的。
回到地方,日子一下子从枪林弹雨变成了柴米油盐。
但我还是按部队的规矩来,干啥都认认真真。
农业局的工作,就是跟土地、跟庄稼打交道,这正是我老本行。
帮乡亲们搞点新技术,看着地里收成好了,我心里也踏实。
工作稳定下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把爹娘从乡下接到了城里。
让他们也享享清福。
03
一晃眼,我从部队回来都快十年了。
人过了四十,还是光棍一条。
不是没人给介绍,可处了几个,都没成。
部队待久了,人变得跟个木头疙瘩似的,不会说好听话,也不懂啥叫浪漫。
我娘天天在我耳边念叨,愁得头发都白了。
我只能打着哈哈,说缘分还没到。
其实我心里清楚,是二十多年前那道坎儿,我自个儿一直没迈过去。
岁数大了,爹娘的身子骨也一天不如一天。
尤其是我娘,老说头晕、身上没劲。
起先我没当回事,以为是老年人常有的毛病。
带她去镇上卫生院开了点药。
可吃了俩月,一点好转没有,人反倒更蔫巴了。
看着我娘一天天瘦下去,我心里头发慌,决定带她去县医院好好查查。
那天我请了假,天蒙蒙亮就陪着我娘到了县医院。
挂号、排队、抽血、拍片子,一套下来,日头都到当顶了。
我娘累得够呛,我扶她到走廊椅子上歇着。
自个儿去医生办公室问结果。
走廊里人挤人,乱糟糟的。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灰布工作服、拿拖把拖地的保洁员。
没留神把污水溅到了我裤脚上。
「对不住,真对不住!」
那人一个劲儿地道歉,声音听着有点耳熟。
我定睛一看,心脏猛地一跳——
那张脸,即便过了二十多年,即便憔悴了许多。
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刘晓芳。
当年那个在全班面前羞辱我的女人。
我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
正当我还在震惊中回不过神。
走廊那头突然急匆匆跑过来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
「王科长!王科长您可算来了!」
那人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满脸堆笑。
我定睛一看,是县医院的刘副院长。
跟我们农业局有过几次工作对接。
「刘院长,您这是……」
我还没说完,就听见身后传来「哐当」一声。
我扭头一看,刘晓芳手里的拖把掉在了地上。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又看看毕恭毕敬站在我面前的刘副院长。
「王……王科长?」
她的声音在发抖。
刘副院长还以为她不认识我,热情地介绍:
「对啊,这是咱们县农业局的王科长,今天是陪家属来看病的。」
他转向我,压低声音说:
「王科长,令堂的检查结果我亲自盯着了,一会儿出来我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那就麻烦刘院长了。」
我客气地点点头。
刘副院长又寒暄了两句,这才匆匆离开。
走廊里又剩下我和刘晓芳两个人。
她脸色煞白,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在原地。
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我看着她这副模样,心里五味杂陈。
二十多年前,她高高在上地羞辱我,说我是「泥腿子」,说我「配不上她」。
二十多年后,我成了她需要仰望的「王科长」。
「您……您是……建国?」
她终于挤出这几个字,眼眶瞬间红了。
我点点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是我。」
刘晓芳听到这两个字,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她蹲在地上,双手捂住了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都在看。
有护士小声嘀咕:「刘晓芳这是咋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蹲在地上的她。
脑子里突然闪过二十年前的那个下午——
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我的情书,说我是「泥腿子」,说我「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现在,她蹲在我面前,成了真正在医院拖地的保洁工人。
我深吸一口气,弯下腰,轻声说:
「别在这儿哭了,起来吧。」
她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看着我。
眼神里全是惊恐和羞愧:
「建国,我……我没想到……」
「都过去了。」
我伸出手,想扶她起来。
她看着我伸过来的手,愣了好几秒。
才颤抖着握住。
我把她拉了起来。
「你……你在县里当科长?」
她小声问,声音里带着不可置信。
「嗯,农业局。」
我简单地答了一句。
刘晓芳又是一阵沉默,眼泪还在流:
「我……我对不起你。当年那事……」
「都二十多年了。」
我打断她,「我早就不往心里去了。」
这话是真的。
看着眼前这个被生活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女人。
我心里最后那点恨意,也彻底消散了。
她低着头,手足无措地搓着衣角:
「你……你妈是来看病的?」
「嗯,老毛病了,来查查。」
「那……那要是住院,你有啥事就吱声。」
她抬起头,眼睛还红着。
「我在这儿干活,跑个腿、递个话啥的,兴许能帮上忙。」
我点点头:
「行,谢了。」
「哪儿能说谢……」
她赶紧摆手。
「我……我还有几个病房的地没拖完,我得去干活了。」
说完,她弯腰捡起拖把,低着头快步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那个有点佝偻的背影。
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回到我娘那儿,她看我脸色不对,紧张地问:
「建国,咋了?是不是娘的检查结果不好?」
我摇摇头,挤出个笑:
「没事娘,结果还没出来,咱先去吃饭,饿坏了吧?」
那顿午饭,我吃得是食不知味。
满脑子都是刚才那一幕,跟放电影似的。
吃完饭,我娘说乏了,我扶她回医院找了个地方眯一会儿。
我自个儿却坐不住了。
心里跟长了草似的,鬼使神差地就想再去看看刘晓芳。
医院这么大,我跟个没头苍蝇似的转了好半天。
才在一个楼梯拐角的旮旯里,瞅见了正蹲那儿歇气的刘晓芳。
04
她就蹲在一个小马扎上。
捧着个铝饭盒,正小口小口地扒拉着里头的咸菜和米饭。
听到我走过来的脚步声,她一抬头。
看见是我,眼睛里又是一惊。
「能……聊两句吗?」
我走过去,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跟平常一样。
刘晓芳「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手脚都没地方放,点了点头。
「你……你那腿?」
她眼神落在我走路有点不得劲的右腿上。
「在部队落下的。」
我没多说,转头问她:
「你来这儿干活多久了?」
「快五年了。」
她声音小小的。
「那阵子……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能有这么个活儿干,就不错了。」
我点点头,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接啥话。
就在这当口,她突然抬起头。
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
「王建国,我……我欠你一句对不起。当年在班上那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