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十六个皇帝,要是论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你敢信吗?他足足当了48年皇帝,差不多占了明朝国祚的六分之一还多,可偏偏有将近30年,躲在深宫里不出来上班,对外只说自己病了。这病养得可真够久的,养到朝堂上官员缺了一大半没人补,养到边境上乱子一堆没人管,最后落了个“明亡于万历”的千古骂名。你说这事儿邪乎不邪乎?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放着好好的江山不管,非要把大明往沟里带,这背后到底是真病得爬不起来,还是故意装病躲事儿?

其实早年间的万历,跟后来这副摆烂模样完全不一样。10岁刚登基那会儿,他还是个听话的小屁孩,对老师张居正那叫一个尊敬,张口闭口“张先生”,半点不敢怠慢。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读书,处理政务也规规矩矩,一点不含糊。那时候有张居正盯着、亲妈李太后管着,万历活脱脱就是大臣们心中的“圣君苗子”,朝堂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连“万历新政”都搞起来了,势头好得很。可谁能料到,张居正一死,万历像是脱了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四年后干脆直接撂挑子,再也不上朝了。

有人说万历是被张居正的高压教育给憋坏了,这话我觉得特在理。张居正当帝师的时候,对万历那叫一个严格到变态,稍微犯点错就往死里骂,还逼着他节俭,连宫里的日常开销都要抠抠搜搜的。可搞笑的是,张居正自己却权倾朝野,排场大得很。万历小时候没能力反抗,只能憋着,等张居正一死,积压多年的怨气瞬间爆发——抄张居正的家,流放张居正的亲信冯保,把老师留下的新政搅得稀烂。可收拾完张居正,万历才发现,没了这个“严师”,朝堂上那群文官,更难对付。

这帮文官跟张居正可不一样,张居正能一言九鼎压得住场子,他们呢?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整天围着万历的私生活和朝政指手画脚。其中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最牛,直接递了份《酒色财气疏》,把万历骂得狗血淋头,说他嗜酒、好色、贪财、爱发脾气,还反问“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翻译过来就是,你皇上能喝酒作乐,凭啥不让我们大臣聚会?换谁被这么指着鼻子骂都得火大,万历也不例外,干脆就坡下驴,说自己病了,从此躲进深宫,再也不出来见这帮文官了。

你以为他真的病到起不来?未必。万历的“病”,更像是一种政治武器。不上朝不代表不管事,内阁的奏疏他照样看,重要的决策他照样定,只不过把办公地点从朝堂搬到了后宫。就像他爷爷嘉靖皇帝,也多年不上朝,照样牢牢攥着大权。可万历千算万算,没算到文官集团会跟他死磕到底,而矛盾的焦点,就是立太子的“国本之争”。

万历心里早就注意三儿子朱常洵,毕竟是宠妃郑贵妃生的;可大臣们不答应,拿着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死磕,说“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朱常洛必须当太子。这朱常洛是万历临幸宫女所生,万历打心底里不待见,觉得这是自己的污点。就因为这事儿,君臣俩斗了十几年,大臣们天天上疏催立太子,万历要么留中不发,要么就说自己病了。到后来,大臣们干脆集体跪谏,堵在文华门不走,逼着万历表态,简直是变相逼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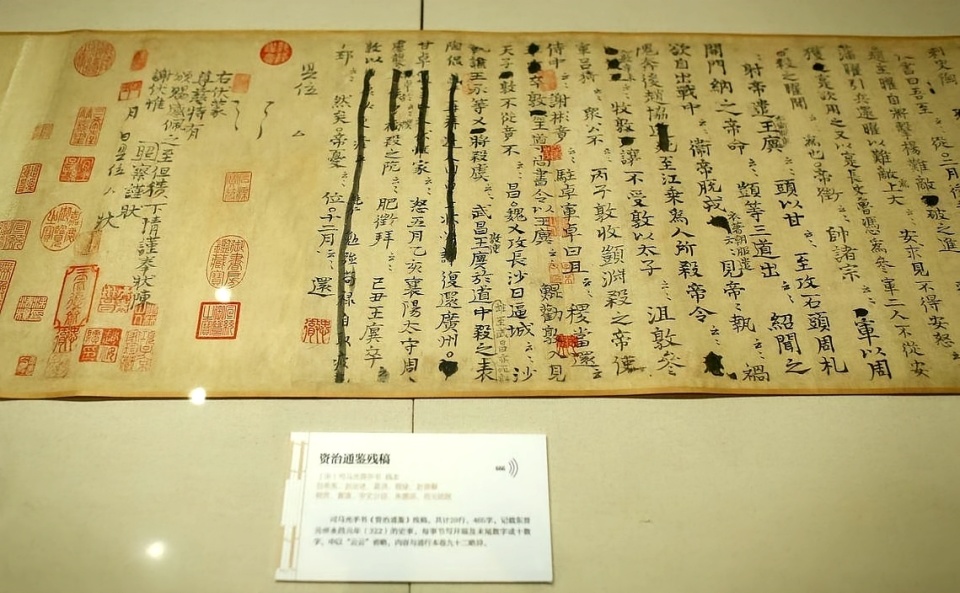
为了跟文官集团赌气,万历想出了个更绝的招——缺官不补。不管是中央的尚书、侍郎,还是地方的巡抚、知府,有空缺了就空着,反正你们跟我对着干,我就不让你们好好干活。到了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了三个尚书、十个侍郎,地方上缺了几十个知府,整个行政系统都快瘫痪了。内阁首辅沈一贯急得跳脚,上疏说民间的小孩都在骂他们这些大臣不作为,可万历就是不搭理,照样躲在宫里养病。

可皇帝能赌气,江山却赌不起。就在万历跟文官们死磕的时候,外面的麻烦早就堆成山了。西边的蒙古降将哱拜叛乱,东边的丰臣秀吉带着二十万大军打朝鲜,摆明了要以朝鲜为跳板打大明。要不要出兵援朝?大臣们又吵成一团,主战的、主和的互相攻击,最后还是万历拍板,派大军支援朝鲜。虽然最后打赢了,可也耗光了大明的国库,军队战斗力也大不如前。

更要命的是东北的努尔哈赤。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消息传到京城,万历倒是果断,下令兵部赶紧组织围剿。可这时候的兵部,连个正经的尚书都凑不齐,代理尚书薛三才还忙着跟万历催要军饷,根本不办事。等到万历越过兵部下令讨论围剿方案时,早就晚了,辽东总兵张承胤率军救援,直接被努尔哈赤全歼,自此后金势力彻底坐大,成了大明的心腹大患。

这时候的万历,是真的病了。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他就头晕目眩、腿脚发软,连床都下不了。可大臣们被他之前的“装病”骗怕了,根本不信,内阁首辅方从哲还直接上疏说他是故意拖延,逼他补官。直到万历允许方从哲进寝宫探视,这位首辅才明白,皇帝是真的油尽灯枯了。可就算到了这时候,方从哲关心的还是补官的事,重病缠身的万历只能虚弱地说“待朕体稍安,即行”,可这话最终还是成了空话。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这位在位48年、“养病”30年的皇帝,终于在深宫驾崩,享年58岁。临终前,他下了遗诏,承认自己“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还追悔莫及,下令补官、废矿税、发内库银子充军饷。可这些补救措施,早就为时已晚。他留下的,是一个朝堂混乱、国库空虚、边患四起的烂摊子,还有一群互相倾轧的文官集团。

后来有人说,万历的“病”,一半是真病,一半是心病。真病是常年沉溺后宫、疏于打理身体落下的,心病则是皇权与臣权博弈的无力感。他想摆脱张居正的阴影,想按自己的意愿治国,可偏偏被文官集团捆住了手脚,最后只能用“养病”的方式消极抵抗。可他忘了,皇帝的权力从来都不是用来赌气的,一旦大权独揽的皇帝选择躺平,整个国家机器就会失灵。难怪明史专家会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毕竟这近30年的空转,早就把大明的根基蛀空了,后面的皇帝再怎么折腾,也回天乏术了。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