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加玛帝国西北边陲的云岚山吹来,先掠过崖顶那株老松,再卷起她袖口一缕碎布。布色褪得发白,像被岁月啃噬过的信笺,只剩半行墨痕:
“弟子云韵,誓以云岚之名,守此山十年。”
她第一次把这句话念出声,是十七岁。那天清晨,雾气浓得能掐出水来,她抱着剑,踮脚去够殿门匾额上的灰尘。指尖碰到“云岚”二字,冰凉,像摸到一块碑。
1
同年,帝国北境雪原,她第一次杀人。
雪片被剑气削成六角形的玻璃,落在死者的睫毛上,化成水,像替他哭。她蹲下去,用袖口擦那人的脸——擦不干净,血渗进雪,粉成淡红。
“原来死人的脸,比师尊的戒尺还冷。”
她回山时,鞋底结了一圈冰壳,踩在石阶上“嚓嚓”响。师尊云山背对着她,只说了一句:“杀完人,记得把剑穗上的血捻掉,别让同门看见。”
她低头照做,指尖触到冰珠,忽然明白:云岚宗的白色,不是雪,是遮羞布。

2
二十三岁,她成了宗主。
继位礼前夜,她偷偷溜进藏功阁,把历代宗主的画像一张张翻开。画里人皆垂眸,像在默背同一句咒。她合起卷轴,顺手抽出一本旧册,封面写着《风絮剑注》——创派祖师手迹。
第二页夹了片枯花,五瓣,边缘焦黑,像被雷劈过。
她把它夹进自己剑柄的缝隙里。
继位那日,鼓声滚过三十六峰,她站在高台,风掀起袍角,露出靴帮一层旧泥——那是她前夜下山,去母亲坟头坐到天亮留下的。
她没哭,只是把剑横举过顶,让阳光在刃口走一道线。
“云岚宗,到我手里,不会再只是墓碑上的名字。”
3
再三年,萧炎闯山。
那天她穿的是素青裙,袖口绣着两朵云,针脚却松,跑出一条线头。线头被风牵着,一下一下打她手腕,像心跳。
她本可以一剑削掉那少年的头,却在剑尖离他咽喉三寸时,看见他鞋底裂开的缝——缝里嵌着乌坦镇的黄土,和他父亲没来得及拍掉的炉灰。
她想起自己鞋底也曾结过冰壳。
剑尖偏了半寸,削断他一缕黑发。黑发落在脚边,像一行被涂掉的判词。
事后,师尊怒她“放虎归山”,罚她跪雪。
雪夜,她把那片枯花从剑柄里抠出来,攥在掌心。雪化进水,花却奇迹似的软回一点韧性。
“原来雷劈过的花,也能再开。”

4
云山与魂殿勾结,东窗事发。
她是在后山瀑布旁撞见师尊的。老人背手立于潭心石,水帘从他肩头裂开,像给他披一件湿透的龙袍。
“韵儿,宗门与私情,孰轻孰重?”
她没答,只拔剑斩落瀑布一角。水声断了一息,又续上。
“弟子曾以云岚之名守山十年,今日,以云韵之名守心。”
出山那日,她只带走两样东西:母亲留下的铜镜——镜面有道裂痕,照人会多一条影子;以及那本《风絮剑注》,扉页上添了她新写的一行字:
“若风可逆,我愿倒吹。”
5
加玛帝国南境,她与萧炎再遇。
暮春,油菜花翻成浪。她蹲在地头帮农人拔菜,袖口卷到肘弯,露出小臂一道旧疤——那是继位礼前夜,她偷偷练剑被竹枝划的。
少年远远站着,手里拎一壶酒。
“云宗主,可敢喝一杯?”
她笑,用衣摆擦手,接过酒,仰头灌。酒从嘴角溢出,顺着颈侧滑进衣领,像一条逃窜的河。
“萧炎,我不再是宗主了。”
“我知道,你只是云韵。”
那天傍晚,火烧云压得很低,像谁把丹炉打翻。她倚着田埂的草垛,看少年御空远去,背影被夕阳剪成一枚黑色的柳叶。
她低头,发现铜镜不知几时从怀里滑出,裂痕里嵌进一粒油菜花瓣。
镜面因此多了一抹亮黄。

6
中州,花宗。
她拜师花玉,学的是“种花”。
第一堂课,师尊给她一粒灰扑扑的种子,让她种在雪线以上。
“活不了。”
“活得了,只要你肯用血喂。”
她照做。每日破晓,划破指尖,滴三滴血。第七夜,种子裂开,钻出一茎蓝胚芽,像一柄袖珍剑。
师尊说:“花与剑,同出一体,皆需以痛开刃。”
那年冬天,雪埋过膝盖,她抱着花盆下山,脚底踩出两串血窝。回头望,蓝芽在雪里颤,却未折。

7
花宗宗主之争。
对手是她师姐,擅用毒藤。擂台设在天目湖,湖面结着薄冰。
战至第三十招,她袖口被藤刺划破,毒液顺血入心,眼前浮起一层绿翳。
翳影里,她看见十七岁的自己,抱着剑踮脚擦匾额。
“云韵,若今日死,你可后悔?”
“不悔,只恨未见花开满云岚。”
她咬破舌尖,一口血喷在剑身,借痛破毒,反手一剑挑飞师姐发簪。
簪子落进冰湖,“咚”一声,像敲钟。
她赢,却未取对手性命,只俯身拾起那枚簪,插回师姐鬓边。
“花宗的花,不该用血浇根。”

8
萧炎成帝,云岚山旧址重建。
他派人送来一块匾,上书“云岚新宗”。
她站在残殿前,手指抚过那四字,忽然转身,把匾翻了个面。
背面空空,她拔剑刻:
“风停处,云不散。”
刻完,她收剑,顺手把铜镜埋进新殿门槛下——裂痕朝外,像一道永不愈合的眸。

9
很多年后,有童子入门,问她:
“宗主,我们为何练剑?”
她正俯身给那株蓝花培土,闻言,用沾泥的指尖点童子眉心。
“为让风停时,心里还有云。”
——
风确实停了,云却未散。
她站在山巅,旧裙褪成灰白,袖口再也跑不出线头。铜镜在门槛下生了绿锈,镜面裂痕被岁月磨得圆润,照人不分影子。
可每当夜雨敲窗,她仍习惯伸手去摸剑柄——那里空空,剑已赠与下一个离山的人。
她忽然想起,十七岁那天,雾气其实没她想的那样浓。
只是她当时踮脚,把雾气都吸进了眼里。

现实里,我们也守各自的“云岚山”——有人是工位,有人是厨房,有人是深夜最后一班地铁。
山不巍峨,却足以遮住远方。
偶尔,在打印机轰鸣或油烟呛鼻的间隙,我们会摸到袖口一条看不见的线头,被风一下一下打着手腕。
那一刻,想起云韵,想起她埋镜时那句没说出口的潜台词:
“若有一天,你再也握不住剑,就让裂痕替你照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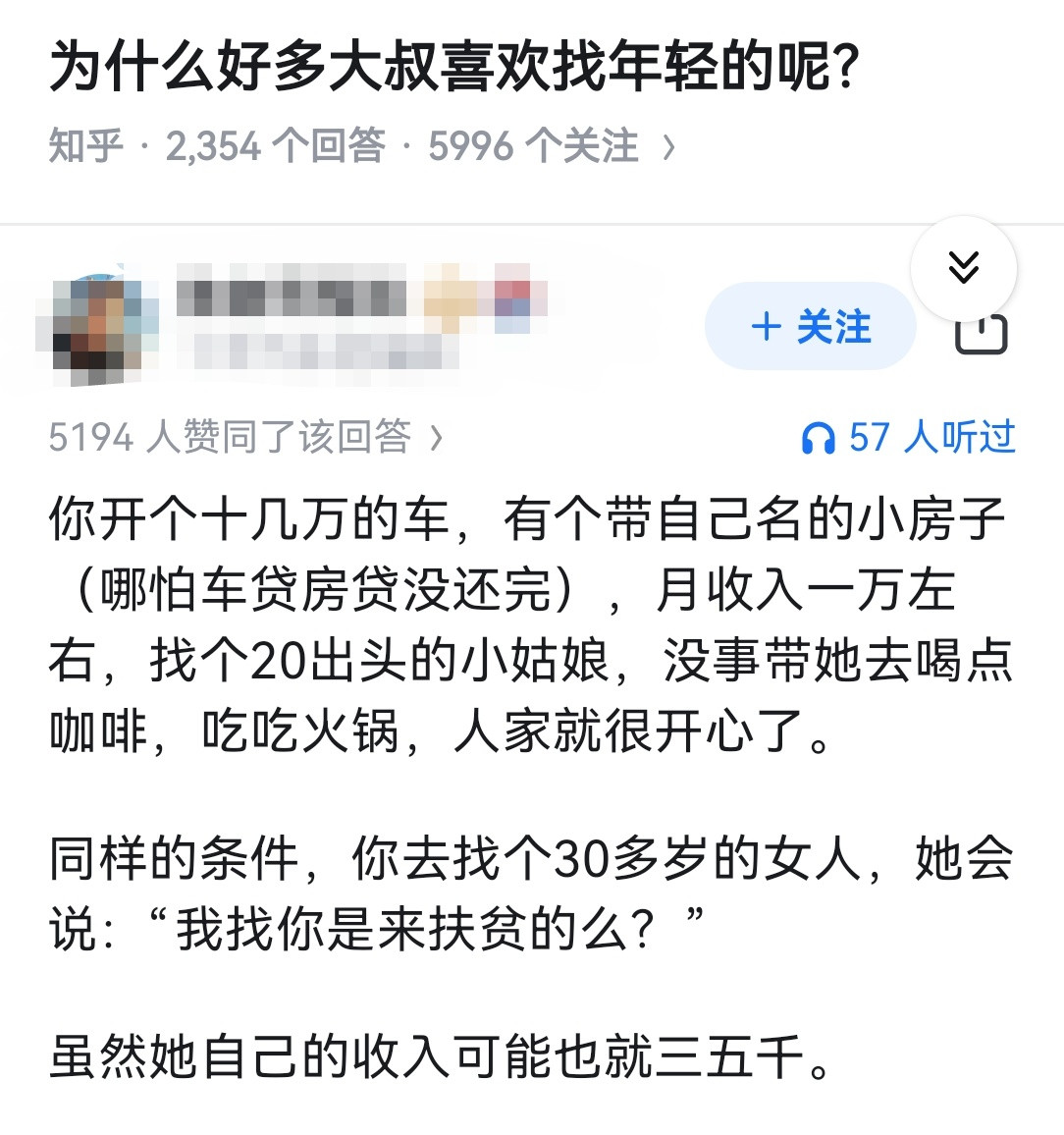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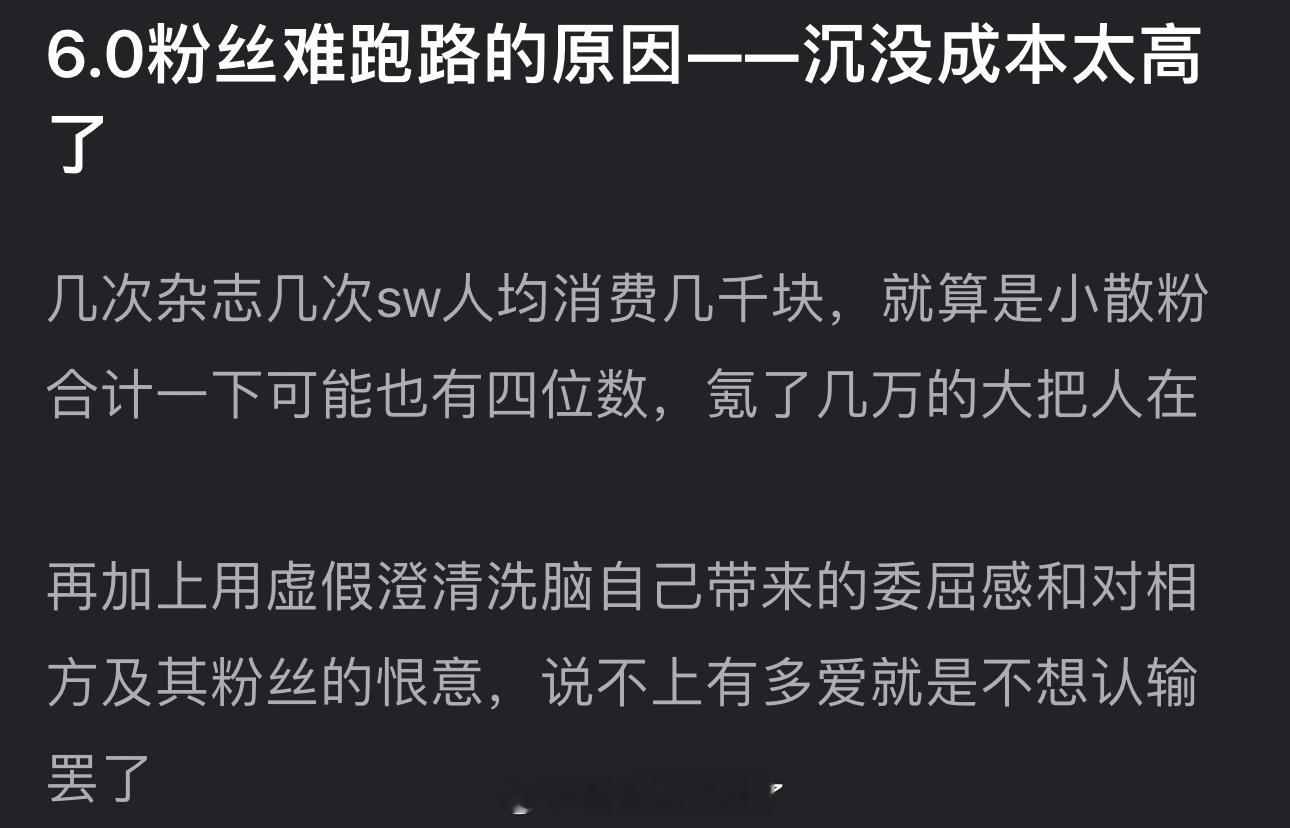
![这图谁做的[???][???][???]我这几天一直盯着这个榜单从来都不是这样[???]](http://image.uczzd.cn/6576684139151121982.jpg?id=0)

